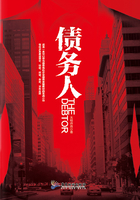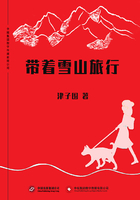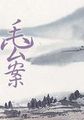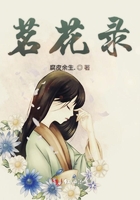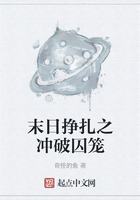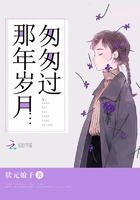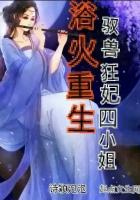这个季节实在不像春天,刚刚进入四月,那太阳就亮得让人难受,气温呼呼地往上窜,只眨巴了一下眼皮,气象台就说有摄氏三十度了。我居住和工作的这座新兴的城市,就整日地笼罩在高原丽日生产的腾腾热气里。天空很长时间没有云朵,只有为躲避阳光匆匆飞过的鸟类。天实在热得没有道理,还没有入夏呢,怎么就如同盛夏了?而这时候的每天晚上,我就坐在自家堆放了一些书的房间里,一边喝着浓茶一边操作一篇关于家乡的文字。这篇文字开始时本想写几千字就搁笔,可是一写,却写了三万多字,是全方位地从历史及现实的角度观照家乡了。因是写的家乡,方格稿纸中就经常出现“星云湖”字样,自家就觉得有清风拂面,不是在流着汗写字,而是在星云湖畔散步了。
这篇文字刚刚操作完,广东一家杂志的编辑长途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稿子。我说刚刚操作了一篇。他说是不是小说。我说不是,是一篇论述家乡的文字。他说你家乡是个什么地方。我说是一个县,山水相依,是滇高原上的鱼米之乡。
他“哦”了一声,说我怎么不写小说,要写什么“论”之类的东西。我说我那块乡土还真有特别之处,小说不容易说到的,就用“论”这种形式说了。后来我们又说了一些其它情况,电话交谈才算结束。我与这位编辑没有谋过面,只有电话和信件往来。因为我曾经在他那里发表过两篇小说,构成这两篇小说的零零散散的素材都取自我的乡土。事实上,我操作的被以为是小说的这种东西,根基都没有离开过乡土,只是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处理。大抵是小说这种东西,在许许多多的文字样式中还能够让识字人接受,因此,凡属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小说就成了顶梁柱。
读者喜欢小说,编辑看中小说,写字人也乐于操作这种很绞脑汁的文字,让一些人走马灯似地登场,让一些情节延展转换,演绎出奇妙的景象,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小说这种东西,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就成了另一个热门,将痴情男女们引入精神家园,饱受折腾。这就是来自小说的作用。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多元化,商品信息的渗入,小说的本真也流逝了许多,不似十几年前几十年前那么火暴。小说就受到来自其它文化式样的挑战。小说的领地就受到了挤压。有些原本是很地道的文学期刊,便也改变编辑策略,以发一些纪实性的文字为主了。写字人就得跟着调整思维方式,适应一种变革。独领风骚的小说失去了许多光彩。
我是一个有乡土情结的人,写字时不太讲究形式,因而就写得随心所欲和散淡恣肆,要转过弯恐怕还要一些时日。其中主要原因是我的心里总装着那方沉甸甸的乡土。那方乡土营造了我的文字环境和气氛。
我们说小说要有特色,此一地有别于彼一地。就我的那方乡土而言,有两个很突出的特色,在写字时是要认真把握和思索的:一是地域特色,因为有一个盆地,盆地里有一个湖,常常有许多事情发生。有一段时间文学界对“意识”这个词很敏感,各种研讨会的说话、报刊杂志的使用频率都很高,比如我们云南这块地方,就出现过“峡谷意识”之说。这个说法好像没过多长时间就消逝了。我以为这“意识”那“意识”,强调的只是地域特色。这才是本质。把一个本是十分容易接受的概念,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玄乎,拐了弯子去说道,是很费力的。我对地域特色的理解,来源于对盆地环境的认识。我曾经生活了许多年的那方乡土上的星云湖,是云南的很多盆地里没有的。而围绕着这个湖演绎出的许多事情,与其他地方就有了差异。这些差异就是特色,于是我总是有意或无意把我的文字融入这个背景里。二是人文特色。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及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习俗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期,并非短暂的时日。就说这方乡土,由那些出土的古滇国的青铜器来判定,时间的长河也许就流淌了两千多年,或者还要长得多。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语言慢慢规范,成为一个交流定式,并融入大一统的汉语音域里。生活习俗有了规律,比如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等,也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沿袭至今。当然,最富有特色的,应是生活于这块乡土上的人物,他们个性突出,生性直爽开朗,豪放豁达,勇于吃苦耐劳,而又头脑好用,常会有些惊人之举。他们一代一代地继承着祖宗留下的这份产业,不停地耕耘和创造。于是,这块乡土就由荒原成为沃野,成为滇高原的鱼米之乡;民族文化就繁荣,且有了特色。有时有乡人沐浴着星云湖的阳光而来,无论是街上碰到还是相逢于别的地方,总有热情握手和大声说话的场面,随意得不拘小节。拘小节了就不是那方乡土的人。突出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让这方乡土鲜活生动,色彩斑斓。我是在写了一些文字之后,才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的。但是每一次思想,都让我吃惊。我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即使不用所谓艺术手法塑造,用朴素的纪实笔法描述,写进小说的人物也栩栩如生。
认识一方乡土是要花一些时间和功夫的,而要用文字去表现乡土,叙述发生于乡土上的故事,或者那些各式各样的人物,更要气力。那块乡土,随着社会的进步,她也不断地变化,若上次去了眼前还是一片矮宅,下次去了就会长出一片高楼,让思维产生跨越,少了过渡。一个农民,春耕你还看他在田野里忙活,夏天了他就做起生意,见面了谈的是商品情况。一个家庭,今年还在温饱线上,明年不知就怎的发了财,富裕起来。如此的变化,我的笔头总跟不上趟,不能企及,不免愧疚。乡土的这种变化也时时提醒我,要增强自家的哲学意识,运足生活底气,提高写字技巧,使成为小说的东西与时代和谐,与乡土和谐。
将文字聚焦于那方乡土,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责任。我知道这种责任很重,可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就懵懵懂懂把他担起来了,并且经过一些折腾,仍然在有趣诱人的路上停停走走,疲惫地劳作。而这种劳作常常需要战胜自我,急功近利不行,心急浮躁不行。完成一篇文字,如同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要抱着让亲人看。看了以后,人家说“长”得还好,就得到了些许安慰,尽管自家感到文字里还有好多不足,以后还需要作许多努力。评品一篇文字,一百个人能有一百种说法。这便是小说的魅力,读文字的人有很多说话的权力。最近看到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这段话是一个标尺,可以衡量每一篇文字的优与劣。我如今操作的一些文字,少了刻意去追求的效果,多了随意性。在随意之中自然流露情趣,文字就可能变得好读起来,但又要时时注意调整情节,在沉稳和宁静中寻找突破。
我崇尚那方乡土,以虔诚的姿态去感应。说着乡土的话题是舒服的,写着乡土的文字也是有意义的。收录于这部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就是这样结构形成并发表的,有的还获过奖。是为序。
2005年初夏重记于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