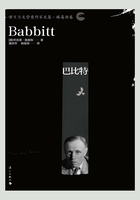九月底边,从湘西出来,在粤汉浙赣两路上来回游戈的中间,忽而感到了一个信念,在当时觉得非常之新异;但是说将出来,恐怕大家都要嗤笑,因为这非但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新发见,这并且还是妇孺皆知的一句抗战老八股。这八股的起讲,就是:“中国的土地,实在真大不过。”其次的承,转,合,当然也统是个老调子,就是:“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当时日我正在武汉下游二百余华里的周围,作殊死苦战。日机日日在江西湖南境界放黄鼠狼的绝命臭弹。死伤人数,日人与我,是二与一的对比。日日死二三万,我则伤亡日自一万至一万五千不定。长沙,虽则日日被轰炸,可一到下午三时以后,市面就照常的兴旺,依旧的拥挤。走到南昌,则戏园还在开锣,摩登男女,还在百花洲、公园里嬉笑偕行,决不像是百公里外的修水以北,炮火连天,正在作你死我活的争夺战的样子。
至于车路上哩,当然有补充兵的列车与伤兵车的来回上落;但是沿岸的秩序,两旁的居民,车上的旅客等等,都和平时一样,绝没有慌张绝望的神情。这些现象,是在说些什么话呢?不是在说:日我相持愈久,我愈对日人有自信,而相反的,侵略者则对我愈会感到焦躁困难么?并且在战线的前后左右,进出的次数愈频繁,感到的日并不足畏,我终有法能制胜的信念,自然也愈有确证。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去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上战线前后的各地一走就对。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得明白的。
所以我们的胜利,是决无问题的了;这反证,更可以在敌人的屡次提出求和条件,和再三再四的发表什么宣言上看得明白。唯其有了这一个信心,唯其有了这信念的确证,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为视察备战的情形,为加强抗战的力量,我跑到了东战场;更由东战场转到了国防第一线的福建的省会。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磨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福建的一隅,日人决不能轻易来进犯,这从我两个月的视察经验上讲来,是可以对大家保证的。
这一次路过厦门,船在死市外半里海中,停泊了一日之久。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一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奸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脸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寞的死市,我心里虽则也感到了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先知亚利米亚的哀歌,所吊的虽则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岂不是同郇市一样地,蒙了不洁了么!
第二天到了香港。香港是正在忙于过新年,一九三八年,只剩了七八日了,明年当是中国胜利获得的最可纪念的一年。我虽则不是预言家,但我也敢断定,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我们的抗战,以后只须支持七个月,就可以得到报酬了。这七个月的支持,只教有英美的金元,和苏联的机械热血,难道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么?
所可虑者,是日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的一般悲观主义者的得势。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在惊涛骇浪中写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五四期,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