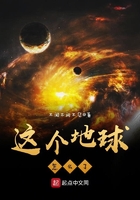我以为,他们是被馋哭的,当我把一盆烩菜端上去的时候,他们一致推着让亮亮吃。懵懵懂懂的亮亮狼吞虎咽地吃下猪肉时,田婶、大庆及姐妹们抽泣得更加厉害了。
每当年根临近,家里就张罗着宰杀年猪了。
一大清早,妈妈烧上一锅滚烫的开水,爸爸喊来一壁之隔的邻居田叔过来杀猪。我们兄妹们也都早早地起床,兴奋得仿佛等待一场“仪式”举行。
这时,房门被里出外进的孩子“鼓捣”得放弃了严格,雾霭蒙蒙的热气,一股一股地见机跑掉。院子与邻居田叔家的院子相通着一个小角门,杀猪的气氛通过角门或者天棚,弥漫开来。循着气霭,孩子们穿越角门跑来看热闹,田叔三岁的小女亮亮也跟在后面,叫哥哥大庆带上她一同参观,却被田婶给扯了回去。
田叔见儿子大庆也跑来看热闹,便断喝一声“轻点鼓捣门”!
大庆和我们兄妹几个一起打下手:找磨石、搓麻绳、用锯末垫地板、抱柴禾……
田叔倚在炕檐边磨刀子……
田叔家在林场是穷出名的“大户”。十口之家,全靠田叔一个人微薄的收入生活,日子总是接不上捻。
九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田叔,还不到四十岁,便被压得弯了腰,驼了背。但从他的脸庞看得出他年轻时定是一个俊朗的男子。
因为田叔有着一手的屠宰技术,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出去给人家宰杀牲畜呗,不少捞外快呢!
田叔淡然一笑,心不动,身不动。
不过谁家若是真的找到田叔宰杀猪羊,他虽然不推迟,也不要报酬,但是他要看这家人的口碑好不好,品质好不好,人际关系好不好,然后再决定帮还是不帮。
田叔并非屠夫,他的专职是名电工,所以在林场他显得尤为重要。暂不说他修理电路如何专业,若想吃上一顿鲜美的“猪肉血肠烩酸菜”却非田叔莫属。
田叔灌的血肠口感鲜嫩、味道独特,他煮的猪肝柔软无腥味。田叔宰杀时,下刀利落,不拖泥带水,内脏摘得干净,收拾得无残留。特别是剃猪泡、卸肋骨,他三下五除二完活,敏捷的动作仿佛轻松在舞蹈。由于,他的技术娴熟,干活认真,所以杀年猪都愿意找田叔宰杀。
当田叔将刀子磨好,在我们的辅助下爸爸已经把粗的、细的麻绳子搓得差不多够用,宰杀行动即将开始。
田叔先把棕绳系成非常专业的“套儿”,但要想让猪上他的圈套儿,仅靠田叔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派上了用场。我和大庆几个小伙伴一起围攻肥猪,先将它逼近猪圈的一个角落,待它没有回旋余地,田叔猛然套住猪的后蹄,它便在劫难逃了。然后,再用比较粗的棕绳将猪捆绑起来,大人们共同努力把它抬到事先搭好的架子上,这会,猪嘶声力竭地号叫,招引了一个个小脑瓜趴在院子的杖栏上,让“送别”的仪式显得是那样隆重而壮观。
当田叔手中的尖刀对准猪脖子下去的时候,我们把眼睛紧紧地闭上,趴在杖栏上看热热闹的亮亮被田婶蒙上了眼睛,她却哭着喊着要吃肥肉。刀子落地的时候,血顺着猪的喉咙不断地流到一个磨盘大的铁盆里,飞溅的血将雪地染得那样的壮丽。田叔手握筷子使劲地在铁盆里搅拌着。接着,我和小伙伴们操起大壶小罐从妈妈翻开的铁锅里往外提开水,帮助田叔为猪洗礼。
沸腾的场面仿佛是冬天里绽放的一束雾花,让围观的场景别开生面。当猪被脱掉了“毛衣”被搬进了室内后,围观的脑袋隐退了,可亮亮闹着要吃肉,不肯退去。
猪经过田叔有条不紊的处置后,一块块方肉下了锅,新鲜的猪肝下了锅,一根根红红的血肠下了锅,我们望着满满的一锅大烩菜,真的口舌生津,拭目以待了。
田叔看了看儿子大庆一眼,大庆无动于衷地和我站在一旁盯着田叔翻煮的血肠和猪肝。田叔又看了看儿子大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庆似乎明白田叔的意思,便灰溜溜地走开。妈妈喊:大庆别走啊,肉马上就熟了。田叔说:小孩子,吃的时候在后头呢。
很快,翻开的铁锅散发着喷喷的肉香,我仿佛感觉到,大庆和小妹亮亮们鼻子正钻进墙缝吮吸着香气。
妈妈找来一个花瓷盆,盛上肉、血肠、酸菜,命令我给田婶和大庆、亮亮们送去。以往,田叔肯定急忙上前阻拦,不让妈妈再盛了。这次田叔眼睛盯着妈妈手中的盆子一声不发,妈妈已经盛满了大半盆,田叔仍然没有阻止,我似乎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一种渴望。
当我端飘着肉香的烩菜送到田婶的房里时,看到炕沿上坐着一个陌生人。田婶和大庆的妹妹们都站在一边流泪。我以为,他们是被馋哭的,当我把一盆烩菜端上去的时候,他们一致推着让亮亮吃。懵懵懂懂的亮亮狼吞虎咽地吃下猪肉时,田婶、大庆及姐妹们抽泣得更加厉害了。
直到亮亮被那个人带走,田家响起一片哭声的时候,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慌忙跑回家中,痛哭着喊:亮亮送给人了,亮亮送给人了……
原来,田叔早就知道这个决定。田叔说:也许亮亮送给人还能过上好日子……说着他落下了纵横的泪水。
那天,田叔和家人都没有吃下猪肉,我记得田叔喝醉了,大家都哭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原委,心里却在暗自怨恨,都是杀猪闹的,似乎觉得那年的猪肉味道比以往逊色多了。
在学习中,在劳动中,在科学中,在为人民的忘我服务中,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捷连斯基
§§第五辑 绿叶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