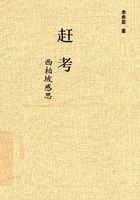今天,辗转听到周姆姆谢世的消息。
周姆姆和我毫无血缘关系,并不是我的亲人。但是我悔恨自己得到消息太晚,未能见她最后一面,送上我的哀思。一切都不能挽回,我只能把思念和哀悼一并化作文字,宣泄我的愁绪。
姆姆,是方言。意即伯母。
其实,她和我母亲同龄,今年八十有七。因此,在情感上,我总把她幻想成自己的母亲。她的老头子比我父亲大,因此称她为姆姆。
我是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她了。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将我卷到赣东北的乡村。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养猪场。姆姆家就在养猪场边。
她的身材,在农村里算是高大,不像我的母亲缠了脚,她长衣长裤大脚,站在人面前,竟使人感到威风凛凛。但她面善,常是一脸笑容。那笑容,就像春天里的阳光,令人感到温暖。她先是笑盈盈地远窥我们这些知青,见面也不说话,只是笑。后来稍微熟悉了,来到她家,她也不说话,只是为你端来一粗瓷碗的茶水,递送到你面前,然后,自己搬张小凳,捡个旮旯端坐,细细品听我们和她的儿子闲话。
临走时,她会出声:“就走啊,留下吃饭吧。”
不久,我知道周伯父长年在福建山区做木匠。元宵后出门,腊月后归来。周姆姆就一人拉扯着四个儿子。很特别的是,周家是迁徙户,选了个荒岭安家,远离其他村民,独家而居。但是,和周围的原住户关系和睦,相安无事。直到建起了养猪场,她家才有了更多的人气。我想,也许是她那张笑脸,也许是她的不多言语,也许是她耐劳的精神,像润滑剂,滋润了她和其他村民的关系。
后来,熟了。
我说:“姆姆,你和我妈是同龄。”她一听,脸上闪出兴奋的表情。竟怜悯起来:“你这么瘦小,就离开了妈。叫我样崽(她儿子,和我同龄)外出,我都会担心死了。”从此,她老叫我到她家吃菜。那烟熏的泥鳅干,那腊肉,现在想起来都馋。当然,喝得最多的是她家的大粗瓷碗茶。她还会将老母鸡下的蛋送给我,让我带回家。我呢,回乡下时,也会买些面条带给她。她的心肝宝贝老幺崽过十岁生日时,我和同学凑了六元多钱,买了一件绒衣给他。姆姆擦着眼角的泪花,高兴地收下了。我和姆姆,宛若亲人。
再后来,更熟了。
她偶尔会讲起自己的往事。有一年腊月,月黑风高,有个人竟来偷她家的鸡。鸡叫了,姆姆也悄悄起床了。她看见了偷鸡者,没叫什么捉贼啊!而是静观,偷鸡者竟没发现主人此刻站在旁边,还在捣鼓。姆姆笑了,说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我来帮你。”偷鸡者大惊。窘迫地看着女主人。姆姆竟真的抓了一只鸡给他。“快过年了,捉回去给全家人炖碗汤。”偷鸡者落荒而逃。姆姆说:“我是真心想送给他,他可能家中没鸡,或缺钱。过年了,少了鸡不成席啊。”
那时,我便对姆姆刮目相看。
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女人,竟然有如此胸襟!她的宁吃亏不占便宜的为人信念,成了她人生的不贰法宝。因此,她的人缘极好。附近的村民,有什么事也喜欢和她嘀咕。不过,我发现姆姆和她的儿媳极少交流,不知何故,只是默默地带着孙子。
姆姆家门口,有棵桃树,还有一棵柚子树,一丛茉莉花。逢到花飘香,树结果之时,她总会招呼大家来尝鲜,来闻香。那妖冶的桃子,那爿爿柚子,香甜可口,她从未想到过用这些果实去换钱。
后来,我上大学,姆姆还特意请我吃饭了。临别时,我图近,欲走后面的小门。姆姆笑盈盈地拦住,不允:“走大门。”她还放了鞭炮,我没有回头,想必姆姆家的庭院前,一片烟屑。
我曾先后几次专程去看过姆姆,谈起往事,她笑而不语。
姆姆走了。
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中国式的母亲。
母亲的儿子和同学说,姆姆临终时还喃喃地念着我呢。
姆姆,走好 !
清明时节雨纷纷。
我会献上一束洁白的花儿,放在你的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