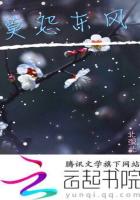钟敬文曾说过:“民间文学,在今天我们的眼里看来,不过是一种艺术作品,但是,在人类的初期或现在的野蛮人和文化国里的下层民众(后者例如我国的大部分的农民),他差不多是他们立身处世一切行为所取则的经典!一则神话,可以坚固全团体的协同心;一首歌谣,能唤起大部分人的美感;一句谚语,能阻止许多成员的犯罪行为。在文化未开或半开的民众当中,民间文学所尽的社会教育的功能,说来是使人惊异的。在钟敬文看来,民间文学的审美性不仅仅体现在生活活动中,还应体现在民众的主体意识之中。
一、回族民众的审美观与民间文学创作
回族民间文学是一种文学创作,其创作主体是广大的回族民众,审美主体也是广大的回族民众。因此,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回族民众集体的意识,体现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在许多回族民间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中,创作就是将自然生存状态下的人的所思讲出来,就是将心头的话唱出来。就如回族花儿唱的那样:“花儿本事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在回族民间创作的场域里,“与其说它是一种客观写照,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情感的主观抒发。其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在于反映愿望,而在于抒发的欲求。在这种特殊的创作活动中,创作的主体,常常又是对象本身,主客体之间几乎相融无间。”所以,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性突出地表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回族民间文学创作主体与审美主体是一致的。前面提到,回族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都是回族民众。与回族作家文学独立创作不同,回族民间文学的创作既有创作者的带动,也需要观众的共同参与,它是一种在场的展演。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域里,回族民间歌手或故事家与听众或观众,在现场的互动中,彼此回应,相互交流。有时他们还互换角色,歌手、故事家成了听众,听众成为歌手或故事家。在这种角色互换的过程中,创作者主体与审美主体界限变得愈加模糊,二者融为一体。
二是回族民间文学审美性是与其生活方式是相融相交的。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思维是回族民众在创造生活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集体意识。因此,他们“经常把生产活动诗话和神话,并借助神话传说的形式或叙事情节等,传达民间审美艺术的内涵。”与作家文学创作形式所不同的是,回族民间文学的创作是以集体的方式产生的,其思想的传达不是某一个体的思想意识,而是集体的,有时,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这一点在回族民族起源的传说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这一传说早已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记忆。其次,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性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而是渗透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自觉地表现在民间文学创作中。也就是说,审视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意义,必须将其放置在整个回族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从中寻找美,发现美。
二、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方式
任何一个民族的审美都带有自己本民族的情感意识,并有民族的情感意识决定了其民族的审美方式;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方式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意蕴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复合性特征。首先,回族民间文学是融合了中西方多种文化的元素,以及回族民众在主动汲取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美的思想,逐渐形成起来的。因此,回族民间文学既保留了阿拉伯文学的奇幻性、神秘性的元素,又融合了汉民族务实、质朴的、单一的风格。同时,它融入******教的思想,由此,孕育了回族民间文学的美学意蕴。
第二,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方式是功利与非功利的交织与重合。口头文学的传达是回族民众精神寄托的方式。当他们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讲出或唱出他们内心喜怒哀乐,他们的精神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的到来,也是他们摈弃一切苦难和忧愁,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是自己精神的主人,遨游、飞翔。所以,回族民众用花儿表达了这种心声:
花儿不是我欢乐着唱,
忧愁着就解了个心慌。
男人们心慌了唱一场,
女人们心慌了哭一场。
我唱了花儿你不用笑,
我解了心上的急躁,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
第三,回族民间文学的审美方式是认识与情感的交叉与融合。回族民间文学是一种“活态”的文学样式,它是回族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特定群体约定成俗的审美需要,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不需要过多的人为因素的加工,就可以流传,并产生相应的审美效应。”回族民间文学美的精髓是民众的创作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加任何雕饰。对自然万物、人生百态,回族民众从不掩饰自己的爱与憎、喜与怒等情感。即使他们在清真寺这样庄严、神圣的场所,他们也会直白地表露心声:
进了大寺朝西跪,
安来和海尔俩赎罪;
不是我不坐乃玛子,
阿訇他和我不对。
这种充满人性活力的歌声,恰是蕴含着艺术美感的载体,体现了广大的回族民间社会民众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对美的艺术的最热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