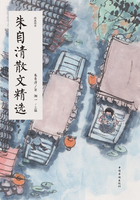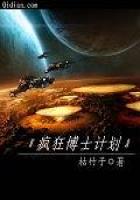每当我告诉他以自己在家所受的委屈,他总安慰我,嘱我拿出勇气来,不要无聊的苦闷。勉励我随自己的志愿去求满足打倒一切魔障,作个特立独行的新人,牺牲奋斗,往前冲去。但我应该怎样去牺牲奋斗?他自己在怎样牺牲奋斗呢?当他的生活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模糊了的时候,他每每以干文字生活的话答复我关于他的职业的询问。然而在报上,在杂志上,并不常常见到他的文字,书坊里仅仅排着他两三年前的作品。他时而广州,时而福建,文字生活要这样劳苦奔波的吗?他说在什么地方办报,在什么地方教书,但是劳碌所获,前年仅带着强悍冷酷的阴影和全套奇怪议论回家,备受父亲和继母的白眼。
近年来,他是连自己那个身干也不送回来给我们瞧瞧了。
神秘的哥哥,从前你要我无事可干的时候,到你那里去,现在你妹妹真的要来依靠你了。这样无用的妹妹,不会牵累你吗?
并不是为着卓然也想到上海去的便利,完全是出自自己的好奇,于是,我试探着父亲商量到上海去的事。父亲对哥哥只是谩骂,说不要家庭,忘恩负义,丧心病狂。但他对我到上海去的事,迟疑了一阵,终于听我自己作主了。若不是怕我坐吃山空,怕我像赘疣一样惹继母生厌,父亲是决不允许的。好呢,真个当水一般看待,要把女儿泼出去了,在我拿不到薪水,而反要在家坐吃山空的时候。
午后,颇觉沉闷,带着《穷人》在中央公园绕了一个圈子,便在水榭边的石堆上坐下。一页一页的翻阅着《穷人》,满想在这伟大的作品里得到一点发现,以资观摩;满想在这伟大的作者的灵魂里得到一点认识,可是看了第二段,便忘了第一段。看到第二页,便忘了第一页。心里好像有个无穷的大漏隙,什么都盛不下。灵魂的深处,好像有什么在穿凿,凿成了碎片,剪成了纷丝往四方八面飞散。书本和我仿佛是陌生的朋友,不曾有一丝的默契。我真不知自己这样轻浮,这样意志薄弱的。
游人渐渐多了,多了,把“僻静”推入了“闹海”。
雅静的山水,倏变了鄙俚的荒野;幽默婉淑的花草,沦落到狂荡泼剌的淫妇一般。到处是人,到处是冠冕的两足动物,连水榭边也络络绎绎的。他们全像幽灵,全像作祟的魔鬼,我说。无论谁,在这儿经过,总得留连一会儿,我每次抬头,总能接触许多道的眈眈的视线,心里愈想不看他们,却又时时去注意他们究竟是否还在瞧着我。这么,反使我眼睛所接触的视线愈多,心情潦乱,更加一个字都看不进眼。我是假装着看书来在公园里的游客前夸耀着自己是一个怎样有学问而且力图上进的有志女子吗?我是在这人欲横流中来卖弄着儒雅风流,来添浪增波,希冀有某种机会吗?我真不明白啊!我明明厌恶他们,暗地却又感觉着丑陋的自己也为人们所推重的一种愉快,本来彼此的目光相互投射一下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神经过敏的责备别人,而迟钝的宽恕了同样的自己呢?二十三岁的人,便装成古井无波的样子?外表装着巍然的道貌,柔弱的心田却又受不住石块压着似的苦闷,卑怯的女人呵!虚伪的女人呵!我只有自己羞惭,恼愤!
我决计不看书,挟着书走,往人稠的地方走。他们看我,我也索兴看他们一个痛快,但等到许多人追随在我的左右时,我甚至更羞惭,恼愤,徨无计了,幸而我在“公理战胜”的碑坊前遇着了卓然,他含笑走拢来招呼我,那些追随者才假痴假呆的走散了。我才稍稍心安一点,实际卓然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广漠的翻阅着男女间不曾发表的心底的著作,真是可笑而有趣的事!
但是和卓然谈起到上海的事,一切的烦闷又把我那自由的意志奔放的心潮重重桎梏了。我索然的回家,把自己在小房间里幽囚着。
六月二十九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风愈刮愈大了,黄金的太阳给密层的尘土包裹着,朦朦胧胧的好似郁闷的黄昏,我紧闭着窗门,满想与尘世隔离,然而纸糊的承尘依旧给吹得砰砰的响,桌上椅上到处铺着厚层的黄土,在空中飞扬着的,却无孔不入的尽往人喉鼻间钻拥,难熬的苦燥和闷热,几有令人窒息之可能。倘使人类是个两栖动物,这时我真想赤裸裸的钻进凉爽的水里,不再抛尸露骨在如此的人间了,倘使我能把自己分解成比灰尘还微细的体积,则悄然在许多尘土之间也可怡然自乐的生活着吧。但我是如此的伟大,如此伟大的我而竟莫能奈何如此渺小的灰尘!
想把自己勉强纳入雅洁清静的境界既是不可能,我只得禁抑着满腔的烦躁郁闷,拿本书来看看,但我看了《穷人》所得到的只有悲愁。看看《复活》,《复活》现在我眼前的只是凄惨的牢狱,我更焦烦闷热了,我索性丢了书本,躲在帐子里躺着去遐想,我这总仿佛舒服点。我们仿佛身入风和日暖的公园,苍翠的树木,芳艳的花,喜跃的啼鸟,标致而逸乐的游客……呵!我想入非非了,起首呢,我俨然是一个下凡的仙女一样,婷婷玉丽的旷达而和蔼的欢笑着,仿佛我的一举一动四周都充满着崇拜敬意的不可名言的情调。继而,我忽又变成一只小鸟儿似的,娇啼巧笑,在许多美丽温柔的手掌里狡猾的东跳西跃,实际却是闪烁的等候着一个最忠诚的,最勇武的英雄的捉弄。
但最后昂首环顾,我又觉着在这乐园驰骋着的英雄不是别人,而是我,我盯住那些俊俏的游客,凝神静气的拣择着可人的一个紧紧的追赶着,结果我勇敢的把他捕获了。那怕他是骗子,是流氓,是魔鬼,不管他的实质是怎样我只急急忙忙捉住那美丽的外貌,随心所欲的玩弄着,肆情的探求着,仿佛是战争,是嬉戏,是愉快,是凄清,也不知有天地,有人我,昏昏迷迷的,我终于瘫软了,溶化了,支解了,也仿佛满足了;但认为这是一种满足之后,却又倦怠,厌烦,而且忏悔了,最后我沉沉的睡去。
经清晨到现在,不过五点钟,这五点钟直同五世纪一样的悠久,我梳洗毕,同家人午膳,进膳时,我怕看父亲的脸,怕看继母的脸,心中横着不可挽救的羞惭,觉着这羞惭兀自有压倒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我糊乱的吃了一点饭,便退入卧室。
下午卓然来访。我们在客堂里谈话,父亲也加入了,我们谈到上海去的计划,最后决定在七月五日前起程,不管哥哥有没有回信。父亲是无可无不可,只是卓然走后,痴痴的瞧着他的背影,好像心里在说:“这姓刘的该靠得住吧?”
想起行期决定之后,不久就可离开此地,心花不觉开放起来。
晚边,狂风息了,飞扬的尘土敛迹了,我开了窗,掸了一切上面的尘土,痛快地洗了澡,用冷水浇了庭院,浇了花草,将睡椅从卧室内搬出来躺着,对着东边天际的彩霞,不禁沉思而微笑。
六月三十日
今晨起床稍迟,四肢无力,头脑昏闷,全身发热,仿佛大病将临的样子。后来才知道是……。照已住的情形,我不常有这样的病态的,是昨天那回事的缘故?是天气酷热,自己脑闷所致?我真不解,以后我得痛改前非,不再像昨天那样的无意识了。写在日记上,多末丢脸呀!多末难看呀!不过,这样,也可说是我犯罪的宣布。我要使自家看了生厌,厌了或能永远绝灭这无意识的行动吧!
本来,在时代的潮流急转直下之际,男女间关系的颓废,紊乱,堕落,放纵,差不多日益加甚了,性生活既没有准绳,性道德也没有定论。妇女们或者回避潮流,怀疑时代,或者感到恋爱的阙如,感到物质保障的摇动,或者感到育儿的苦痛和累赘,感到成了眷属的不自由,于是不敢从事结婚,更不敢自由的企求性的满足,宁肯让青春跟着流年飘逝,让欲火在心底燃烧,燃烧得走头无路遂行自渎。自渎仿佛也是一条无路可走时的一条路,可是这样的去求满足,满足以后,不仍然是个空虚,厌倦,苦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