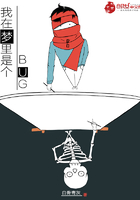武英殿。
“这些日子天气阴冷,御膳房特意给皇上准备了姜茶,皇上喝点,歇息歇息?”夕照将一个精致的青花茶碗放在崇祯案前,掀开盖子,几缕白烟飘出碗口。
“好。”崇祯展展后背,端起姜茶,小心的呷了一口,抬眼望了望窗外。
“雪不大,却总下个不停,教人心里不舒畅。”
“皇上不喜欢这天。”夕照笑笑,“要不等哪天雪停,天晴日暖的,小人陪皇上出宫散散心如何?”
“出宫……哎……”崇祯双目微合,轻叹了一声,“如今清军未退,京城尚在戒严之中,朕怎有心情出宫游玩。”
“皇上放心。有卢督师坐镇,清军很快便会退兵的。”夕照安慰崇祯道。
“唔……”崇祯又饮了一口姜茶,将茶碗轻轻放在了手旁,“你说,朕是不是催卢卿催得太紧了些。”
“两道手谕而已,皇上不必多虑。”夕照将端茶的托盘放在茶几上,“尚书大人说得也对,国内连年灾荒,又征战不断,粮饷一向短缺难济,战事还是速战速决,少做拖延的好。”
“朕便是听杨卿说所言有理,才下手谕过去,可卢卿本也并非消极怠战之人,这般催促总是……”崇祯话未说完,但听门外哒哒哒一阵脚步声迅速接近,传令太监手持一份信件,停在了暖阁门口。
“皇上!急报!急报!”
“拿来朕看。”崇祯才应,传令太监便快步上前,将信件拱手呈上。崇祯从弓着身子的传令太监手里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脸色骤变,腾地站起身来,连茶碗一起碰翻。姜茶泼溅在崇祯衣袖上,茶碗滚落下桌案,啪的一声,摔得粉粉碎。
“没烫着皇上吧!”夕照吓了一跳,连忙用袖子为崇祯擦拭。而崇祯却并不理会溅湿的衣裳和打碎的茶碗,瞪着眼睛呆呆盯着这封急报,半晌才微张开口,从唇间断断续续的吐出了几个字。
“卢象升……战死了。”
“卢象升死了?”
“是,卢督师以身殉国,随后清军攻往鸡泽,高公公军队亦不战而溃。”
砰!
杨嗣昌坐在自家后堂,耳中听着报信人的话,直觉得心里怒气上涌,抬手重重一拍桌子。
“高起潜这个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带不了兵就不要逞能,卢象升死便死了,可好好的精锐也让他糟蹋了!不战而溃,不战而溃!这怯战的罪名,他想让谁担着!”
“大人息怒……”报信的侍卫偷偷抬眼看了看杨嗣昌,又迅速低下头。杨嗣昌眉心紧锁,拄着手臂,沉吟了片刻,方才开口道:“罢了,事情发生了,总是得收拾,你这就去兵部把消息告诉陈新甲陈大人,另外教他找几个得力的探子来,我有事吩咐。”
“是!”
不到一个时辰,陈新甲调拨的三个探子便来到了杨府。
一个时辰的工夫,杨嗣昌已是压下了怒气,恢复了往常的泰然。只见他安稳坐在堂上,询问其中一个道。“唔……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名叫俞振龙。”应答者面皮黝黑,身材粗壮,很是一副勇武模样。
“好。”杨嗣昌点点头,“事发突然,报信人来得也匆忙,卢督师死讯只怕有所不实,你们这就前往巨鹿,好生探查卢督师究竟是生是死,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才可回来禀报。”
“遵命!”三人齐声领了命,便要离开。而杨嗣昌却直起身子,伸手一拦:“等等。本官话还未说完。”
“大人尽管吩咐。”俞振龙道。
“不过究竟是生是死,也并不打紧。”杨嗣昌嘴角一挑,眼中掠过一抹阴冷,“若是谁能探得卢督师怯懦畏战,临阵脱逃……三人皆重重有赏。懂了吗。”
三人闻言一愣,互相对了对眼神,都是闭口不言。这句话并不难懂,只是那其中的含义,让他们实在无法如刚才一般应得干脆利落。“好了,你们去吧。”杨嗣昌见三人呆着不动,便重新靠回椅背,打发三人道。俞振龙目光投向杨嗣昌,迟疑了片刻,勉强拱了拱手,与其他二人一起离开了杨府。
兵部的探子果然效率甚高,五日之后,俞振龙便从巨鹿归来,径直来到杨府,向杨嗣昌复命。
“本官交代的事,可都查清楚了?”杨嗣昌手中拿着一卷书正读,嘴上问着,也不抬眼看堂下的来人。
“查清楚了。”俞振龙低着头,恭敬答道,“卢督师……的确已经殉国了。”
听闻俞振龙这一句,杨嗣昌眉心蓦地一抽。确实死了不算,还不偏不倚的正是殉国,这兵部的探子到底是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们临走时,本官是如何吩咐的,你可还记得?”杨嗣昌心中不悦,但两眼仍只看着手中的书,脸上不见表情。
“小人记得。”俞振龙简短答道。
“既是记得,那卢督师究竟情况如何,你可真的查清楚了?”杨嗣昌说着,语气加重了些。
“回大人,卢督师在蒿水桥一战身先士卒,奋勇抗敌,最终寡不敌众,以身殉国,此事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俞振龙站在堂下,敛着神色,既不抬头,也不退让。
“你……”杨嗣昌书卷啪的一丢,眉头渐渐聚起一团阴云。他直直看着俞振龙,压着心头火说道:“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本官最后再问你一次,卢象升到底死没死,就算是死了,如何死的?”
“卢督师在蒿水桥一战身先士卒,奋勇抗敌,最终寡不敌众,炮尽矢穷,卢督师手刃数十敌兵后,身负四矢三刃,从马上跌下,以身殉国,此事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道神明,无枉忠臣!”
俞振龙猛一抬头,瞪起眼睛,话音句句洪亮起来,那夺人心魄的气势竟慑得杨嗣昌也暗自心悸不已。他牙根一咬,稳下心绪,随即展开眉头,又挂上了一副不慌不忙的淡定神情。
“好。本官明白了。”杨嗣昌重新拾起书卷,缓缓说道,“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他瞥了一眼对面梗着脖子的俞振龙,“来人,把此人带到刑部去,交代胡大人好生问他一问,兴许他才能想起点什么来。”
家丁得令,一拥上前,便要将俞振龙拖走,但谁知俞振龙身高体壮,几个家丁连拉带拽,竟都没能将他拉出房门。俞振龙面对着杨嗣昌,脸上丝毫不见畏惧,话甫一出口,嘴角竟挑起一丝轻蔑的冷笑:“杨大人说得不错,小人们查到的的确不止这些,杨大人怎不问问,本是三人同去,为何今日只有小人一人前来?”
“为何?”杨嗣昌很是不耐烦,只随口应了一句,但话音未落,却是脸色一变,“你们难道……”
“哼。”俞振龙大臂一挥,一下子甩开了试图挟持自己的家丁,“此时兵部的某位大人,应是将小人们查到的消息与卢督师的遗物,一同呈给皇上了吧!”
“什么!”杨嗣昌表情一僵,书卷一下子从手中滑落,还未等他多作反应,一家丁便匆匆跑进门来:
“大人,宫里来人了!”
“宫里来人了?!”杨嗣昌倒抽一口凉气,睁大眼睛,紧抓着椅子扶手,只见几个衣着华丽的太监前后走进房来,打头的太监清清嗓,尖声说道:
“皇上口谕,宣礼部尚书杨嗣昌入宫觐见。”
“微臣杨嗣昌,叩见皇上。”
“平身。”
从杨府到皇宫,这一路上杨嗣昌走得无比艰难。看那探子的神情,他们应是已查清楚了整件事情,至少他们一定是知道了,卢象升之死,背后有自己在推波助澜。虽然其中不乏高起潜的自作主张,但杨嗣昌明白,若皇上真要追责此事,自己再如何能言善辩,也是难以撇清干系。如何才能尽量避开责任,将事情都推在高起潜身上……就这样一路琢磨思量着,不知不觉间,他已跨入了武英殿大门,来到了暖阁之中。曾经赐予卢象升的那柄尚方宝剑,如今就横在皇上面前的桌案上,杨嗣昌看着宝剑,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而待他偷偷瞄向崇祯时,却发现皇上若有所思的浅蹙着眉,那表情与其说是震怒,不如说是疑惑。
“皇上召臣前来,有何旨意?”杨嗣昌试探着问道。
“关于蒿水桥一战,朕刚刚收到兵部详细的战报。”崇祯开口说着,语气似乎平静如常,“关于卢卿一事,朕觉得颇有疑点。”
“哦?皇上此话怎讲?”
“据朕所知,在南下之前,卢卿麾下一直是有宣大军三万,为何战报称蒿水桥一役,卢卿一处只有战力五千?”崇祯说着,直看向杨嗣昌。
皇上是果真不明,还是有意反问?杨嗣昌听了崇祯的问话,心里一瞬之间转过了好几番心思。看那俞振龙笃定的样子,他们应是确实掌握了事件内情,并向兵部告发了自己才对,而看皇上发问时的神色,却又好像当真是心怀疑惑,向自己求解。难道是陈新甲帮自己隐去了战报中关键的内容……?陈新甲一向与我同心,如此想来也是不无可能,既然有此可能,那么无论如何,此时也不能抢在皇上挑明之前自乱阵脚。杨嗣昌暗中打算好,便一欠身,从容答道:
“回皇上,南下清军势众,高公公处战力短缺,卢大人曾借兵增援高公公,所以兵力配比有所变化,由于此番调兵乃一时应急,也并非紧急要事,便没惊动皇上。”
“高起潜领四万军队,如何还战力短缺?而卢象升一借,又如何将主力全都借了出去?”崇祯眉头愈紧,又追问道。
“这……高公公虽拥军四万,但怎奈敌方十万大军,实在不好应付。卢大人怕也是如此考虑,才多借了些兵应急。”杨嗣昌恭谨作答。
崇祯打量着低眉顺眼的杨嗣昌,眼睛一眯,心中疑惑仍是未解。“果真如此……?但卢象升遇敌之地,与高起潜所在鸡泽相距不足五十里,却为何不见有半个援军前来解围?”
“高公公已调兵去救,只是未能赶得及……”杨嗣昌顿了顿,接着说道,“卢大人当时兵力匮乏,本不应这样贸然进军,只是卢大人他一向固执己见,他人劝告皆难入耳,如今一朝失算,便再无法挽回,以致国家憾失栋梁,臣得知此事,也是叹息不已啊……”
“贸然进军……莫非是朕那两道手谕害了卢卿……”崇祯喃喃说道,眼色一暗。
“不不,臣并非此意。”杨嗣昌赶忙辩解道,“就算皇上下了手谕,卢大人也应首先调回兵马,善做准备,再图进军之事。许是卢大人过分倚赖援兵在侧,才如此草率罢……总之依微臣之见,此次战败实因卢大人审时度势不足,皇上切勿自责。”
“哦……?”崇祯闻言,低着眼睛,默默思忖了半日,忽然毫无预兆的挑起眼角,目光直刺向杨嗣昌。这突然的眼神令杨嗣昌登时心中一沉,本已安定的心思又开始慌乱起来——从那几句问话来看,皇上的确是不知内情的,可为何此时看向自己的眼神忽又这样锐利,难道是自己的一语不慎,倒让皇上起了疑心?杨嗣昌忙一句一句反思起自己的前言,一时间虽没寻到什么破绽,但顾虑着言多必失,却也不敢再多开口。君臣二人就这样两相沉默相峙着,直至热茶凉透,方砚墨干,那令杨嗣昌最为担心的场面,到底还是没有出现。只见崇祯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垂下了眼皮,轻轻挥了挥手。
“你且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