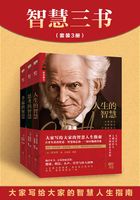夜深,黑暗吞噬了万物,白昼世间的喧闹皆躲藏进了夜色之中。
望月楼门前挂着两排灯笼,通明的灯火在黑夜之中尤为显眼。
某间客房。
床榻上的人儿半眯着眼,一手探到了枕下,手中握着一把匕首,另一只手紧紧的抓着被子。
沈素期昨夜半梦半醒间忽觉有人靠近,那人身上气味她太过熟悉,她所以当时第一反应竟不是醒来预防,而是睡得更加安稳。
是故错过了证实那人身份的时机,昨夜那人来了匆匆便走开,既然那人昨夜会来,便说明今夜也极有可能也会来,她只管等着便是。
微风吹动了烛火,烛光摇曳。
子时,一黑影落在窗前,缓缓朝床边移动去。
池靖卿今儿个跟随江湖神医学了一整日的号脉,现下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先是将沈素期的手从枕下拉了出来,岂料沈素期手腕一转,锋利的刀口对准了他的面门。
池靖卿心头一凛,下意识侧过身体,尽力掩饰着自己的面容。
沈素期一手扣上他的手腕,逐渐加大了力气。她虽中了毒,但毒素压制住时,仍可发出七成的力量。
不多时,池靖卿手腕上便出现一道红色印记。
屋内只点了一支蜡烛,因此光线太过昏暗,沈素期眯着眼睛,未看清他的相貌,冷声质问:“你是何人?”说话间,坐直了身体。
池靖卿抿唇不语,余光瞥见她缓缓下床,眉头一皱,当即甩开她扣着自己手腕的手,趁她因着惯性后退了半步时,迅速伸出手,夺过了她手中的匕首。
匕首在他手上翻转了一下,扔到了桌上。
沈素期心头一惊,好快的速度,当下拿出早准备好的茶杯,往地上一摔,当即有一人破门而入。
池靖卿听闻此声音,来不及去看清来人,快速走到窗口,一跃而下。
沈素期指着窗户,对着赵子威道:“那人刚刚出去了,你快些去追。”声音透着急切。
直觉告诉她,那人她认得,那熟悉的味道与触觉,使得她心底有一个声音响起,那便是无情将她抛弃之人。
赵子威一脚蹬上窗口,同时向下看去,便见池靖卿一手扣着床沿,一手被自己踩在脚下。
当即挪开脚步,扫他一眼,收回了腿,且关上了窗户。
沈素期见状,走到了窗前,怔怔问道:“赵公子,你为何不去追?”
莫非方才那人是他也忌惮的?若说江湖寮寮主忌惮二王爷,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赵子威向来不是怯懦胆小之人,怎会又退了回来。
后者略有不自然的避开了她的视线,拿起桌上的匕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自然些:“那人跑远了,我若追过去,难以保证不会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届时你便危险了。”
声音平静,他背对着她,看不见她眼底的疑惑,只听她问道:“你若追出去,也追不到吗?”凭他的轻功,竟也无法追上那人吗?
赵子威拿起匕首,耐着性子解释道:“素素,并非追不上,只是我更加担心你的安危。”话虽如此,暗自思量,池靖卿即已经放弃了她,今晚出现在这里,是为何意?
沈素期眉间几分失落,方才那人似乎是他……
她走到窗边,面对着凉风,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自己的手心,似是自言自语:“我到底在奢望什么……”声音轻微,随着一阵晚风,破碎在半空。
赵子威心头一紧,转身看着她,斟酌了一下,道:“素素,京城的事情交给别人吧,你不适合这里的勾心斗角,太过危险了,我带你走。”前几日若不是她身上没有文牒,他便直接带着她离开京城了。
无论她醒来后如何打骂,他皆不后悔。
沈素期莫名一笑,唇角隐晦,略带苦涩,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都逃不掉池靖远的眼线。”离开京城,这想法过于可笑了。
赵子威眉头一皱,反问着:“那么依你之见,下一步应如何?”话语一顿,猜测着,“莫非你还想回皇宫?”不必听她回答,他的语气中便透着一副不可能。
沈素期一时语塞,散落的发丝随着风微微扬起,迷乱了视线。她抬手将发丝理在耳后,露出略显无奈的桃面:“年关之前池靖远会到护国寺祈福,届时会与主持单独见面,这便是一报仇的好机会。”
只有提到仇恨时,她黯淡的双眸才会闪现异样的光芒。
赵子威心头一紧,不假思索,便道:“素素,皇上出行必定会有大批高手随行,一点杀气都不会放过,只凭你一个人,便要杀了池靖远,犹如螳臂当车。”语气尽是不赞同。
岂料沈素期此次竟莫名的坚定,闻言半点未犹豫,道:“赵子威,池靖远与我本便是云泥之别,这是最为合适的机会。”即便会再次搭上性命,她也不忍错过此次机会。
赵子威见她神色坚定,便想到了当初拦截秀女马车时,那意外许是她一手造成的。心头暗惊,她为了报仇,竟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顾他人生死……
他所认识的沈素期,何时变成了这幅模样?
沈素期见他一时未言语,关上窗子,缓缓走向床榻:“赵子威,我现下已无大碍,你若无事,便早些离开吧。”语气淡漠,一手掀起被角,躺了进去。
连男女大防都全然不顾,这当真是最初与他交谈都会脸红的沈素期吗。
赵子威说不清是何心绪,只叹息了一声,朝门口迈着步子,突然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脚步一顿,一手触碰到门,低声道:“素素,无论你因为仇恨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走。”一字一顿,声音坚定。
沈素期呼吸一滞,听着关门声响起,蜷缩在内侧,背靠着墙壁,双手紧紧的抓着被子,长叹了一口气,尾声轻颤。
翌日,晨光熹微。
午门前,文武百官分两列排队而站,今日不同之处在于,在文官之中,有一身着红袍的男子,眼神清冽淡漠,面孔棱角分明,且线条冷硬。
超群绝伦,立于乱世而坚韧如石。
便是新科状元,状元本非官员,不过有了一个可入朝为官的身份罢了。
是故现下新科状元站在这里,也无人拉拢,从现下四国趋势来看,战争是早晚的,现下皇上应重武,文状元估计是无用武之地了。
午门开启,百官进殿。
冬日朝唐殿大门紧闭,殿内阴冷空旷,今日却因皇上少有的和颜,气氛稍有些缓和。
池靖远一手搭在龙椅之上,摸样略显随意,他一随意,大臣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朝拜过后,礼部尚书上前一步,弯腰恭敬道:“启禀皇上,今日乃是新科状元任官之日,还请为新科状元赐官。”声音朗朗,盖过大殿众臣。
话语一出,群臣相互看了几眼,似在无声交流着。
池靖远坐足了明君的样子,环视众人,缓缓道:“众爱卿以为朕应认命段状元何官职。”难得的,语气中没有逼迫之意。
兵部侍郎上前一步,道:“皇上,文状元乃是文官,现下四国战事将起,皇上应更为看重武将才是。”这话说的公正无私,实情也确实如此。
镇国大将军点了点头,上前附和:“皇上,臣也以为大越正是用人之际,武将必不可少,文官嘛,太平盛世方可重用。”
这话不仅否定了段喃,同时也贬低了在朝文官。
自古文武不两立,此话一出,立马有文官站了出来。
御史大夫举着朝笏,道:“皇上,安内方可平外,若不注重治理国家,如何应对外国?”说到最后,神情几分激动。
祁国公见有人站出,当即附和:“皇上,无内患才可扫平天下,还请皇上三思!”扫平天下几字,正中了皇上下怀。
池靖远一摆手,顿时大殿安静了下来,他看向段喃,沉声问道:“段状元可有何想法?”话一出,段喃立即成为了焦点。
段喃面不改色,眼神淡漠,无恭维也无刻意,坦然应道:“草民相信,皇上定会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话说得毫无私欲,池靖远眼底滑过一丝赞赏。倘若不是先前见过了他表忠心的样子,当真会以为他自持清高。
池靖远坐直身体,毫不吝啬欣赏之意,道:“大越内部需要才人治理,翰林院许久未入新人了。”话语一顿,看向众人。
众臣倒吸了一口凉气,翰林院?就算是皇上惜才,这官职未免定得太过高了。
先皇在位时,也只有一位状元入了翰林院,便是侍讲学士闵瑞文,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先皇重用世家。
现下段喃刚中了状元,便进了翰林院,皇上如此,难免教人以为翰林院随便何人皆可进入。
文臣一列当下响起了异议的声音。
岂料皇上根本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续而道:“翰林院空缺了内阁学士,恰好赶上了科举,一切皆是天意。朕将段状元认命为内阁学士,众爱卿可有异议?”语气当真没有一丝逼迫。
但这时谁敢反驳?皇上已说了此乃天意,若反驳便是逆天而行,是要遭天谴的。
当下群臣跪拜,高呼着:“皇上英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高呼之下,又有多少不满之声。
只段喃一人,面不改色,荣辱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