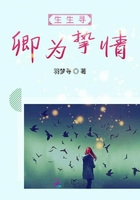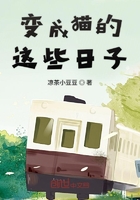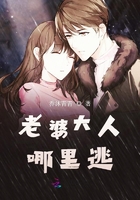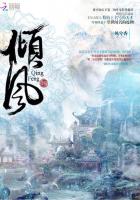一、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亚洲的东部,即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区的一片广阔富饶的陆地上。早在公元前年前,中华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已经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部落集团。据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多处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并表现出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年代,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与夷族、三苗族等开发了黄河流域、东部沿海、长江流域等地区,氐族、羌族、戎族等开发了西北和西部地区,濮族、越族等开发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族、匈奴族等开发了北部地区,肃慎族、东胡族等开发了东北地区。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萌生,促进各民族之间彼此了解的增进、联系的加强,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在国家尚未诞生的时刻,孕育中华民族的沃土上,主要分布着三大集团:处于黄河中游的是华夏集团,有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着名首领;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是东夷集团,有太昊、少昊、蚩尤等着名首领;位于江汉流域及长江以南地区的是苗蛮集团,有头等着名首领。除此之外,黄河上游还聚居着氐羌集团,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则有百越集团等。
大约在公元前年左右,黄帝击败了炎帝,两个兄弟部落进一步融合;黄帝击败了蚩尤,华夏部落集团遂又融合了东夷部落集团。到了尧舜之时,部分苗蛮部落集团被融合进来。经过大禹治水、征服自然与部落战争,终于融合而为华夏族,并且已经拥有九州,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广袤的土地。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族诞生的重要标志。
日益壮大发展的华夏族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不断地拓展疆土,发展经济,增进与其他民族的联系。经过春秋战国年间的人口流动、经济文化交流及各国征战,到秦汉时期,终于出现了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主体民族——汉族,有了共同的语言,还有了统一的共同区域和以农业为基础,使用共同的货币,以城市为中心的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是汉朝和以后朝代的中原人在与周边其他民族接触中逐渐、自然地产生的。它是南方的荆楚、百越等族与华夏族融合的结果,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它具有凝聚核心的作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不断得到巩固加强,成为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各民族之间始终保持各种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依赖,最终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伴随着民族的融合、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华民族逐步成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拥有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各民族都尽力维护民族大家庭的友好与和平,并在共同的劳动中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大厦。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也是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精神,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漫长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民族集合体即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包括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等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数量最多,各民族居住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汉族为主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二、中华文化的成就与有容乃大、百川汇海
中华文化不仅是与印度古代文化、欧洲古代文化、阿拉伯古代文化并列的世界文化体系,而且是世界文明史上影响巨大、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文化系统。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达五千年之久。华夏文明之光不仅驱散了东方的黑暗,使亚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走出文化的荒漠,而且还照亮了西方,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世界上农业发源地之一的中华大地,培育了最早掌握耕稼技术的民族,而几千年来,农业文明也一直是华夏文明的主要特色。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其中璀璨的明珠。中华民族的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农学、数学、天文学、中医学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而纺织、建筑、冶金、车船、印刷等各以特殊的风貌,留下了座座丰碑,在世界上享有美好的声誉。
中华民族的丝绸、瓷器更以其华美瑰丽、精妙绝伦,而风靡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不胜枚举的辉煌成就标志着华夏文明在世界进化史上的显着地位。
中华民族的思想成就、文化创造也同样令世人敬佩。哲学巨子老聃、孔丘、墨翟、孟轲、荀况、韩非等开创的思想流派,以及后世哲学家们共同建构的中华哲学的范畴体系,是中华民族思维特征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华夏文明中发达的辩证思维,重视人类情感的伦理化倾向,以及人文主义的理性精神,这一切都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心态。而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书法、绘画、雕塑等,这些文学艺术的光辉成就自然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凝聚全民族的重要因素,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中华文明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就建筑而言,元代回回人亦黑迭儿丁曾制定了元大都(今北京市)的建筑规划。藏族人民在唐代兴建、清代扩建的布达拉宫,设计和建筑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世界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就天文历法而言,元代回回人扎马鲁丁所着的《万年历》,曾被元朝颁布实行。就文学艺术而言,古代鲜卑族民歌《敕勒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彝族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等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其一定地位。壮族先民创作了花山崖壁画,闻名海外的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是汉族和鲜卑族、吐蕃族等西域各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着名的剑川石窟的石雕,个个都具有浓郁的白蛮、乌蛮等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对华夏文明也贡献良多。中国戏曲的成熟,表现为元杂剧的兴盛,而其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传播于华夏。
华夏文明的璀璨、绵延也证明了它善于吸收外域文化的成果。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文化交往的新篇章。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以佛学为代表的印度文化输入我国,并以“新的理论和思想风貌,反回去就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柳诒徵先生在论述印度文化传入时说:“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及至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艺术也传入中国。明末的徐光启就主张并采纳西方的“济世适用”之学,“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受其成”,“有利于国,何论远近”,“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清初的康熙帝不仅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在学术上也融会中西,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聘用外籍科技人才,在他倡导下编成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是融合中西算学、历法的鸿篇巨制。他在位时由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担负主要任务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测绘工程,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
包容大度,互相学习,相互吸纳,是我们民族的发展规律。
就我们国家而言,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是各民族借迁徙、聚合、战争、贸易等不同形式在交流往来,彼此融合,文化相互吸收中而形成的。就连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也是由不同部族和民族文化融合交流,逐渐演变而成的。华夏族对龙的图腾崇拜,逐渐为南北不同民族所接受,南北许多民族、古老氏族图腾崇拜的驼面、鹿角、虎须、蟒身、鳄鱼爪等都被移植来,塑造到龙的身上。龙的塑造完成,就是不同部族、民族文化不断融合交流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华夏化,华夏族也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文化高峰。东胡族、东夷族、苗族、彝族、氐族、羌族、巴族等许多民族都汇入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具有深远意义的“胡服骑射”,就是华夏族开始大胆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分的一次尝试。具有蛮夷文化背景的老聃、庄周成了华夏文化系统的巨匠。楚文化的集大成者屈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人。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汉族的形成,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使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出现新的高潮。而“五胡十六国”即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个政权,正是黄河流域及巴蜀盆地各民族大融合、大杂居的体现。汉族的南迁,又为它与东南广大地区的东瓯、杨瓯、百越、苗族的接触与融合提供了条件。值得一提的是,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其统治期间,极力消除鲜卑族与汉族的隔阂,任用汉族官员,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为了促进本民族更好地学习汉族文化,他不顾鲜卑族贵族的反对,毅然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以其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采取了十分开明的民族政策。
“贞观之治”不仅是封建政治的翘楚,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在他统治时期,能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强迫他们与汉族杂处通婚,保证少数民族信教自由,给予他们同汉族平等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