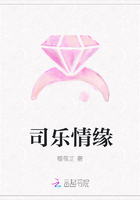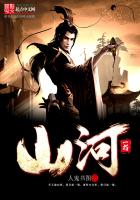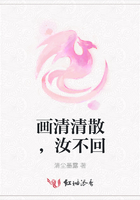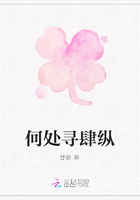中华民族自豪感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有产生、发展,以及达到高潮的历史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又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自豪感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涉及社会科学,还直接与自然科学相联系。
因此要把中华民族自豪感研究透彻,绝非一件易事,在此我们想根据中华民族自豪感产生的历史过程,谈一谈中华民族自豪感产生的几个主要因素,即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以及民族自豪感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同时,也顺带谈一谈中华民族自豪感对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中华民族自豪感的概念
研究中华民族自豪感,应该弄清楚三个基本概念,即“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自豪感”。前文已对“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了详尽讨论和阐述兹不详论。仅对中华民族问题作点小补充。
关于中华民族,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中华民族是个文化共同体,也是历史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多元性”主要指文化的多元,二是“一体性”。“多元性”是指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民族,包括曾经出现,现在已消失的民族;而在今天,则指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显示多元性。“一体”是指共同性,也即归属性,就是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各民族的一种稳定体,共存于统一国家内。
同祖、同根、同文等是“-体性”的主要特征。和“多元性”相比,“一体性”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中华民族自豪感是中华民族融合、内聚和凝结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由地域、语言、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翦伯赞说:“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民族自豪感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核心是国家政权,而它的灵魂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迥异其趣的中华民族精神,而地域等自然因素则是中华民族自豪感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特定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自豪感形成的影响
中国的特定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自豪感的产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早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最早先人就已经劳动、生息和繁殖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之上了。我们中华民族居住的地方,坐落在亚洲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达大沙漠,南至南海诸岛。在这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之上,地势西高而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西南部是海拔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青藏高原往北,往东,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云贵高原东坡,地势明显下降到海拔米(米;再往东,主要是丘陵和平原交错的地区,海拔在米以下。
在西东落差呈三级阶梯的大地上,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生态环境:
有广阔的平原沃野,有众多的江河湖泽,有峰峦高耸、地面崎岖的丘陵,有凹凸不平、形态如锅的盆地各种地形交错分布,给先人们以优越丰润的条件和严峻艰难的环境,中华民族就在这个天生的自然框架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的先民自古以来便孕育出如下几种颇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一是自我中心意识,二是安土重迁意识,三是和衷共济意识,四是反对外来压迫和干扰的意识。
这几种思想意识,就是民族自豪感最初的,也最原始的表现形式。
因此,地理环境的影响对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形成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中国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难以形成,更说不上中华民族自豪感了;如果没有这种地理条件,也难以形成高度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自豪感就失去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和文化底蕴。在形成中华民族自豪感的过程中,地理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三、社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中华民族自豪感形成的因素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我们的先人为了改造自然造福后代而奋斗。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文明程度,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经济在其间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成长发展进程,是与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发展相适应的。
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东亚大陆的华夏族先民,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后,凭借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很早就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定居农业的优越性使他们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别执着的感情,充满了赞美:“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他们对天尊敬如严父,对提供生存基础与财富来源的大地则亲如慈母,所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种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华夏先民养成了一种“固土重迁”的习惯,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之人外,大多数的古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守在土地上,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是不愿脱离故土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因此而受到制约,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社会结构又大大强化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这种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类型与周边的游牧经济和渔猎经济相比较,自有其稳固和安定的优越性。先进的物质文明给各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精神文明,华夏族被推崇为“礼仪之邦”和“深明事物之邦”,历代政治家也把“重农抑商”
(或“重本抑末”)作为发展国家的基本国策,使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相对稳固,国家的统一得到保证,这是形成中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
农业是华夏族形成的经济条件,也是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华夏族及先人最早活动的黄河流域,有着宜于农耕的自然地理条件,肥沃的中原土地,充沛的雨量和可以引之灌溉的河流,使农耕生产成了这一地域内生产活动最好的选择。同时,这一地域的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早从春秋时期起就形成了以“农业立国”的治国思想。农业成为传统的产业,随着统治地域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和农耕技术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历代统治者就十分注意总结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春秋时期,就有了我国第一部养鱼专着《养鱼经》。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着作。元代王桢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着作。在中国历代史书典籍中,大量记载着农业生产的产量、品种、收成、灾害、水利、农具、农耕技术、节令等情况,以及农业生产知识和各种农业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反映出华夏民族是有着悠久而丰富种植业生产经验的农业民族。在长期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的东方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古老的农业经济,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刻苦耐劳,对中国和世界古代物质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成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是中华民族一笔永不枯竭的财富,是形成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形成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升华,尤其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这种表现就更加直接地显现出来。
公元前年,秦国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千秋伟业,这自然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反过来,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制的形成,又影响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开阡陌,废井田”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那么秦的统一,又使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铁制工具的进一步推广,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提高,都标志着封建经济的快速提高。在这一时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这有利于国家赋税的征收,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经济生活是中华民族自豪感的依托,这种基础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在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秦汉时期,统治者为解决戍边兵卒的军粮,在边地实行屯田垦殖。
汉代的屯田多在西北边境。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年),“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为了经营西域,汉武帝时还在宜城、武威、陇西数郡边境屯田。
除征调戍卒耕种垦殖外,也有招募或遣发“犯罪”之徒常居边境从事屯田的。大多数的屯户,即在边境安家置产,落籍立户,成为移民。移民们把内地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边疆,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移民与边境各族人民相互依存,逐渐融合,缩小了边疆与中原的差距。两地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随之得到巩固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时期。曹操为巩固政权,稳固北方的统一,促使成千上方的匈奴人降伏魏廷,将匈奴部众编入户籍,与汉人长期杂居,接受所在郡县地方官吏的管理,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这极大地发展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蜀汉政权平定南中后(南中是汉晋时期对今天的云南地区、贵州地区、四川南部的总称),诸葛亮提倡广开屯田,以牛耕代替锄耕,使当地土着民族“渐出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在西南的彝族、傣族、佤族,景颇族和苗族中,至今仍流传着请葛亮传授种稻、牛耕等先进生产技术的传说。这一时期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曾给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孙吴政权占据江东(即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苏、江西的广大地区)后,对当地的山越百姓,施以暴力命其耕田当兵,或强迫给世家豪族当部曲和佃客,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激起了无数次的起义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