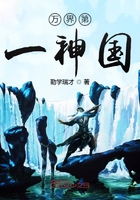在我说完之后,四周围只剩下夜虫的低吟。宁静的夜变得更加寂静,身边的两个男人都陷入了深度沉默,大概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会打出这张牌吧。
好,既然你们无话可说,那我走。
夜风在我耳旁刮起呼呼风声,凉凉的空气渗进我每一寸肌肤。我横冲直撞一路向前,没有人叫住我,也没有人拉我,我就这么冲到了小公寓里。
“怎么风风火火的?不是又出什么事了吧?”戴着眼镜盘腿坐在沙发上加班的霍如珺抬眼看了看我,担忧地问。
我把包甩在沙发上,然后呈大字形躺下去,“太多事了,不知道从哪说起。”
我抬手揉自己的太阳穴,感觉脑袋几乎濒临爆炸。
这晚我有预感自己会做恶梦,所以洗完澡后就爬上了霍如珺的床,要求跟她同睡。
半夜,我梦见自己走到了一个悬崖边,脚下是万丈深渊和湍急的流水,而我想也没想,一步没停地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地心引力让我重重下跌,那种失重的漂浮感让我从梦中惊醒。
醒来时满身大汗,而窗外天才蒙蒙亮。
没有了睡意的我毅然决定爬起来上班,但从我刷牙起,右眼皮就一直跳。
学医出身的人很难去相信这世界上有妖魔鬼怪之类的存在,左眼跳喜、右眼跳灾这种话平时也我们医学生之间也只被当成迷信似的笑谈,偏偏今天我反常地被这跳个不停的右眼皮影响了心情,早上出门还差点和一个骑单车的老大爷撞上。
到医院后,我换了衣服开始巡诊,结果一大早就碰上子宫肌瘤破裂出血的病患,惊得面色虚白地赶紧把人送到抢救室,然后因为没吃早餐而低血糖,导致丢脸地在手术台边出现“晕台”的情况,差点没被江姐的白眼给瞪死。
江姐从手术台上下来对着我就是一顿狠批,挨完训后我还被罚手抄住院医师职责。回到值班室里时,韦萱给我递了块巧克力,“江姐更年期嘛,你别跟她计较。要开心。”
我嚼着韦萱给的巧克力抄资料,右眼皮越跳越凶。
难道今天要出什么大事吗?
这种状态维持到了下午,午休后我洗了个脸准备打起精神上班,意外地接到了妈妈打给我的电话。
“小芸啊,今晚要加班吗?”
“还不确定……妈妈你怎么问起这个?”我很惊讶,并且迅速地猜测妈妈人在A市。
可是她怎么会突然过来呢?
尽管换了心脏,但妈妈的身体还是不能跟平常人一样对待。她跟舅舅一起住在毗邻A市的小县城里,替舅舅的生物实验小花园做日常打理的事务,过着安静而与世无争的生活。每次妈妈要来A市看我之前都会提前通知,这样方便我和舅舅两边安排时间。
“妈妈,你在A市吗?”
“是啊,你舅舅来A理工大学作报告,我就跟着过来了。”妈妈的声音和以往一样清亮,保持着她以前在剧团的面貌和风情,“要是你晚上不加班,我和你舅舅就来接你下班。”
我莫名慌张了一天的心被妈妈的几句话所抚慰,趋渐平静,暗暗欢喜,“那我先去忙,一会儿确认了要不要加班,再给你打电话。”
“好。”
我还没有挂掉跟妈妈的这通电话,就听到手机提示有另一通来电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