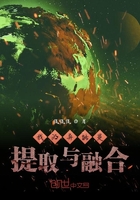教学占用了吴冠中大部分宝贵的时光,他的创作只能是“业余”的了。每年的寒、暑假都是集中力量拼搏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画具“走江湖”,从北京到海南,从山东到西藏,从茫茫戈壁到西双版纳,祖国辽阔的大地,留下他艰难而又兴奋的足迹。这个行当,被人们称为“旅行写生”或“游山玩水”,但他却极不赞成这种提法,因为那艰苦的跋涉和艺术劳动实在是丝毫也不轻松的。他住过大车店、渔村、工棚、破庙,在深山老林甚至连投宿都十分困难,随遇而安,只要有好题材画,能在老乡家落脚也就十分欣幸了。他不修边幅,穿得破衣烂衫,又背着那么多“家什”,往往被老乡截住问:“修不修雨伞?”“收不收鸡蛋?”他在作画的时候,全神贯注,饿虎扑食,正如梵·高所说的那样:“当手指握住了画笔便像琴弓触上了琴弦”,他把一切都忘了,甚至可以连续工作一整天不吃不喝,有时中间勉强吃一个冷馒头,反而要闹消化不良。他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营地时边走边啃,吃得很舒服,赛过“西太后的窝窝头”。一次,他在写生时,有一位老乡从旁边走过;待日暮时又从这儿返回,见他还在画,就忍不住递过一块干粮说:“你饿了吧?吃一点!”这位老乡一定是把他看做“苦行僧”了。吴冠中曾经在一位朋友为他画的写生像上题诗,这诗说尽了“旅行写生”的甘苦,简直可以当做他的“自画像”来读:
山高海深人瘦,饮食无时学走兽。
感君相随更相助,夜来和衣席地卧。
缘底事?顶恶风,甘共苦,
天地彩色笔底浓,身家性命画图中。
1959年酷热的夏天,吴冠中利用暑假自费去海南写生。背着数十公斤的油画颜料和画具,坐硬座车先到广州。火车晚点,抵广州已是夜里十点多钟。站上排着好几条长长的队伍,他两肩背着、双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一步一挪地跟在队尾,等待登记旅店。饥渴,劳累,炎热,急躁。他弄不清队首的情况,只好频繁地向别人打听。听不懂广东话,人家给他比划了又比划,也不得要领。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看见了队首,原来是卖西瓜的,弄错了!于是重新排入登记旅店的队,再排乘坐三轮车的队。乃至抵达遥远的一家旅店,已是次日凌晨……
到了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管理处一看他的介绍信,是艺术学院开来的,便安排他住高级招待所,干净、漂亮,带套间。吴冠中心想:糟了,我要在这里写生一个月,可付不起高昂的房费!于是要求换个地方,人家倒客气得不得了,说:“这套房间是专门为贵客准备的,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是大艺术家,住别的房间太屈尊了!”吴冠中有苦难言,这位同志哥好热心,只是不知道他所尊重的“大艺术家”的寒酸。吴冠中不好意思明说,便借口说:“我画起画来油画颜料弄得一塌糊涂,万一弄到沙发、地毯上,洗都洗不掉!还是换个随便点的地方吧?”好说歹说,总算搬到了住上下铺的职工宿舍,每天只付几毛钱,这才心安理得了。
一个月过去,他再取道返广州回北京时,行李又大大地加重了,大包小包都是在海南写生的油画,画在三合板上,油色还未干透,画与画之间留有空隙,千万不可重压,万一粘在一起,一个月的劳动就白费了。上火车先找放画的地方,但行李架上已经重重叠叠,再无插针之地,无可奈何,只好把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还不放心,就一路站在旁边,扶着。从广州到北京,几千里的路程,他就这样站着、扶着,小心伺候着他的作品。旁边乘车的旅客直纳闷儿:这个人真怪,那些大包小包里是什么宝贝啊?咳,宝贝,那确是比身家性命还要贵重的宝贝啊!吴冠中说:“劳动成果是可观、可叹、可喜、可泣的!”这是母亲对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亲生婴儿那样的感情!油画平安无恙地到家了,他的一双腿都站肿了!
“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有出息的画家都渴望到生活中去……高僧玄奘为取真经而献身的精神永远教育着我们,华夏子孙为探索艺术真谛而视苦为乐者正大有人在!”吴冠中尽管经历了无数坎坷,但始终没有动摇“生活是艺术惟一的源泉”这一信念,辛勤地在人民生活的土地上开掘、耕耘,无论寒暑,不分昼夜。然而,他又绝不满足于照抄生活、复制生活,在文艺界上空阴晴无定的气候中,他默默地一只能是默默地进行着早已酝酿在胸中的一项探索:油画的民族化。他的感情是乡土培育的,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情思,挖掘出来的形式美感的意境便往往是带泥土气息的,油画这种外来艺术种类也就必然打上我们民族的印记。“民族化”不是强迫油画“适应”我们的民族形式,那是生搬硬套,不是“化”。“化”是水乳交融,变为自己的血肉。不“化”,油画始终是金发碧眼的客人,不能在此立足。走别人的老路,省鞋,省力,但没有出息。西方现代艺术中交流着东方的血液,而南朝张僧繇的“凹凸法”被认为受孕于西方,谁也说不清混血儿最早诞生于东方还是西方。有东方父亲和西方母亲的混血儿,也有西方父亲和东方母亲的混血儿。混血儿多半漂亮、聪明,集中了西方的形与质,东方的神与韵。这便是“化”,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不少画家在探索两者的结合,培育“混血儿”。梵·高和马蒂斯作品中汲取了东方的韵律感,是西、中结合的成功经验。吴冠中恰恰是从这一经验中引发了中、西结合之路,中国人画西洋画,不是去取宠于西方,而是将他们艺术中的精华提炼、加工,注人自己的肌体,以东方的神韵给“混血儿”缔造新的灵魂和外貌。他的这一主张,到80年代已经获得中国美术界普遍的赞同,但在五六十年代,却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有悖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老牌正宗”的油画画风,因而也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吴冠中执著地然而又是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路。“我无法考虑为五百年后的观众作画,我只能表达我今天的感受,我采取我所掌握和理解的一切手段,我依然在汲取西方现代的形式感,我同样汲取传统的或民间的形式感,在追求此时此地的我的忠实感受的前提下,我的画面是绝不会相同于西方任何流派的。”
这是一条险道,也是一条寂寞之道。“名家,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也有欺世盗名的。倒是不少有杰出成就者默默无闻,往往等三十、五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被人们发现。是群众暂时不理解吧?也许。既然有大量的吹捧,群众便容易崇拜一时显赫的‘名家’、得宠的名家……显赫的名家的威势遮掩了人们的耳目”“风格无处借,它是树,是从幼苗成长的,它长期吸收雨露阳光的滋养,屡经风雪的摧残。不是所有的树苗都能长成大树的,更不可能在数日、数月,或三五年内便长成大树,这是艺术规律,也是生命的规律。”
一个多么自信的人!信念和毅力正如郑板桥的一首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1966年,吴冠中四十七岁,正处于人生和艺术的旺盛期、成熟期,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浩劫使全国大乱,艺术事业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陷于灭顶之灾。吴冠中的恩师林风眠和潘天寿都受到了严酷的批判和肉体摧残,潘天寿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曾经“收容”吴冠中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以及早年曾是杭州艺专的教授、后任工艺美院副院长的雷圭元、庞熏琹都被打成了“黑帮”,和他一起从艺术学院转来的卫天霖被诬陷为“文化汉奸”,他的另外一些师长和好友如刘开渠、李可染、董希文、罗工柳、彦涵、石鲁等人也都统统被“打倒”,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之后,再一次“殊途同归”,都进了“牛棚”。所幸的是吴冠中从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当时也还未处于“权威”的地位,因而没有享受最“高级”的牛棚待遇,免受了戴高帽游街、皮带加拳脚的皮肉之苦,但精神上的虐待也足够一个艺术家领受的了。“大批判”混战之后,他和学院的教师、学生一起下放到解放军驻河北获鹿县的某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住在老乡的家里,睡土炕,每天往返于村庄与田间,面向黄土、背朝青天。谈不上艺术了,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他成了一位老农一一比老农还要多一份精神枷锁。但是,在这里,他却似乎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农民的儿子复归为农民,这正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失意时所走的路,周而复始,返璞归真。这里没有故乡江南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和乌篷船,只有黄色的土墙、黄色的泥顶、黄色的土路,是名副其实的黄土地。不要以为黄土地单调、枯燥、不人画,当你住下来,成了“乡下人”,亲自尝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儿,便像主人一样爱上了它,很美呢!土墙泥顶的农居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燕子飞来,呢呢喃喃呼唤着春天,呼唤着人们心灵的憧憬与向往,又何尝不是置身于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村姑,赤膊的汉子,叼着旱烟袋的老汉……这纯朴的乡情、浓郁的色调,倒是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苦苦争春,顽强地表现自己。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意欲一展色相、一吐芳香,又被人任意践踏!
乡间的土路旁,一位头戴草帽、面色黧黑的“老农”叹息着俯下身,扶起被人踏伏的小草,捡起刚刚开放便拦腰折断的野菊花,那被碾压成泥的花瓣溢出紫色的汁液,仿佛在滴血!一个灵感、一种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向他袭来,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下乡之前甚至都不允许带画笔!吴冠中不禁想起当年告辞巴黎、执意东归,难道就是为了这种下场吗?留在巴黎的同学好友,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耕耘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羡慕吧,妒嫉吧,痛哭吧!
过度的劳累使吴冠中的涛病严重了,连走路都困难,下地劳动、插秧、送肥更加难于胜任。感谢好心的领导的照顾,让他留在村子里的副业组养鸡鸭。吴冠中受宠若惊,伺候鸡鸭格外小心,兢兢业业,不敢怠慢。
谁料祸起萧墙,一只黄毛乳鸭突然死了!这件事如果出在贫下中农身上,鸡毛蒜皮而已,但他这个牧鸭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又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便复杂了,有人说是他心怀不满,用打死鸭子来进行“阶级报复”。于是解剖小鸭,说内脏无病,只有骨头是青色的,证明是遭打致死。指导员根据“立场坚定”者的汇报,要吴冠中向群众检査交代打死鸭子的“思想根源”。天哪!一位热爱生命的艺术家,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于这只黄毛乳鸭?他还是托了这批鸭子的“荫庇”才谋到了这份比较省力的差事呢!但是,他现在纵使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像他这样“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任何解释只能是“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他索性一言不发,听凭处置,反正一个“鸭司令”也不怕革职。指导员发火了,说要在第二天发动全连对吴冠中进行“批判斗争”。
这一夜,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吴冠中哭了。睡在同一炕上的学生劝慰他,他望着心爱的学生,发出郁郁不平的愤懑:“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简直是《十五贯》!”第二天,这位学生在劳动中议论此事,抱打不平:“吴先生说得一点不错,就是《十五贯》!”那时节,打小报告是极其盛行又极其可怕的,这私下的议论很快便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马上传话:叫吴冠中到连部!
可怜“鸭司令”不知内情,还以为指导员自省昨天的武断与粗暴,要向他道歉呢。到了连部,才发觉气氛不对,指导员的火气比昨天更旺,声色俱厉地责问:“你在下边散布了什么不满言论?”
吴冠中愕然,实在想不起所指何事。指导员盛怒之下卷起了衣袖:“老子上了《水浒传》了!”
吴冠中更加摸不着头脑。指导员见他不开窍,又补充说:“《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只有你聪明,我没有看过吗?”
吴冠中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使他觉得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这是一个哭笑不得的荒唐年代,连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都做不到了!
……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局势已经有所好转,“不准画画”的禁令稍稍放开,允许在星期日“搞点业务”了。九死未悔的艺术家又心痒痒、手痒痒了。吴冠中托人从北京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就地取材,从乡村小店里买到了马粪纸小黑板,原是供田头学习《毛主席语录》用的,太多了,积压在商店,正好买来挪作他用。上面刷一层胶,就代替了画布。那么画架呢?老乡家的粪筐,有高高的背把儿,既便于携带,又可作画板的支架,筐里装颜料、画笔、调色板。吴冠中背起了这独创的、新式的画具,在黄土地上又开始“走江湖”了。学生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粪筐画家”。其实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很快便群起效仿,每逢星期日,就纷纷背筐出门了,于是形成了“粪筐画派”,吴冠中是创始人,“领导新潮流”!
每个星期,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的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又全靠晚饭后那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犹如在押犯的“放风”,多么珍贵啊!吴冠中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画麦田、稻田,画红高粱,画农家小院、石榴花,画向日葵,画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切。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他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绿色世界,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他天天在瓜地里寻寻觅觅,不知是在寻找什么贵重的东西,许是手表啊,钢笔啊……“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倒是没怀疑他偷瓜,他自己也忘了“瓜田李下”应该避嫌。纯朴的乡亲啊,他怎么向你们解释呢?他丢掉的太多了,那是他几年的生命,他最宝贵的艺术事业,他们能帮他找回来吗?
古长城脚下,是当年杨家将战斗的最前线,已是“番邦”的边境了,故名“番字碑”。纵目长城,抚摸番碑,古战场触动了吴冠中对国土山河与古代英雄的无限情怀,赤心报国的中华儿女,为什么总是这么艰难!
1972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好不容易请了探亲假,前往贵阳探望病中的岳母。老人的病使他们焦急,但能够借此“自由活动”几天,又有说不出的欣喜,犹如飞出了笼子的鸟儿。他们从石家庄出发,途经“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吴冠中忍不住了,中途下车,废寝忘食地作画,一连画了几天,才恋恋不舍地重新登程,前往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