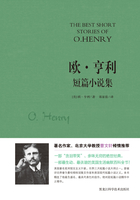“阿恺,下星期月考,你准备得怎么样了?”景恺的背吸引力过强,专对背后之人开放,且他的背影仿佛散发着罗伯特·巴乔的忧郁气息,是女人都会忍不住轻拍一下。景恺的背被他人的手偷袭得麻木了,机械般转过身去。景恺一看,又是一位美女,半天之内,景恺巧遇三位美女。吓得他自以为世上的丑女都自卑地去见上帝了。
景恺于是道:“也就这样喽!你呢?”
“还行吧!只是要考9门科目,想到都怕。”景恺笑着同她示和,便转身复习去了。
又至周末,顾父同样不在家,一张百元大钞被他抛弃在了茶几上。景恺拾起他的施舍,未有片刻犹豫,直奔网吧。
路上不巧,景恺人缘太好,以至于无缘无故就撞见杨鸿、姚健二人。一问之下才知二君也欲通宵。杨鸿一见景恺,搜刮之心四溅,开始上次未献完的身,搂着景恺,道:“恺大哥,我家经济比较落后,等下上网你就多照顾一下啊!”想这家伙要钱的方式可真与古时的鸨母有得一比。可至少后者能有窑姐陪你,前者收了钱,霸王餐反客为主,连句情话都不给,劫钱又劫色,这才谓人财两空。景恺可怜他的智商投错了胎,只好勉强答应。
窑姐没陪成倒赔给了刺猬男。当然,能为人与动物间的和谐作出此等牺牲,景恺之钱花不足惜。不过倒霉了他的耳净,整晚都被“B哥”萦绕着。
次日清晨,三人肩搭着肩搀扶着回景恺家。一路上,景恺才了解到他俩家住乡下,故意骗家人在校留宿而跑出来上网。景恺嘴上给予此二人儒家思想,可心里却排斥这古老的中国观念:当今时代,没点背叛,哪叫生活。没点叛逆,那叫白活。尤其是作为男人,不从背叛提升到背离那就枉对男人。不从叛逆升华到叛性那就枉对女人。所以,既为了男人又为了女人,三个叛贼就这样给自己判了刑。
回到家后三人倒地而睡,醒来时已是明月当空。景恺禁不住天气的诱导,不禁地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得客厅门开。那一瞬间景恺的回忆一概停留在父亲的暴力中,可这毕竟在现实中是未来的想像,未想而已。顾父不见,杨姚二人拎着一些食物回来。
杨鸿边嚼着手中的薯片边把嚼完后的能量用人话的形式表现出来:“B哥!醒来了啊!我们买了东西吃。”
景恺看着杨鸿这退化成蛔虫的作息方式十分不解,干脆将其打回原形,问:“你们两个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哪来的钱?”
那蛔虫现形坐到沙发上蜷成一团,盘笑着说:“这是我们俩扣伙食费的成果,反正最后有人报销嘛!”说时他用眼瞅了一下姚健。
姚健接到指示,定位十分:“阿恺!钱这个东西嘛……。”
“行了,行了,多少钱?我出!”
杨鸿一听到“钱”字,便不让姚健当马仔,亲自出马,马出狂言:“五十一!”
景恺一听,差点没把他打回马厩。叫道:“杨鸿,你也太大牌了吧!五十一哎!我一星期一半的伙食费!”
杨鸿一听此价卖不出去,恨不能学超市经营,概不还价,只好委屈地像开小卖部,能抠则抠,道:“那四十好了,剩下的我们两出。B哥,可怜一下吧!”
景恺见他那衰样,不忍心再多看一眼这世上最殂动人心的面相,便摆摆手还他一副尊容,道:“行了,行了。我出了!”杨鸿一听,一连声“B哥”拍得景恺已分不清自己前世是马是人。
第二日清晨三人回到学校,良心还未能将他们遣责到发奋读书的地步,三人也就无所事事。
人生如梦,只是由于钱包失血过多,早餐便被景恺在进食的名单中略去。胃瘪得只能与肚子亲密地耳鬓厮磨。
上午考语文,景恺的肚子无地呻吟,只能在考试中肆乱抱怨找不到知己。但脑子不与它沆瀣一气,懂得“故天降大任于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道理。它胃人师表,最后终于胃命是从,完成应试语文统一大业。
三天的考试闷得快要被这热天给蒸发掉。他人选择在这闷热中爆发,景恺则在这爆发中消亡,静静地等候时间留给自己的沉默。考试间,景恺因受到网络游戏持久性的影响,脑中思考已分不清问题和答案。总之,是问题那肯定是网络问题。或答案,那必然是虚幻答案。所以说,网络一无百用是废话,说它百无一用那是屁话。至少它能邂逅现实与虚拟,这便是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的最大不同。
好不容易挨到学校放的两天假,景恺找不到朋友,他那嘴巴恨主人没有人缘,气得两天未开口说话。眼睛更恨景恺没有女人缘,得不到养眼的它恨不得跨过鼻子的封锁线去和嘴巴做知己。嘴巴更恨不得一口吃掉鼻子,去和眼睛叙说苦衷。
“哎,B哥!B哥……”
“呃,怎么了?”景恺竟没想到这回忆亦能载入史册,随时从思册翻便能觅出其身影。
“你紧张吗?明天就要发试卷了?”
景恺对杨鸿的紧张无所顾忌,道:“紧张如果能多加几分,我倒愿意,可惜这不是做梦。”
“真不愧是B哥!真够牛B的,那你跟我说说你以前的光荣事迹吧!”他满脸的好奇取代了他好学行使的职能。
“好汉不提当年勇,说了有什么意思?”景恺这口是心非的造就不及成熟,但对付杨鸿这种生物却是绰绰有余。
前张桌的姚健也扭过头来与杨鸿同流合污,对低能生物情有独钟,说:“你就说下吧!让我们见识见识!”
“就是,咱们兄弟之间还讲什么好汉不好汉的,我说你是好汉你就是。”杨鸿这一说,把景恺也给扯进了智障的行列。无奈,都是同类生物,还有何不可讲。景恺只好在明日或说末日来临前风光一回。好比一个罪孽深重的坏人临近死期,明知道自己要入地狱,反正是一死,不若在死之前来个痛快点的,将自己生平高德的善事公诸于世,以此乞求死后能安息长眠。于是,景恺便开始了死亡之叙:“初一的时候,我从广州转学回到家乡,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我在校征文比赛获得一等奖,我于是一炮而红。接着我又被北京世教中心邀请,可惜被我拒绝了。”
“啊!为什么要拒绝?”景恺眼珠一瞪,杨鸿那张嘴便被一切尽在眼中所堵。
“由于我在广州受过华南理工大学英语教授的专门辅导,三年英语的底子好。在一次校听力竞赛中我又夺得第一。接着我的成绩便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从班上倒数第二一直稳升至年级前五。”说着景恺又瞄向杨鸿一眼,看他有无要言的冲动,得到否定后景恺又继续:“校运会时,我又崭露头角,还有我的书法和绘画也一度扬名。我的声望在学校迅速走红。上了初二我患上网瘾,经常逃课上网。尽管如此,我的学习依然保持在班级前茅,所以众多老师也拿我无可奈何。”
“哇!B哥!你天才啊!”姚健受到景恺眉目传情的启发,也对着杨鸿东施效颦,结果被杨鸿反送秋波,景恺被他们眉来眼去的传情惹恼,突出眼睛的局限,扩大战略范围冲出一句:“继续讲,讲大声点。”顿时这场面违背了景恺的话语变得安静起来。
景恺将自己生平大多功绩都贡献出去,而自己小小成就在汪洋回忆中不值一提,干脆残留给自己回忆。杨鸿见景恺未提感情方面的造就,像是每个伟大的男人都要有毛泽东的风流,才够称伟人,于是问:“B哥,当时有没有女生跟你好过?”
景恺为了不再做被告,只好不可奉告:“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好了,我要学习了!”说罢,景恺立即翻出几本资料晃过二人。二人也知情趣,自知原告做不了,一个继续倒头睡觉,一个扭头装睡……。
今晚的景恺很是高兴,因为总算有人能知自己的光辉事迹了。当然,这只是死前的陪葬品,景恺知道,明天他会为死而更高兴的……
第二天发试卷,当景恺拿到化学试卷时,脸已经被灰烬所埋,所以说面如死灰。杨鸿眼疾手快一把抢过他的试卷,用手遮住分数,学古人从右往左一一逐开惊喜。
“9、5、哇!B哥,你159分啊!牛B啊!”杨鸿篡夺时间席位把景恺的脸定名为面如逝灰。姚健被惊抢过试卷,一看,诚实说出:“你白痴啊!总分才150,怎么可能化学满分还超出9分!最后一个数都没看完就胡说,又没睡醒啊!”
杨鸿的智障权被侵,法律却没明文规定这类行为犯法,自然很不服气,说:“你多少分。熊什么熊!”
“比59多得多,我再怎么考也不会考B哥这么点。”显然,姚健要贬的不是分数,弦外之贬骂的是这分数的缔造者。景恺的情绪默不在意,想当年刘易斯破纪录时也诽谤万千,何况自己这个纪录非世界级别。这样一想,景恺的分数与心数间便平衡多了。
正当景恺的心绪被稳定在木板的一端时,一个熟悉的女生打断了这平静。“景恺,你化学多少分?”景恺在失落的废墟上抬头一看,不朽的希望全让杨雨馨张开的大口吃掉。这时颜丽华和其他几个同学也走来踩在翘板的另一头。
“我——”景恺对自己的分数打不了保票,这天平板严重失衡,景恺的失落被一群无知者顶到了极端。
“好了,好了,B哥今天心情不好,你们有事明天再来吧!”景恺高处一望,是杨鸿做了救世主。只见他一一劝说一帮女生,一边把自己从至高点扶下来。景恺感激不尽,却又不好刻意盗用他人献身主义,只好将这主义藏于心中缓缓品读。
试卷接二连三地被现实接受。景恺的个人纪录没有经验,结果没能保持多久,被后来居上者一一逐新,化学一科只得聊以自慰。可惜了英语对同仁略有怜惜,考了个七十问鼎倒数。景恺此时不知该喜该悲,或许该喜该悲。不幸的是,老天被景恺相中,被他在心中默默地将上天做与肉体性欲了一番,最终成为景恺自我安慰成绩的罪魁祸首。
大概是上天对景恺施以报复,景恺这成绩也不甘落后,硬是在一批积极分子的宣传下发展为全班纪录。这下可好,这纪录一被公布从有人问津质变到无人问鼎。景恺托成绩的鸿福,在班上居下临高,无人压敌。当晚便被班主任赦以特权,把他叫到办公室进行专题采访。也亏得韩老教语文,连做访谈的基本都被他捏造,答问全为他一张嘴所设。似乎做记者的核心内容就是未卜先知。不过韩老的卦算得不赖,连景恺的网络遨游事迹他也能算出。最后进入逢凶化吉一章,给景恺开下“不准去网吧”,“不准上通宵”,“不准谈恋爱”等诸多处方。罗嗦一大堆,主旨无非是把《宪法》的条文厚脸皮地搬到《校法》上缩小化加以阐明。景恺从来不搞迷信,自然对其约法也视为草芥。
一回到班,顿时众望景恺。景恺的脸早在韩老那儿给训得厚颜无耻。如今应对实战,已是镇定自若,神色不动。任凭他人眼中啧啧。从这以后,景恺再也不敢正眼看雪萍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班上七、八个男生为缓解月考压力——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说法,实际说法应是月考为缓解班上七、八个男生的压力。决定这周末晚去网吧上通宵。这谎言对景恺似有留恋之情,景恺对其也爱不释口,打电话给父亲谎言自己月考成绩不佳,要在校留宿学习。顾父经商倒亏,被欺诈了一回。景恺挂下电话后,愧疚万分,但那愧疚就像个报了杀父之仇的人,再怎么愧疚,也仅对他人而言,触及不到自己的良心。
好不容易挨到周六,上午照常上课,景恺照常被精神统治,下午刚回家,顾父的钱被主人习惯性地抛弃在桌。有其父必有其子,景恺效仿顾父慷慨之举拿起钞票就走,这忘恩负义首次被落实于钱上,也只能怪这钱生得时乖运蹇。
一日三时只剩晚上,似乎这夜晚才配得上行动二字,那按压轴的说法,在夜晚行动的人皆称英雄,因为英雄都是晚一步出场。景恺一直抱怨时间没有朱自清《匆匆》的风格,值日老师甘做第一任英雄缓缓执行了所谓的登名记录。景恺对这迟到的英雄一无好感,直奔校门后才找回些时光飞逝的感觉。那门卫给中国的教育家做了次代表,对学生的光明视若无睹,连询名都懒得牵动嘴边肌肉。由此看来,中国真正的教育只是个自私的团体,从不满足大众需求,一意孤行是它的原则,一腔热血是它的抱负,一无是处则是它的内涵。
景恺走在去网吧的路上,脚虽一直埋怨中国城市规划得不协调,但能踩在中国教育的头上,这心也就有消遣的余地。十分钟的践踏,景恺总算在娱乐功能区找到眉目了。众兄弟的心里在网络基地驻扎已久。见景恺来,好不自胜,拉他一起入伙。景恺一高兴,大发军饷,准备今夜奋战,通宵达旦。
正当鏖战间,景恺突然祸起萧墙,被他人后“捅一刀”,景恺不知究竟,一往后看,是此次战争的领导者,易文雄。只见易文雄对他斥道:“小顾,你有麻烦了!”
“怎么了?”
“你是不是登记了留宿?”
“是!”景恺心跳不安,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易文雄这话在无意中又捅了自己一刀。
“在熄灯查房时,教官见你人不在,现在值日老师、班主任还有好多老师都出来找你了。这是我们班同学刚给我电话说的。你赶快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易文雄说着,像终于把刀给拔了出来,可景恺的心在这自相鱼肉后已经彻底死了。
易文雄倒有领导风范,临危不乱,振振有辞,最后把景恺也给辞了。
景恺立刻慌了神,易文雄也开始行动,收编部队,把这消息告诉了在座的诸兄弟。景恺的心被震得像拉空的弓,还没上箭已被开弓,后果可想而知。
最后的局面被景恺统筹,因为被统筹的只有他一人。那些自称兄弟的人早已让畏惧赶跑了。就这样,景恺单枪匹马开始了这场叛军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