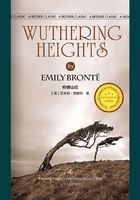由于朱海波的残废,朱全良不得不重新学习,学习如何养好鱼塘的鱼,他开始看那些关于养殖方面的书:《鱼类学》《池塘养鱼》《鱼病防治》《淡水生物学》等。由于陌生,朱全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眼睛还好,还能看清楚书上的字,养鱼看似简单,却有很多学问,要保证过冬的鱼不会死,赶到春天卖个好价,就这样,朱全良边看书边学习琢磨。
夫妻俩一边养鱼,一边照顾残废的儿子。由于上次詹雨桐的疏忽,所以她不敢再怠慢。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翻身,詹雨桐掌握好一定的时间,每天推朱海波出来晒晒太阳。朱全良也跟着孙喜宝学习喂鱼、配饲料、抽水、开增氧机、割塘边的草、观察鱼的习性、测量水温、检测塘里的水质,朱全良是一个会计师,现在又涉足一个新的行业,他仿佛从一座山上下来,再从山脚下爬向另一座山。鱼塘的东面有一条排水沟,沟里长满了水生植物。到了周末,钓鱼的人从城里来了,在排水沟里钓鱼,钓上来的鱼很小。他跟那些钓鱼的人聊天,知道他们都是退休老干部,闲的没事,在乡下钓钓鱼,消遣消遣,他们都有退休工资,而朱全良却没有。
由于最近的忙碌,詹雨桐和朱全良打算带着朱海波去山里玩一玩,放松放松,开车的是马建国,马建国开的是一辆旅行面包车,那辆车很宽敞,他们把朱海波连人带轮椅一块抬到车上,用带子把朱海波绑在轮椅上,又用绳子将轮椅固定在座位的一侧,汉斯菲尔德也上了车,孙喜宝留在家里照顾鱼塘。马建国开车开得很稳,他们走的是北二环。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新修的马路都是八车道,双向行驶。路两边的几个淡水湖已经将这个城市连接起来,这座城市已经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房地产正飞速发展,新修的公园集休闲、健身、购物、游玩为一体,沿途经过了民运村、国际会展中心、博物馆、图书馆、森林公园等,马建国解释这些建筑都是这几年新建的。他们去了苏峪口,朱全良怕朱海波着凉,转了会便开车返城了,在公园西边的餐厅吃了一顿饭就回家了,回到鱼塘时天已经黑了。
詹雨桐对朱海波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她都推着轮椅带朱海波出来晒太阳,朱海波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他的听觉已经退化了,除了汉斯菲尔德的叫声,他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但他每日都能看到从云层里钻出的太阳,能看见池塘后面被风吹得沙沙响的芦苇,塘堤上忙忙碌碌的蚂蚁,塘面上漂着海藻形成的水花。这一切,是詹雨桐的功劳,是她坚持每天推朱海波出来晒太阳。
一天,孙喜宝被朱全良叫了去,朱全良要将孙喜宝解雇,詹雨桐却执意不肯解雇孙喜宝,那天,他们吵了起来。詹雨桐说:“垂钓项目马上要实施了,正需要人手,眼前的困难可以克服。如果垂钓项目做好了,收入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在需要人手的时候把孙喜宝解雇了,不但垂钓项目搞不好,还有倒闭的可能。”
“再说了,你对养鱼、喂鱼、鱼塘的突发事件都不会处理,五六十亩水面,我们两口子怎么能顾得过来?”
碍于詹雨桐说的有些道理,孙喜宝被勉强留了下来继续帮忙。朱全良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什么,觉察到詹雨桐和孙喜宝之间的暧昧关系。
垂钓项目终于落成了,他们接待了第一批来池塘垂钓的客人,他们是三个退休的老警察,他们穿着休闲服,其中的一个还戴着墨镜,他的眼睛是沙眼,那天正好刮着西北风,孙喜宝将三个马扎摆在塘边,树立起三个遮阳伞,那三个警察钓了整整一个上午,由于天气不太好,又在刮风,塘里的水面还荡起了波纹,刚刚放进塘里的鱼都躲在角落里,上钩率不高,两个警察每人钓了一条,另一个警察什么也没有钓到,朱全良按最低标准收了费。到了饭点,由于朱全良的推荐,三个警察在雅间里吃了一顿农家饭,是朱全良做的:四个小凉菜、一个莲花鱼、一个红烧鸭子,三个人还喝了一瓶老白干。由于朱全良服务周到,他们说还会选一个好天气再来鱼塘钓鱼,吃同样的菜,还留了朱全良的电话,说来时会给他打电话。
冬天来了,朱全良再一次提出要解雇孙喜宝。他真的发现了什么,觉察到了他们之间的缓味关系或者生活中的某个细节,有时朱全良到镇上的集市买东西也要让孙喜宝一同去,为的就是不愿意把詹雨桐和孙喜宝单独留在家里。朱全良又一次说到解雇孙喜宝。
“如果你说的还是那件事,就免谈!”詹雨桐说。
“没见过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你知道人家孙喜宝帮过我们多少忙,鱼塘的重活脏活他干遍了,从未叫过一声苦,是谁将一车车饲料一袋袋搬进饲料房,是谁一天将三顿饲料喂给鱼吃,是谁将塘里冰层厚厚的积雪扫干净,是谁将塘边的草割得整整齐齐,是谁在清塘时用捞网将泥水里的鱼捞干净,剩下的我就不说了,你掂量着看。我知道你总是看他不顺眼,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咱们多难,现在稍好些了咱不能过河拆桥。郑来香死了,现在你让孙喜宝带着孙斌住哪儿去啊?”
朱全良不做声了,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