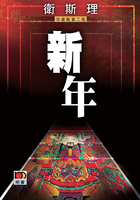那辆车拐弯时,詹雨桐的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她看见一个警察在马路中间维持交通秩序。警察穿着新式制服,手上戴着白手套,打着手势示意詹雨桐靠边行驶。不远处一辆出租车追了客货车的尾,撞击的碎片散落在马路上。前面的客货车将一个过路的小黑犬撞死了,狗的遗骸躺在前轮子不远处,因为急刹车前面的车被后面的车追了尾,事故处理车停在路中央,另外两个警察用长卷尺在丈量刹车痕迹。詹雨桐把车开进小区的停车场,车位全停满了,她进退两难,前面靠近垃圾处理站有一小块空地,她把车停在那片空地上,锁了车。她老远就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门口蹦着跳着,跟一只白色的幼犬玩耍,他上身穿一件黄色短袖衫,下身穿蓝色短裤,脚穿一双旅游鞋,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他手里还攥着半根黄瓜,他是小区保安的儿子。詹雨桐跟这孩子说话时,从里面出来一个保安,他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詹雨桐向小区里面走去。通向小区的那条小巷也成了詹雨桐的T台,她的穿着时髦,走路的姿势像模特,每次经过小巷,都会招来路人异样的眼光。这时,她会加快步伐迅速步入12号公寓的电梯间。
“雨桐,快进来。”尹继民说,“我等了你一整天了,让我看看你手里拿的东西。”
他给她开了门,又回到洗手间里,用剪刀剪鼻孔里的毛,她用双手搂住他的腰,她差点让他的剪刀戳进他的鼻孔。
“《阿拉斯加少女》”,她把那幅画递给他,“就是你要的那幅画一《阿拉斯加少女》,为了画这幅画,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还观看了几部关于爱斯基摩人的电影,熟悉那里的冰湖环境,在郊外一个已经封冻的湖面上找到了灵感。我还参考了阿尔弗雷德·丢勒的技法,尽可能画得好一些,我以前从未尝试过油画。有一天,我穿着风衣,戴着墨镜,裹着围巾,一个人站在湖的冰面上,看着远处麦色的芦苇发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双脚好像被冻在冰面上了,从我旁边走过的人还以为我是一尊雕像呢,他们看见我嘴里冒着气才发现我并不是一尊雕像,是一个矗立在冰面上的埃斯美拉达(《悲惨世界》里的吉卜赛女郎)。我奇装异服,又举止怪异,没有人不注意我,我把脸蒙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不让任何人认出我,直到有了灵感我才跑回家拿起画笔将阿拉斯加少女眼角的皱纹抹去,少女永远不会有皱纹,只有中老年妇女的眼角才会有皱纹。”
“真辛苦你了,”尹继民说,“那次旅行我拍了很多照片,唯独《阿拉斯加少女》让我获了奖。阿拉斯加有广阔的冰湖,那里的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只在那里待了三天就回到了西雅图,要不是寒冷难以忍受,我还真想在冰天雪地里多待几个月,尝一尝爱斯基摩人的烤鱼。那些鱼是从冰湖里捞上来的,坐上阿拉斯加少女的雪橇向更加寒冷的地方飞奔。我还跟极地犬合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也成了游客们的抢收货,他们争先让我给他们也拍几张,要不是相机没电了我们还在拍。手套里的手都冻得弯不了,我们在爱斯基摩人的冰窖里住了一个晚上,是几个人挤在一块睡的,冻的人根本睡不着。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睡不着我们就唱歌,大声唱着长工号子:哎嗨一哎嗨一哎嗨,驱寒的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求返回,我怕我冻死在阿拉斯加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幅画本来是一件摄影作品,是尹继民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拍的,尹继民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也是本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他的相册里还有一些老照片:皱了的出现裂纹的全家福,身后是海水的单人风景照,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的吻落在父亲脸上的父女照,他跟他的夫人与兵马俑的合拍照,在海上乘船拍的老龙头的正面照,与某某名人的合拍照。
她把这幅《阿拉斯加少女》摄影作品画成了一幅油画。
詹雨桐上前搂着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说:“你可千万不能冻死,要死咱俩一块死。冻死之前我还要画一幅《阿拉斯加情侣》抱在怀里,这样,即使是冻死了也会感动所有人,待人群散尽后,厚厚的雪会将我俩搂得紧紧的尸体覆盖,等到几百年后,科考队员会发现他们找到了最值得研究最值得收藏的化石一南情活化石。化石在科考队员的怀里悄悄融化,没准我们还会变成复活的恋人呢。不过,我刚才在路边停车时,把车蹭在一棵树上了,那是一颗法国梧桐,该死的树,气死我了。”
“那次从美国回来,”尹继民说,“我才知道阿拉斯加州并没有跟美国大陆相连,而是一块从俄罗斯买来的土地,倒是跟加拿大连在一块,越过白令海峡就到了俄罗斯,没想到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竟然还是邻居。啊!真是冷得要命,雪景美极了,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过《呼嘯山庄》吗?里面的雪景美极了,阿拉斯加比《呼嘯山庄》里的雪景还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