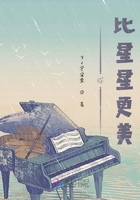二十七年后,南京秦淮区某医院,重病卧床的二胡叔脑子犯糊,把当年的事又对我讲了一遍,护士喂完药,他很快睡下了。我走出医院,突然想回家里看看,经过船板巷的时候,停下脚步,回想起老魁捡养我的一幕。
那是事隔一年后的一个夜晚,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南京城南的船板巷行人寥寥。忽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冬夜的寂静。这时老魁路过,闻声后快步走过去,一眼看到满脸泪水的婴儿,心生怜悯,于是抱起婴儿回了家。
他自己一直没成家,和年过花甲的母亲一起生活。早年是外来户的他们,在南京城也没个亲戚,是典型的独户。
母亲见儿子突然抱个婴儿回来,又惊又喜,但也没细问,她自己儿子是什么人她心眼儿里最清楚不过。把婴儿放到床上,老娘掀开婴儿的裹被一瞧,还是个带把儿的,估摸着还没满月。看着看着,他母亲竟然流出了眼泪。
这也难怪,年轻那会儿,她生的第二个儿子还未满月便无故夭折,当时取名叫狄木。眼前的这个嗷嗷待哺的男婴,燃起她内心深处对狄木的想念,或许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她便给这个婴儿取了个名字也叫狄木。
那以后,老魁便成了我的父亲,他母亲顺理成了我的老奶。
说来也怪,自打记事起,我就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也就是在年根儿底下他回家,才能和他在一块儿多呆些日子。小时候,我总是问老奶,父亲怎么老不回家,老奶便解释说他在外面忙活,抽不出空回来。
长到六岁,老奶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常跟我讲人不学点儿文化,在社会上很容易吃亏,叮嘱我在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
老话说的好,天有不测之风云,我初中还没读完,寒假的一个夜里,没有任何预兆,我的老奶突然撒手尘寰。这事是我第二天早上才察觉的,那会儿老奶的身体已经冰凉而僵硬。
我们家本来就没有亲戚,父亲又没回来,老奶的丧事都是周围邻居们帮忙着料理。当时我还问一个邻居老奶去世了,我父亲是不是要回来了?邻居却跟我讲他人现在在哪里都不晓得,想给他捎信儿都没个路子,他又怎么会知道我老奶过世的事情呢?事实正像他讲的那样,父亲后来一直也没有再回来。
我老奶虽然过世了,但家里还是有些底子,往年父亲每次回来也都往家里留不少钱,加上二胡叔、热心的邻居们的照顾,在生活上,我从来没有发过愁。
像二胡叔一样,我天生也没有读书的脑子,老奶在世时,我就想跟她讲我不想上学了,但一直没说,怕伤她的心。现在老奶过世了,我更是没了心思继续去学校,十五岁开始,也就在二胡叔的古董店里帮忙,长了不少见识。
但我天生坐不住,这点儿倒挺像我父亲。八年后长大成人,二胡叔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托人给我在城里某个私家旅行杂志社谋了份记者助理的差事,能满世界转悠,倒也合了我的性子。
杂志社的主编是二胡叔的亲侄儿,他人挺不错,待我跟自家人一样,平日里没少照顾我,抽空儿就教我怎么拍照,怎么撰稿。一年的时间,我升到摄影记者职位,而主编改行开了书店。
我家在城南,杂志社在城北,一个南一个北,来回折腾了一年,身子骨实在有些顶不住,干脆,我就近在杂志社周边租了个房子。公寓环境不错,房租算得上那周边最便宜的。自己的家,也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回去收拾收拾,给老奶上上香。
这些年,每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尤其是晚上,我总会想起老奶和父亲,这世上我唯一的两个亲人。老奶去世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父亲现在是死是活我仍是无从知晓,但内心里总觉得父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期待着某天他的突然归来。
第二天傍晚下班,就在我快迈进公寓大门时,突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愣了得有三四秒,才认出眼前拍我肩膀的、一头卷毛儿的不是生人,竟然是自己家隔壁的发小儿----李震猛。
小学到初中,我和李震猛都在同一所学校,处的算不上铁,偶尔打打交道。但自打我离开学校后,便很少与他联系,算起来,我们两个得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
李震猛这个人是家里的独苗儿,父母很是溺爱。但他似乎生来就不是个活闹鬼,上小学那会儿便开始在学校里拉帮结派,没少跟人打架斗殴。听人讲,高中还没毕业,他便与社会上在刀口上过生活的人厮混在一起,没少犯事儿被警察抓进局子。
“杆子,几年都么见面,单看我后背就认出我来?行啊你!”
“你个呆逼一样,我哪有那么来斯,我可在你住的这地儿外面蹲了一个下午,专门找你来的!”
“找我?有么急事儿吗?”我想多半他现在是缺钱了,不然怎么也不能花一个下午的工夫蹲街。
“大街上可不是我们两个聒白的地儿,走,路对过大牌档开洋荤!”
南京人最爱上的馆子就是大牌档,虽然名字叫大牌档,但是却很干净整洁,有浓厚的古都底蕴,吃饭聊天最合适不过。上到楼上,找了个清静的座位,点了四道招牌菜,一瓶五粮液。
“杆子,几年不见,怎么,现在在哪行儿发财呢?”我先递了根儿烟过去。
“发个屁财!这些年不是撞见鬼就是活丑,社会不好混啊!”刚点上,他就狠狠的吸了一口。
“啊是怎么晓得我住在这块儿?”
“跟人瞎打听唄!”
“杆子,么事情你就直说?虽说我们老长时间没见面了,但我们是老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绝不嘀嘀嗒嗒!”
“棍气!够味!来,我们两个先干一个!”
满满的一杯酒下肚,李震猛紧接着又给我倒了一杯。
“狄木,听人讲,你现在在杂志社做记者呢?”
“么的错!到现在,已经做了六年多了!”
“记者挺好,比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阎王吃小鬼好多了,怎么,现在一个月有个万八块的吧?”
“么的,也就几千块,我是月头放卫星,月中吃半斤,月底鬼转经。”
“想不想赚个大的?跟你讲,我手上可有个发大财的路子,你,想不想干?”
“什么路子?”说实话,每个人都会做发财梦,我也不例外。
“你当记者肯定也去过不少地方,贵西,你去过吗?听说过那块有个叫乌寨的地方吗?”
“贵西么去过,你说的乌寨是什么地方?听着,怎么有点儿像少数民族住的地方!”
“具体的我也不晓得,但现在,我可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大主顾,他早就放出话儿来,说谁要是能替他寻个去窟寨的路子,就给谁三百万的票子!”
“三百万?这么多?”我激动的差点儿没坐起来。
“先别虚,别虚,我还没说完呢,除了给他提供路子呢,还得拍几张乌寨的照片。他手上有些个手绘的图样儿,照片和图样儿对的上,三百万才能顺利到账!当然,如果事后领着他的人到了那个地方,还有更多的票子!怎么样?这事儿,你肯定愿意干吧?”
“三百万?这数字儿听起来真挺诱人!可,这好事儿,你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我有些疑惑,有这样赚大钱的机会,他自己不独干,干嘛非得搭上我呢?
“瞧你这话说的,你这是没把我当老把啊!我李震猛什么人你还不清楚?有什么好事儿,头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自己的杆子!”
“这事,你自己不也能办吗?不就找到那块儿,然后再拍几张照片吗?”
“杆子,这事儿你干不正合适吗?你看,你是记者对吧?不论去哪块儿,拍什么样的照片,那怎么的也算得上出师有名!再说了,最近我忙的实在是抽不开身,所以,这事儿只能麻烦你了!但是,杆子,你放心,一切完事儿后,所有的票子,我分一半儿给你,这可不是在花你!”
“杆子,实话讲,你说的这事,我倒也有心思干,有谁不想发财啊?可我得工作、上班,抽不出时间啊!这事儿,我可帮不上,你还是另找个吧!”
十多年都没见过面,可李震猛这一开口就是上百万的票子,估猜,十有八九,这里头有什么猫腻儿。他在社会上可算的上老江湖了,我可弄不懂他的心思,弄不好,出了什么事,我还得进局子,只好推脱。
“杆子,有了几百万,你还用上个吊班,啊是地呀?”
“算活拉倒,算活拉倒,这事儿你还是找别人吧?”
“啊油,我的乖乖隆嘀咚,真么想到,你这小子现在也有两把刷子了!看来,不给你一得儿鱼饵,你是不会上勾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