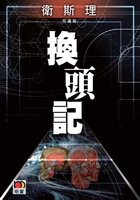司仲抬头看了看草坪周围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回头对沈秋韵说:
“主人不恭,反怪客人无礼吗?”
沈秋韵故意大声说:“章副大队长讲了,今天你教我练琴,谁也不准打扰!”
黄营长赶紧从屋里出来,对几个哨兵说离远点,离远点!”
两人上楼到了琴房,等沈秋韵坐到琴边,司仲问:“哪个章副大队长?”
“章志呀,他接了汝平的位置。”
“汝平,真的一”
“暴死了!”
“章志的官运亨通啊!”
“你的官运也来了!”沈秋韵故意讽刺说。
“你是什么意思!”司仲感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沈秋韵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
司仲把钢琴弹得震天价响……
沈秋韵转到司仲侧边小声说你不要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夕卜。你们的导师列宁不也坐过牢吗?出狱后仍然是一个革命家!”
“你到底想说什么?”司仲平静下来问。
沈秋韵急着说:“爸爸、妈妈知你被囚,就一直在找门道救你,没有结果,又反过来求姐夫和章志了。”
“他们不会立地成佛的!”
“你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唯物辩证法看世界吗,”沈秋韵寸步不让地说,“汝平死后,他们兔死狐悲好像都夹起尾巴走路了。”
“是吗?”
“爸爸对章志说:司仲是秋韵的救命恩人,花多少钱,我们也要把他救出来。”沈秋韵述说着,“昨晚,我们开了家庭会,姐姐当着爸爸妈妈的面对姐夫说,司仲和秋韵早有婚约,看你讲不讲手足之情?姐夫当着二老的面说:我叫章志给他办个出狱手续就是了。只是他们必须马上离开成都,最好是出国。”
“请转告伯父伯母,切不要为我浪费一分一厘,”司仲深怀感激之情,“那样会让我不安九泉。”
“我就知道你不会领情的,”沈秋韵生气地说,“可他们就是不听!”“你要我如何领情?,
“既不唱高调,又可不为囚徒。”
“还有第三条路去桃花源吗?”
“我们一同去美国吧,”沈秋韵温情脉脉地说,“其实科学救国梦与大同梦也是可以殊途同归的。”
“不要祖国了?”司仲惊异地说,“眼看着日本鬼子吞食我们的国家,忍心一走了之?”
“海外游子总比待毙的亡国奴强!”沈秋韵含泪说,“你现在身陷囹圄,何言救国?”
“既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在美国读完博士,圆你的科学救国梦?”
“不甘心于你的无情无义!”沈秋韵愠怒了,“决心回国来找你算账的,没想到苍天有眼,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司仲低下头,痛苦地说:“是我对不起你,早该忘掉我!”
沈秋韵见状气一下消了:“淞沪抗战你拿起了枪,未能挽救祖国的危亡。现在被你的上级出卖,壮志难酬。出国深造有了实力再为振兴中华作贡献,不也是莘莘学子都在走的路吗?”
“回想去南京请愿的那一腔热血,今天你一”
沈秋韵又激动起来:“我怎么了?我要的是现在和将来!你以为坐在牢里高唱反叛之歌,就是共产党人的节操吗?事实说明不出牢笼什么人生价值也没有!”
司仲淡淡一笑说你不要耻笑我沦为阶下囚,这并不是章志的高明,而是他利用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对党的忠诚,将我骗人罗网的。他敢放我出去,我第一个取下他的人头!”
“你对你以前做的事后了吗?”
“无怨无悔!”司仲仍笑着说,“没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无数共产党人正在为此前仆后继!”
沈秋韵出奇冷静地说:“真正聪明的人,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走出牢笼。”
“何以利用?”司仲不屑一顾地说,“暴动计划,下属名单,都是党的绝密!我决不能拿去当筹码,换取个人的自由,当可耻的叛徒!”
沈秋韵并不生气,附耳对司仲说两个字:拖延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营救你。”
别动队策反大队部里,灯火通明。
牛克前皱着眉对章志说重庆参谋团对我很的工作很不满意。”“为什么?”
“司仲手里的暴动计划和下属的名单一样也没弄到手。”
“他们也太不近情理了!”章志很生气地说。
“你还说哩!”牛克前大怒道,“都怪你和汝平争功,早早地就把他给捅上去了,现在怎么下台?”
章志有点惧色地说我原以为司仲在共产党内混得不久,稍微一拉就会过来,没想到他会这样冥顽不化!”
牛克前看了看表说天亮后,刘司令就要来传达蒋委员长的密令,处决一批共产党要?把司仲塞进那里边去处决了算了,省得这个案子把我们也搭进去!”
章志深知,牛克前是怕他彻底破了开县中心县委的案子,抢了他的位置,嗫嚅着说他的案子汝平不是早报上去了吗,而且……”
“你是说一,”牛克前故作姿态,“还有点油水可捞?”
“司仲那里,逼得太紧恐怕不行。”
“把你的绝招都使出来吧!”牛克前想,“你那点狼子野心能瞒得过我吗?”
“只有将你刚才的办法变通一下一”章志试探着。
“快说吧,时间紧迫。”
章志走到牛克前前低语了一阵,牛克前原先哪里知道章志说的要对司仲搞假枪毙的计策,是事先得到别动队刘司令批准的。听后不同意地说刘司令耳目众多,他知道了可是要掉脑袋的!我告诉你,汝平遇害的事,南京追得很紧。”
章志狡黯地说如不这样,要真叫重庆参谋团把人弄走了,他们一旦破了案,我们就只有掉脑袋了!”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牛克前这时才明白章志的阴谋,说完很不高走了。
章志料到牛克前绝对要把对司仲的假枪毙搞成真枪毙,让自己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他再次冥思苦想自己的计策,完后肯定:“如果此计成功,刘司令决不会把功记在牛克前身上,出了纰漏呢,你牛克前是正职,上司又不会追究到我身上,而该你牛克前去兜着!”
于是,章志便不顾一切地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牛克前发现,自开县中心县委被破坏后,章志在刘司令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心想:“刚把汝平解决掉,又马上冒出个来与自己叫板的章志,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好你个章志,不是要搞假枪毙蒙蔽重庆参谋团吗?我就来个真枪毙,看你还能不能叫死人说话弄出有用的口供去请功!”于是赶紧策划对司仲的处决行动。
半夜,在悔过室刚刚人睡的司仲,就被几个提红马灯的别动队员叫了起来。在瀛环中学禁闭室关押时,难友们就告诉过他,晚上提红马灯的别动队来提人就是弄出去行刑。他穿好衣服走到镜前梳理了一下头发,从容不迫地走下楼去。在别动队员不知不觉中,他悄悄将沈秋韵白天送给他的绿花手巾,挂在梳妆台下的抽屉把手上,以示与她永别。
刑车在城里弯来拐去地走了很久,刚出城在一座桥头就被黄营长对开来的车挡停。
“太疤!”黄营长下车用手电照着对面车上的执行官喊道。
太疤下车问:“黄营长,你怎么知道撵到这里来呢?”
黄营长:“我还没问你是怎么在我眼皮底下把人弄走了的哩!”
太疤兄弟,这就要怪章大队副比牛大队长的官小那么一点点了!”黄营长走到太疤跟前递上一纸公文在他脸上一照说说得好!刘司令叫你马上回司令部去另有任务,牛大队长在那儿等你。这里交给我。
你执不执行呢?”
太疤照着电筒逐字逐句地读完了刘司令签署的命令,才无可奈何地对黄营长说老弟,牛大队长特别交代过,他一会儿要来验尸啊!”
“去你妈的吧!”黄营长骂道,“刘司令大,还是牛队长大?”说完对囚车司机下令,“随我来!”跳上车朝十二桥方向开走了。
太疮摸不到东南西。半天才想到是章志到刘司令那里去讨了执行令,抢在行刑前来截住刑车的。他不敢怠慢,赶快回去向牛克前复命。
刑车在黄营长的押解下,东弯西拐地又走了很久,来到十二桥西头一个密林里的小坝子。小坝子四面树上挂着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十一个戴着镣铐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推下车子,一字儿排开。
黄营长走近大家说“刘司令爱才惜才,走时对我讲了:只要你们现在愿意回头,前途还是大大的有啊!”
十一个人,个个挺立,昂首迎天。
黄营长走到司仲面前十分痛惜地说司老弟,章副大队长特别关照你啊,他说你是个孝子,你就忍心舍你母亲而去吗?那个暴动计划和下级组织人员名单,真比你一家人的性命还重要吗?”
黄营长一个劲地说交出来吧,刘司令说了,只要交出一件就送你出国。章副大队长把护照都给你办好了,现在交出来,马上把你送走,车在后面等着哩!”
“黄营长,时间到了!”执行官催促说。
司仲不予理睬。
黄营长放下马灯退后几步,大声命令说:“我喊口令齐步走,再数十下,愿回头的向后转,立定不动……”
“齐一步走!”黄营长开始数,“一,二,三……”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司仲唱起了国际歌,十个人跟着唱起来,和着节拍向前走。
黄营长慌忙吹响了口哨,排枪响起,十一个人全都倒在血泊中……
黄营长将血泊里的司仲一把拉起,从上摸到下,只在左腿上摸到了一把鲜血,暗自佩服剑子手“当真做得利索!”
章志在床上梦见:黄营长将司仲带回来了,司仲感激得五体投地,叩首如捣蒜地说章兄,过去你是我的上级,现在和将来,我永远是你的下级啊!母亲居孀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怎能舍她而去呢?我愿交出暴动计划和全部下属人员名单……”
“报告!一”
章志听出是黄营长的声音,心想:“梦已成真!”从床上一跃而起,开门便问,“暴动计划、人员名单都拿到了吗?”
黄营长呆若木鸡。
“没关系,没关系!”章志见状自我解嘲地说,“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嘛!”
“是!”黄营长哭笑不得。
“人呢?”章志神经质地吼叫起来。
“还在车上,穿的大腿肚子没伤骨头。只是流血太多!”
“啊一,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嘛!还不赶快送医院?”
“是!马上去。”
“保密!要绝对保密呀!出了纰漏拿你是问!”
“是!”黄营长机械地转身走了。
“叮!叮!叮!一”电话响个不停。
章志转身拿起电话一听是牛克前打来的,本想先对他说点什么,一时又想不起要说些什么。
“喂!喂一”对方叫个不停。
“啊!是牛大队长呀!”章志不得不应,脑门直冒冷汗。
“你把司仲弄到哪里去了?”
“你说什么?”章志极力让自己镇定些说,“晚上我多喝了几杯,刚才睡了一会儿哩!”
“我马上要见司仲!”
“你一奉谁的命令?”章志感到来者不善,两眼发直地望着墙上的蒋委员长画像。
章志深知身为叛徒的牛克前,是决不允许他的部下再背叛他的!虽然他最近常遭到刘司令的训斥,但重庆参谋团还是很器重他的。我若要直接与他抗衡,那就是以卵击石。于是缓和口气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你的黄营长没告诉你?”
“这样吧,电话里说不清,我马上去你那里。”
章志放了电话却跑至U刘司令那里去了,还没哭诉完“报告!”机要员送来一份电报:
刘司令:
速将一般共党分子移送刘湘处理,立即将司仲、龚志平押送重庆反省院。
重庆参谋团
刘司令将电报递给章志说你看,牛克前这家伙又在背地捅刀子了嘛!志平?”
“牛克前没向你报告?”
“没有呀!”
“开县中心县委副书记。”章志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从宣汉县抓来的。我回成都后,才听汝平大队副告诉我,说牛大队长让他以无处关押为由送至U华阳监狱去了。”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刘司令十分生气地说,“你们在背后都干了些什么?”
“过去,一直都是牛大队长向你报告。”章志分辩着说,“我还以为他们都对你讲了哩!”
“你回成都后见过龚志平吗?
“听汝平说,交过去后,他去提过几次人都没见着人。”
“为什么?”
“刘湘的人说,他们也会办共产党的案子,不用我们操心!”
“啊!一是这样……”刘司令想出了对策说,“我电告参谋团,说司仲已被牛克前在执行总统的密裁令时处决了。押送龚志平嘛,叫牛克前去办!如何?”
“好,好,好!太妙了!”
“还要做两件事,”刘司令仔细地对章志交代说,“你马上去找太疤,搞个笔录,要他交代枪毙十一个人犯中司仲的名字是牛克前指使他添上的。只要这一句就够了,按上太疤的手印。送我阅签后,交档案室备案。”他又悄声说,“你马上叫黄营长用我的车,将司仲送到华阳监狱,档案上将他的名字改为成久持。把这杯尝之有味,品之不对的陈酒,送给刘湘去吃吧!哈哈!”
“妙,妙,妙!”章志拍手媚笑说,“让参谋团去和刘湘斗吧,好不乐哉!”
“这事——,”刘司令深思熟虑,“此事,你必须在天亮之前办完。只要司仲消失了,谁也奈我不何!而成久持身上的油水,我们再慢慢榨嘛!”“是,是,是!”章志“扑通”一声跪下,捣蒜似的磕头说,“刘司令,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快起来吧,”刘司令躬身扶起章志,“我马上打电话叫牛克前去执行重庆参谋团的命令,这一两天他恐怕没时间来纠缠了。”
瀛环中学门口那一声“不许动”惊呆了跟在司仲后面的胡麻子。眨眼工夫,他看到司仲和蒋致君就被便衣抓住了,正要来个饿虎扑羊袭击便衣特务救走司仲和蒋致君时,忽见司仲回头一个撤退的信号,两脚便钉在地上纹丝不动了。幸好蒋致君没有发现,胡麻子才得以在惊魂稍定后,悄消失在人中。
胡麻子离开九思巷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牢记司仲叮咛的“成都是豆腐干街,遇到紧急情况,不要老沿一个方向走,弄不好又走回了原处,让人家逮个正着”。他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才折向右边的大街继续走,来到一家小巷边的茶馆里,找了个进出方便的位置,看看四周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才坐了下来。他要了一碗茉莉花茶和一盘瓜子,生平第一次这样悠闲地喝起茶来。
“小兄弟,”胡麻子还是怕自己又转回瀛环中学去了,拉了下掺茶的伙计问,“九思巷离这儿多远?”
“它在东,你在西,”小伙计说,“两杆烟的路吧”
胡麻子听后才放下心来想:“昨晚那个旅馆是不能去了。三哥什么都为我想到了,可却把自己丢了!回去怎么向组织和张婶交代呢?”他端起茶碗,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腰间那一百个大洋,又装做搔痒抓了几下左胸内衣,触到昨晚司仲交给他的那张大额兑票,才又端坐起来吃瓜子。忽然间一不远处一缕绿光射着了他的眼睛,歪头一看:“怪了那不是三哥寄还给了沈女士的蝴蝶碧玉佩吗,”他差点喊了出来,“怎么挂在她的脖子上了呢?”胡麻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玉佩,她似乎发现了他的举动,当两人的眼光对个正着时,她起身迅速走出了茶馆。胡麻子这才发现她是来找人的一“莫非她是在找三哥……”他想起了司仲给他讲的他与沈秋韵的故事。但此时,已容不得他多想了,跨出茶馆就追。他见巷钻巷,见弯顺弯,忽然又觉路径不对,停下来站到一棵树下,提起衣服的下摆扇着风。再回头一看,先前的茶馆就在对面:“坏了!”他背脊透凉,“遇上特务了?这该死的豆腐干街!我怎么又转回来了呢?难道在瀛环中学门前露了马脚?”于是,赶紧钻进小巷径直离开。
胡麻子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找了家中上档次的旅馆住下来,没敢再街上了。
第二天,胡麻子到百货店去买了一灰一青两套短绸衫裤,按照司仲的第二套方案,扮作上省城来打货的客商。回到旅馆他试穿了两套衣服,感觉很合身。尚在床上,总觉得轻飘飘的……“像这样穿起,一阵大风不把我刮到天涯海角才怪哩!那时,我去找谁?不如回去向谭天万代理书记报告吧。”胡麻子翻来覆去地想,“三哥是被什么机关抓的都不清楚,如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