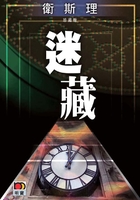或者说,也根本不愿意细想吧。
即便有那么一瞬间感到难以言表的异样,也很快被刻意地忽略过去。
小弦是不可能做什么奇怪的事的,因为那家伙是沈弦,是她这么多年来最信任的伙伴,更是能够让她安心的存在。
只要这样想着,就能够迅速轻松下来,然后抬起头,继续向着前方的未知,走下去。
在画室兼职的工作并不轻松。小孩这种生物简直就和小动物没什么两样,活力充沛,向往一切闪闪发光的存在。优雅,美丽,仿佛什么都会,任何事都难不倒她,这样耀眼的新老师在小鬼们眼里简直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可以呼朋引伴地仰着头看上大半天,睁着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张着嘴,又叫又跳。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孩子跑来画室说也想要报名学画画,大多是邻近社区的,还有附近小学的。这么一大帮小恶魔凑在一起,经常让谢华年产生一种把他们集体塞进麻袋扔去填海的冲动。
而正牌老师张望则已经完全被新一轮暴涨的生源整得疯掉了,一边欢喜,却又一边手忙脚乱地完全应付不过来。
张望也曾经有一次忍不住好奇地问过:“谢小姐你为什么肯接下这份工作呢?我看你都是业余时间才能过来,每次来的时候也都是一脸很辛苦的模样,想来正职工作也不轻松吧……你总不会是闲得无聊一时兴起——”
是啊,一个生活优渥的大小姐到底是为什么要放着舒适惬意的日子不过跑来伺候这帮小不点?
在普通人眼里看来,简直堪称不务正业之最啊。
如果母亲知道她竟然跑来这种破破烂烂的小画室做兼职,一定会连形象气质也顾不了了全瞪着眼咆哮着吼她一脸吧……
确实,在许多个瞬间,谢大小姐也依然会觉得怀疑,甚至有一些可笑。
辛苦就一定有未来吗?
明明根本谁也不可能保证。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朝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未来走下去?
如此固执地,竟连自己都常忍不住感到恐惧。
“相信”这种力量,真的能有这么强大么。
还是说,这就是“爱”呢?
是吗,是因为“爱”啊。
如今这个时刻,是她二十余年的人生里,距离“爱”与“理想”,最近的时刻。谢华年深深地这么认为着。
那么,就算不能全都握住,至少也要拼尽全力地,抓住其中之一,绝不放手。
程锦开始筹备他在S市的个人咨询所。虽然有着海外学成归来的经历,在这个过于含蓄压抑的社会,依然起步得有些艰难,为了迁就客户,连公休日也常常不得不搭进去。对于种种被冠以“心理”之名的病症,国人总还是抱持着羞耻与轻蔑的成见,觉得只要“坚强”、“不作”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与其上什么诊所,还不如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吐吐槽就得了。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程锦的咨询所几乎是无人问津的,直到过去在海外的同学介绍来了在华的外籍人士,才渐渐在对外咨询这一领域打开了局面。
而相较于这边缓慢上轨的进展,谢华年那一边的状况简直堪称地狱。
谢华年心里清楚明白,如今她想做的事,一件也不能透露给旁人知道,尤其是家里人,无论是程锦的事也好,还是……另一件事也好。
这一次,她什么也不能依靠,只能依靠自己,靠自己抢占先机,站稳阵地,让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反对之声都无话可说。
公休日和普通上班族的下班时间反而是孩子们去学画的时间,而家里公司那边的事也不能松懈,每天好不容易回到住处的时候,谢华年都只想直接倒在床上睡过去,有好几次竟然真地躺在浴缸里睡着了被水呛醒过来。
如此高度紧张疲劳的状态,不要说见面,连通上电话也十分困难。
明明是两个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人,邮件却几乎成为唯一的联系方式。不知该说太奇怪还是什么别的。
她和程锦见面的次数,甚至还不如沈弦来得多。毕竟沈弦那家伙可是会没羞没臊毫无顾忌地扑上门来就赖着不走的。
偶尔一瞬闪念,谢华年会恍惚觉得,忙碌不过是一种借口。
是回避。
无论是程锦,还是她自己,都在有意无意地避免见面,避免听到对方的声音。
因为……依然会焦躁吧。
毕竟还是不一样了啊。
太多曾经,发生过的事,谁都不可能假装从不存在,无论多么想也没办法简简单单将过去抹掉,若无其事地重新开始。
一旦听见那个声音,看见那个人在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得困扰起来,那些原本刻意掩藏的不安便如同受到了蛊惑,蠢蠢往外冒着,让人焦躁得情难自已。
甚至,变成另一个自己。
这样奇怪的相处方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总得有一个人先打破。
而如果可以的话,谢华年不想再去做那个人。
不论从前还是现在,与程锦的相处中,她觉得自己永远都是先伸出手的那一个,做每一个决定,无论开始还是结束。这种感觉就像徒手抓着一抹幻影,纵然竭尽全力,也依然随时可能消散。只要自己稍微有一瞬松懈他就会不见了,一切就会结束。
想说,逼着对方主动一次会怎样呢?这种赌气的想法虽然很丢脸,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就在脑海里生了出来。
想要这样去做,就仿佛想要一个证明,证明所有这全部并非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然而,这种心绪复杂地较劲在得知程锦竟然在置办咨询所内的用品时直接找了王不理帮忙,连事先问都没有问自己一声时终于彻底崩坏了,长期蓄积的压抑转化成另一种无法控制的情绪,强烈地迸发出来。
为什么约了那家伙也不肯来找我呢?
这么理所当然地就被忽略了,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
既然如此,我又算是什么?
这样的想法在心中盘桓不去,任何的解释听来都只是借口而已。
从激烈争执到无力争执,真正让谢华年彻底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的是程锦的质问。
“华年你到底是在爱着,还是说,想通过所谓的‘爱’来证明什么呢?你所执著的,到底是我呢,还是你迫切想要证明的,那个‘拥有未来的自己’呢?
“你爱的……真的是我吗?”
瞬间心悸,遽然如被扼住了咽喉,整个人就空了。
被否定得如此彻底。
眼前人说话时低垂的睫毛颤抖出哀伤的纤细,嗓音轻柔到每一声都令人心惊。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在看着我?
为什么我竟然会是这样的?
这真的是爱吗?
如此辛苦,疼痛,这样的恋爱,世上怎么可能会有。
可是,如果这并不是爱情,又还能是什么呢?这样拿不起又放不下的自己,究竟是在做些什么?
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叫着:“不是!不是这样的!”却怎么也找不到理由。
无言以对,无可辩驳,连自己也无法说服。
是谎言,亦是真实。
并非爱情,又是实实在在的爱情。
只是终于在爱对方与爱自己的战争里,狼狈地分出了胜负,如此而已吧。
是啊,这就是,打心底里不能相信,却又固执地竭力维持着的,无法承认也无法推翻的“自己”。
爱情从来不该是输赢的角逐。
即便只是一刹那的动摇,忍耐的理由也已被击得粉碎,驱使人依然前行的,只剩下惯性而已。
又或许是为了逃避。
接下来的一周内,谢华年都在重复着前一日的生活,仿佛已经设定程式的机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直到忽然就在踏上公司大堂电梯的那一瞬间两眼发黑地栽倒下来。
穿过玻璃射来的阳光,刺得头脑一阵胀痛。
醒来时已经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眼前从模糊到清晰的,是那张熟悉的脸。
沈弦。
谢华年本能地想坐起来,立刻感到一阵晕眩,伴随着想要呕吐的反胃感。视线还有些昏暗,脑袋被绷带紧紧缠着,可以感觉到右侧太阳穴上方的某个位置隐隐疼得厉害,大概是撞伤了。她挣扎了一瞬,便放弃地重新躺回绵软的大枕头里,含混不清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因为我二十四小时在盯梢你啊。”沈弦皱着眉,一副发怒的模样,嘴上却仍说着不着四六的胡话。
谢华年默然望着他。
“骗你的,你自己失去意识之前拨了我的电话,真的完全不记得了吗?”沈弦的声音听来似笑非笑,没有了镜框的遮挡,那种凝神审视的眼神便愈发显得锋利而灼热,让人无法招架。
踩上电梯之后的事是真的没有任何印象了,或许只是下意识的应激反应,按下了那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保存为应急呼叫的按键。
谢华年一时失语,只能无言地看着对方,以仰视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