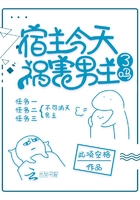“俄共”之所以不断分化、分裂,除了来自外部的挤压拉拢外,很重要的是与其自身定位不明确有很大关系。“俄共”的纲领路线的正确与否,也与这一点密切相连。关键在于,“俄共”究竟充当一个试图推翻现政权的革命党,还是充当一个在现存制度下建设性的反对党?对于这一点,“俄共”领导人是含糊不清、左右摇摆的。
“俄共”自20世纪90年代初重建并进行登记后,它声明不谋求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认同议会民主,就成了体制内的政党,它参加的一系列竞选活动、议会活动,无不表明它是在现存体制的框架内开展活动。可是,“俄共”作为反对党,它不能不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坚持当一个“不妥协的反对派”,什么问题上都与当政者闹对立,进而再去支持罢工和“街头政治”,在当今俄国政治、经济、社会正在复兴和平稳发展的境况下,“俄共”可能进一步走向孤立和衰落,甚至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威胁。久加诺夫似乎看到这一点。如今已不足20万人的政党近半数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30岁以下的年轻党员竟不足7%,这样的政党完全有可能丧失“大型政治组织”的地位,沦为政坛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甚至进不了杜马的门槛。如果“俄共”改弦更张,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建设性的反对派”,那就必须抛弃共产党固有的某些纲领和政治主张,与当政者既有建设性的批评监督,也有建设性的决策参与和合作,在这样的前提下去谋求选票和府院中的职位。这样一来,“俄共”也就失去其原有的性质和地位。在不健全的俄罗斯政党政治下,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不可能建立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健全的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因此,“俄共”只能长期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对“俄共”来说,正处在这样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只有正确判断内外形势,对自身合理定位,以此制订切实可行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才能走出困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三)“俄共”的纲领、章程及其方针政策已经不适应俄罗斯现实
1993年召开的“俄共”二大提出的任务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式的人民政权”,恢复各民族的“联盟国家”,即恢复苏联;近期目标是“阻止国家资本主义化,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1995年,“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规定,要“建立人民政权”。但这里所说的“人民政权”概念十分宽泛和模糊。事实上,俄罗斯自独立以后,10多年来政治、经济的转轨和社会转型,已经初步建立起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并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特别是普京当政以来,始终得到很高的民众支持率,就是一个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不顾实际地提出恢复“苏维埃式的人民政权”,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在行动纲领上,2000年,“俄共”七大规定,“俄共”要成为普京政权“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的角色;2002年,“俄共”八大仍规定“俄共”将同新一轮自由化改革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2004年,“俄共”十大上,久加诺夫仍主张“要继续为恢复苏维埃政权而努力”,除了搞议会斗争以外,还要搞群众性的街头政治,他在报告中说:“普京当局正在把俄罗斯引向西方强国附庸的道路,将使俄罗斯社会局势不断激化。”这种判断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
(四)历史包袱未能真正卸下,意识形态存在严重缺陷
“俄共”领导人提出以社会民主为核心的主流意识,放弃一些传统教条,但他们又沉缅于对旧体制的怀念和对恢复苏联的期盼,使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打上保守的烙印。对“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反思停留在概念辞藻的浅层次上,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方向又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范畴。例如,久加诺夫在1999年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称斯大林不仅是20世纪俄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而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则轻描淡写。他还认为,要把斯大林遗产中好的内容应用于“俄共”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工作中。对此,在许多俄罗斯人的心目中,“俄共”成了“守旧”、“僵化”、“保守”、“倒退”的同义词,其思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总的说来,“俄共”领导人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思想特征。原先“俄共”领导人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国思想”等口号来对付叶利钦,如今这些口号被普京接了过去,成为其治国理论的组成部分。这样,“俄共”手里的意识形态武器更少得可怜了。
(五)“俄共”未能适应转型期俄罗斯社会阶层的急剧变化
所依靠的社会基础不断削弱,这是“俄共”党员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社俄罗斯农村废弃的村庄似乎显现了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动会贫困阶层是“俄共”的主要依靠对象。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推行的激进改革使大量社会贫困阶层成为左翼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可是,普京当政后,实行平民主义路线赢得贫困阶层的好感,随着国家经济状况不断好转,普京推行一系列旨在消除社会贫困的措施,使不少人从支持“俄共”的行列中分化出来,俄罗斯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一瞥转而支持现政权。
“俄共”对知识分子的疏远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苏联时期,知识分子长期受到集权统治的压抑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社会变动时期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民主派及民主政治的潮流,而在居民文化水平较高的俄罗斯社会,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更明显,这方面恰恰是“俄共”的薄弱环节。
传统的共产党活动基地在大城市以及工人集中的大企业。而在当今俄罗斯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各阶层分化变动都很频繁,事实上,“俄共”在大城市已找不到强有力群体的支持。历次杜马选举表明,在农村,还有大量居民是“俄共”
的支持者。美国学者斯蒂芬·K.韦格伦在俄罗斯5个地区农村的抽样调查,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3次(1993、1995、1999)国家杜马选举表明,“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基于大城市和大型城市居住区的堡垒”,“农村选票是俄联邦共产党再度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南部农业地区,由于支持共产党候选人而被称为‘红色地带’。”据作者分析,20世纪90年代改革带来的“市场灾难”,使“农村居民和农业工人成了最大的失落群体”,这些人也成了支持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美国学者的这一调查,至少说明在急剧变动的转型社会里,许多传统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阶层分化的加剧,一个政党只有准确把握社会变化的动态,提出适宜的口号去吸引群众,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
“俄共”的由盛及衰也许显示了这样的“民意表”,它正在失去若干个社会群体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打击不法金融寡头深得民心,“俄共”却将一些大富豪作为它的候选人。排在“俄共”候选人前列的18名中就有5人是百万富翁,其中最富的是尤科斯董事穆拉夫连科,存款约0.5亿美元,年收入达1138.4万美元,还兼营房地产。这些富人在“俄共”党内地位显着,使“俄共”阵线模糊不清。
(六)“俄共”领导集团内部不团结,大大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主要领导人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严重。“俄共”发生一系列大分裂都与领导人处置不当有关,使党的元气大伤,社会影响日减,不少党员希望更换领导人。但久加诺夫认为,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分裂分子及时清除出去,完全承袭了过去“苏共”处理党内斗争的思维模式。久加诺夫还多次表示,他决不后退,要战斗到底。
久加诺夫在2006年6月“俄共”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虽然开始认识党面临着生存威胁,但他在报告中提出要准备参加新一轮杜马和总统选举,为此要将党员人数至少扩大到61万人,要将抗议活动成为党的主要斗争手段。从这个报告中看,“俄共”领导人坚持“不妥协的反对党”的立场基本未变,而他提出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扩大2倍的党员人数也是无法实现的,斗争方式基本上也是陈旧的。看来,“俄共”领导人尚未走出传统的思维和活动方式的窠臼。而“俄共”真正要在俄罗斯政坛上站稳脚跟,必须从思想观念、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上不断创新,才能逐渐壮大并成为一支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