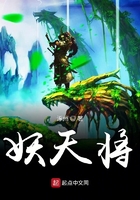张大牛感觉到自己在消散,他脸上狰狞,他怒!肝主怒,属木,张大牛的肝便化为乌有,一道灵光如蛇般窜了出去,归于林木之中,张大牛只觉再无愤怒,身体魂魄里似乎被剔出了一些东西。
他便悲伤了,肺主悲,属金,他的肺也化乌有,灵光溢入,遁入砾石之中,他便不再有悲,他知道,自己便将要这么散消于世间,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恐惧的吗?张大牛恐惧了,肾主恐,属水,他的肾也便消亡了,灵气散入荒川泽国之中。
在这将消亡的瞬间,少年时的往事,那大家还将他当成神童的美好岁月,那老娘舅,那启蒙老师,还有镇东头的阿花……还有那一袭白衣纵行的荆十九,对了,她说她叫荆凤鸣,要能娶她做媳妇儿,就算不再是神童了,不再是天才了,怕也无须计较了吧?
胃主思,属土,思绪逸过,又一丝灵气逸入大地,他不复有思念了。
于是他便只有苦,一心的苦,不尽的苦,他有无穷的苦。思绪的飘零是他无法挽留的,二十出头的少年,又知道什么叫悲凄?他向来不是血溅五步的性子,自然他的怒也很浅显。他明知是爆体的结局,却还去练,对于恐惧,其实也不如他想象中的胆怯。
但他苦,那十二岁前的神童的日子,真的都是欢愉么?也许不过是编织来麻醉自己的说辞吧。从两岁起,他就再也没有童年了,别人在过着童年,他在过着少年的岁月,已被启蒙老师不辞劳苦地灌输无尽的、似乎永远也学不完的符语和手印。
他也羡慕别人手上的糖人儿的,但老师总是对他说:“你是天才,你生来就与他们这些不同的。快点把这段驱邪咒背下来!”他也惦记着游神赛会的热闹,但老师总不准他去看。他吃了许多的苦了,他在十二岁前,几乎把别人少年、青年以至中年的苦全受了,直到十二岁发现自己不是神童时,他脸上也装得如老师及父母一般的悲伤,心里却何尝没有一丝窃喜——不必再受煎熬了。
但从天才到平凡的突然转变,却仍是苦的,又是九年,许多的苦。就算豁出去别乡离井,就算豁出去青楼寻欢,却又遇上荆十九他们的争斗,无妄之灾,无妄之苦!这样倒也罢了,救了翼姬,却落得饿死沼泽的苦,尽是苦。
张大牛守着他的苦,任天雷轰击在丘陵上,山摇地震也不放松。
第十二道天雷终于把这丘陵劈成粉末夷为平地。张大牛的身躯自然早已化作烟尘。但他的苦仍在,他最后的一线心念,仍守着他的苦,在那方圆百里,焦土一般的地面,一个如火般的心脏,仍搏动着,或者说,一团如心脏一般的火,仍炽热地跳动着。心主苦,属火。
乌云在空中迅速地消散,突然得如同它们聚合在一起时那样,无半点征兆。如洗的碧空,炎阳高照。天地间的灵气,似在一瞬间被唤醒,汹涌着向那颗如火的心脏挤了过去,此时那只悲鸣的、早已在天雷下尸骨无存的秋蝉的叫声似仍在耳,天地间的灵气却重造了张大牛。
一个新的张大牛。他张开眼,在最后的一刻,他用全部来坚守着,直到此时才张开眼。只望见,苍白柔弱的手,全然不复以前胖得手背只有五个小肉坑不见指骨的滑稽,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削瘦得病态,这是一个虚弱无比的身躯。
在只余苦时,他的灵智无比的清澈,在那一瞬间,借着轰击他的天雷,他看清了一切。没在天雷里灭亡,却是在天雷里顿悟。这世上,再无一人比他清楚火的心;更无一人,比他更明白雷的法。只因他重生在雷火中,他就是雷和火,火和雷就是他。
张大牛按着膝盖想站起来,但这虚弱的身体,却让他无能为力。放眼四周,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天雷中化为粉末了,唯他的身边有一截半焦的树枝,张大牛便拄着这半焦的树枝,站直了身体。
天渐渐地黑了,张大牛张开手,光芒照亮了前方,几道电弧在五指间跳跃,渐渐地,交错出花骨朵儿的模样,一朵闪电花,绽放,开出一朵炽烈到白色的火焰在手心里。哪怕是修真者,可以招来天雷毁灭一个城市的修真者,也无法如此随心所欲地操纵电和火。
这不是道术,不是法术,这是张大牛紧守着他的苦、在抛弃了其他的一切之后,顿悟到的这天地间火的规则,这是规则的力量,这是魔法。在付出沉重代价以后,顿悟出来的魔法。他不再是那个从流沙镇出来的少年了,他再没有悲伤,也再没有恐惧,也许连喜怒哀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对规则的领悟。
张大牛蹒跚地走在已成焦地的沼泽里,他有些凄苦地微笑,他想:现在自己大约不能背着翼姬在沼泽里走上大半天了。但他终于成就了自己童年的梦,如果再见到他的启蒙老师,也许那佝偻的老人,会为此高兴吧。
只是张大牛知道,他缺了一些东西,他不知道怎么样寻找回来,他不知道寻找回来以后,是否会失去对规则的领悟。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他是东陵大陆的第一位魔法师,没有人能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