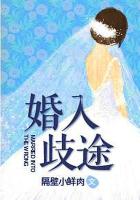“吾师已逝,太史官与陆老相爷,却杜撰神话以愚生民:吾师于西陵之灭世封印兼天劫合力之下,仍破困而出傲啸天地之神话!
或曰此说足以激发东陵黎庶之热血云云。吾以为,此非热血,实如驱邪道场之间,形若臆症之巫婆胡乱挥洒黑狗血罢了,一言蔽之:愚民,谋取所需。
据闻庙堂诸公之谋不止于此,尚欲在天下人眼前演一出戏……前日使人来说,劝某粉墨登台,坚拒之。若吾师在,必同此念。——光武二年十二月,初六,大雪。”
冬雪洋洋洒洒着,用漫无边际的皎洁掩盖大地可怖的伤疤。
朔方军经略使古刀的左脸上,新添了一道皮肉外翻的剑痕。在与西陵军的最后战役里,回中军坐镇的杜三郎让修真者于空中高呼“天下第一刀”,终于让古刀找回了往日的豪气,一刀斩碎了剑神迈克尔的领域,击杀了对手,而这道剑痕,便是那位西陵强者在世上留下的最后印记。
坐在院子里赏雪的古刀执着妻子的手,有些犹豫不决地道:“真的走么?”前几日战后论功,多人提议拜古刀为荒朔节度使,即荒川与朔方重镇都由他一言以断了。东陵的高层都知道,名义上东陵各路乡老公推的平军国事总理大臣古虎餐已然不在,现在行使东陵同中书门下平军国事实职的是古虎餐的弟子杜三郎。因此虽然只是提议,虽然正式文书还没下来,但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没有理由为难古刀。
风韵犹在的古刘氏眼里是深重的悲伤。所谓医者父母心,只要有半分良知留存,看着彩号营那么多生命一个个在自己眼前逝去,心中总不能坦然。她的声音里有说不出的倦怠:“之前家宴高朋,夫君箸脍,脍以丝连,席间竟无助者。他日庙堂艰险处,安有所援?”说的却是前些日子宴请亲近的友人,席间古刀以筷夹肉菜,厨子做菜时没把肉切好,连在一起,结果没有人伸出筷子去帮古刀按住,以使得他可以将肉夹起。古刘氏因此以为,他日如果有事,这些人都是不可以相托的。
古刀望着檐前飞舞的雪花,有些不舍。想起前些日子与陆老相爷的长谈,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古虎餐若还在,大约古刀是不会苦恼这些事的,自从出天牢以来,他向来不用发愁这类事,只管站在古虎餐身后便好。如果阿福还活着,他会怎么选择?古刀想到此处,眼睛亮了起来,也许,这次跟从前一样的选择,就好了。
雪花掩不去腊梅的清韵,在张七郎的眼里,站在腊梅边上的阿尔特弥斯却比腊梅更脱俗。因为这个深目高鼻尖耳的女子,许多军中的袍泽都与自己少了来往。张七郎的老母亲日夜不肯消停,在家便和张七郎的几个弟媳一起咒骂这花妖迷了七郎的魂,出门更和一班邻里的老太太同气连枝地念叨……
张七郎苦笑着向杜三郎举起杯,无言地喝尽了杯中的酒,摇头唤着杜三郎的字道:“子腾,相比之下,战场更清静些。”
“七哥,你还是叫我三郎还是小杜吧。”杜三郎显然对古虎餐给他取的这个字很不以为然。他成年前本来对自己的名字就很不满了,杜辟,同窗都管他叫“肚皮”,想不到冠礼取字,古虎餐仍是不改的恶趣味。
“七哥,有什么可烦恼的?毕竟在战役结束前,你就把你家这位说服反正了,又不是俘虏,怕什么?不过话说这位,鼻子高得跟割纸刀有得一比,眼睛蓝莹莹的,夜里你就不怕吓着?当时咋就对眼了呢?”杜三郎是古虎餐养大的孤儿,尽管性格大相径庭,话语里多少带着一些古虎餐的印记。
被他问到这节,张七郎的脸皮便发起紫来了,只是低声地道:“对眼就是对眼了,有个屁好说?再说咱是粗陋军汉,哪有嫌弃别人的分儿?小杜啊,咱是丘八,能跟那些读书人一样,花前月下一套套地整?看对眼了,就问人愿意不愿意,反正战场上,一眨眼指不准就死球了,要不问出来,心里留个结,走都走得不痛快。你师父够厉害的吧?说去也就去了,唉……”
张七郎话方一出口,他老母亲便从外面进来,叉着腰指着张七郎咒骂着:“你吃了猪油蒙了心么,还是这花妖把你迷成这样?正一品的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脸面,全都不要了,跑流沙镇去做什么?”张七郎挥手让阿尔特弥斯进房去,免得老母看着她愈加生气,然后便只是闷头喝着酒。老人转头见着杜三郎,便道:“小杜,你师父呢?给老婆子叫他过来!俺家小七给他卖命几十年,总算有个出身了……这叫什么理!”
杜辟听着,眼眶不禁红了起来。白袍队都是古虎餐养大的孤儿,说是师徒,其实也是近似父子的情分,任他战时如何运筹帷幄,平日里如何能说会道,处理政务如何得心应手,此时已说不出话来,匆匆一拱手,逃也似的出门去了。
卫将军陈延的大宅子里,生着地火龙,奴仆已将晚饭几十样菜陆续摆放上桌,新嫁入门的将军夫人看着难得回家吃饭夫婿,小心地待候着,说几句中京新贵圈子里流传的笑话,陈延这餐饭吃得很是开心。
“对了,管家呢?”
将军夫人不经意地道:“那厮手脚不干净,昨日为妾所觉,便教家丁杖毙了。新来这个,看着倒还伶俐。”
“嗯,让他按这单子,每人做春冬衣十套,再赠五百两盘缠吧。”陈延掏出一张条子交给夫人。那些都是军中的旧袍泽,多是伤残预备着回乡的,虽说大帅自朔方定的规矩,官府自有补助,但他还是想为这些老兄弟尽点力。
陆老相爷似乎完结了他青史上的使命,大战结束之后,身体愈来愈差了,一日间能清醒理事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时辰。“天波,你倒是如何打算?”他之所以联同史官,来做古虎餐仍在人世的文章,却不是闲得发慌。
在陆老相爷面前,陆天波仍是依旧的不成器,他急切地道:“此间已是太平,古虎餐也已身死,孙儿寻思着,择日公开身份,联系军中旧部。张七郎据说是要辞官去流沙镇的了,加上他要娶那西陵妖精,疯骑军里其他人等也渐渐不奉他为首了,待得张七郎离了中京,尽起军马,一发复辟,还我凌家天下!”
“荒谬!你怎地这般不争气!”陆老相爷很是无奈,但却见陆波脸上露出怯容,又想着自己会否太过严厉了些,闭上那重重叠叠松驰的眼皮,过了好一阵才睁开眼,好生对陆天波道:“便要复辟,也不应你来挑这个头……你怕是不知道吧?古虎餐,怕是还活着,若不然,老夫何必作这场戏?”陆老相爷要做的这场戏不是给天下人看的,是给可能还活着的古虎餐看。
“你亲眼看见大帅活着?”李镇南在章台街的勾栏里一把扯过同袍的衣领,急急地问道,“大帅真的破困而出?”左右亲兵早已把无关人等驱赶出去,在门处扶着刀柄把守,十尺之内便是一只虫儿也难飞进。
那被李镇南扯着的校尉苦笑道:“哪里还有假?两个疯骑军拿着我的备用衣服上去给古帅的,然后古帅便和那个叫白霁仙的女修真飘然而去了。我当时也愣了,还问了一句:大帅,这仗就要赢了啊!您老必是公侯万代……”
“大帅怎么说?”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然后扯了块布写了这张东西,叫我给杜三郎送去。现时到处都在说大帅死了,而那些大人明明没见到大帅,又在骗百姓说大帅还活着。我就寻思着,是不是拿这块布给杜三郎呢?如果给了,那不是……”
李镇南本来是属意疯骑军的,只是当年古虎餐见他手底功夫与张七郎他们相比显得稀松,反倒是统兵颇有些能耐,就劝他在朔方军里做个统兵的校尉。但他对古虎餐的那份崇拜、愚忠,与正牌的疯骑军不差半分。于是连忙摊开那块从战袍上割下的残布,仔细看了,只见上面大约是在战场上随手拈来的焦木,写着疏疏数十字:“天下太平,予终得避世。未尽世事托于谁?杜家有英才,及冠字子腾。诸公若计拙,平章可委身。”
那字写得极潦草,疏懒的神色跃然纸上,几乎一看便是古虎餐手笔。李镇南只激动得双手发抖,喃喃道:“好!好!”便再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门外有亲兵叩门,却是跑来加茶水的小厮被放哨的亲兵拿下,来问李镇南如何处置。古帅不在中京之事,岂可外泄于市井之间?也许这小厮什么也没听到,但也许他耳力过人,十尺开外隔着门户仍能听到。战场上杀人如草的李镇南根本就没有犹豫,只是冷然道:“取十两银子给他家人,便说被西陵潜伏的余孽所刺。”把手一挥,卷起那块残袍自出门去了。
中京在这两三个月内,虽然未曾尽复旧时繁华,但那清理出的西直门大街上,引车卖浆之流已四处可见,长街两旁的小摊档都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当铺街头开了两家,街尾临出城门处又开了三四家。若不是插着草标卖儿或者自卖以活口的人实在太多,倒颇有几分太平年月的味道。
一队马车约莫二十数辆,还带着二十来匹空鞍无人的战马,缓缓从西直门大街向城门驶去。前面开路的十七骑疯骑军,盔甲用油脂擦得光亮,仔细看去却能发现上面有刀砍的痕迹、箭射的凹陷、魔法的腐蚀。修补一套这样的盔甲所耗费的金钱和材料,可能会比重新购置一副全新的要贵上七八倍,不过在如今的年月,这便是疯骑军招牌式的装束——他们视盔甲上每一处旧创为是男儿的豪迈和荣光。
车队后面还有七八十名披着白袍的年轻人,他们尽管也骑着马,却没有前面十七骑抬头挺胸的气势,看着那些插着草标的苦人儿,这些披着白袍的年轻人都纷纷别开脸或是低下头,不忍去看。
行在长长的西直门大街,这支沉默寡言的队伍连一点声音也没有。直到那些白袍的年轻人里,有一个策马走近同伴,低声道:“三郎,我不走了。若任由这块大地上的民众过如此凄惨的日子,我等一身本领学来又做什么?与其让那些贪官污吏尸位素餐,不如尽我一点绵力……”
边上有同窗叹息道:“郑四,你也不过一个脑袋两只手,你留下来又能做什么?”
“做得一事,便是一事;不做,终无一事以成。”那个被唤做郑四的平静地回答,显然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冲动。
杜三郎摇了摇头,示意他们不要再争吵,只是对郑四道:“我不阻你,但你切记今日之言。”郑四在马上一抱拳,便向队尾奔去,一时间随他而去的有十数人,他们选择了与马队相逆的方向,用看待逃兵的眼神送别自己的同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