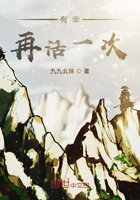(1)
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第一年,梭罗开垦了一公顷的广阔土地,种土豆、玉米、豌豆、萝卜,种的最多的还是豆子,吃不掉的就拿去卖。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单调生活相反,梭罗常常进城,也经常邀请朋友到他的小屋中参观、做客,他甚至还举办过一次大型野餐会,以倡导废奴运动。
关于梭罗在湖畔隐居时的生活,1994年出版的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梭罗”辞条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吃野菜野果及他种的豆子。梭罗的母亲和姐妹确实周六常来看他并带来糕点,梭罗不想拒绝这些食品而伤害挚爱他的母亲的感情,他用这些糕点来招待经常来访的客人。他的朋友施奈德回忆说,梭罗确实有时去父母家或爱默生等朋友家晚餐,但这些拜访并非是因为他不能养活自己,或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孤单,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家庭与朋友,感到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邀请,他自己实际上希望这样的事更少些。
但依然有谣传中的“刻画梭罗入木三分”的事件:每当爱默生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铃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越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这一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因为要听到晚餐铃,一英里半显然是太远的距离。即便能听到铃声,住在一英里半(约合五华里)之外的梭罗竟然总能“第一个”到,不也是同样奇怪吗?
(2)
爱默生解释梭罗的隐居时说:“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梭罗的选择是面向自己的内心的,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以前的生活:
一个人参加展览会,期望能发现一大群男男女女聚集在那儿,而看到的只是劳作的公牛和干净的母牛。他前往一个毕业典礼,期望能发现这个国家真正卓越的人,结果,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淹没在那一天里,以至于他只好远离了演讲人的视线和话语,以免在他周围的无实体中失去自我。
他确信历史上记载的最积极的生活总是不断地远离生活,而现在,他实现了远离生活而同时又是真正的生活。
《瓦尔登湖》中肯定了这种真正生活的意义: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地呆上一天,那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是不被打扰地呆上一年,那可能会令很多人发疯。对于梭罗来说,真正的孤独并不仅仅是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而是一生。除了爱默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梭罗的交际面很窄,甚至在他与爱默生之间也时常产生隔阂。至于与女人的交往更是令人悲哀,母亲和妹妹是他交往最多的女性,他甚至比凡·高还要悲哀,在世几十年竟没有女人主动爱上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认为,梭罗一生的精力没有用在讨女人欢心上,而是倾力抒写《瓦尔登湖》。正因如此,美国人才有了这本让他们骄傲的奇书。
更重要的是,梭罗对于孤独与寂寞有与众不同的理解:
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厕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更寂寞。一个在思想着在工作着的人总是孤独的,让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寂寞不能以一个人离开他的同伴的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学的学生,在剑桥学院最拥挤的蜂房内,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个托钵僧一样。农夫可以一整天独个儿地在田地上,在森林中工作,耕地或砍伐,却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工作;可是到晚上,他回到家里,却不能独自在室内沉思,而必须到“看得见他在那里的人”的地方去消遣一下,用他的想法,是用以补偿他一天的寂寞;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学生们能整日整夜坐在室内不觉得无聊与“忧郁”;可是他不明白虽然学生在室内,却在他的田地上工作,在他的森林中采伐,像农夫在田地或森林中一样,过后学生也要找消遣,也要社交,尽管那形式可能更加凝炼些。
爱默生说:“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在木屋里,在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梭罗像上帝创造的那个亚当一样,纯朴而勤奋地劳作,因为没有夏娃,他永不被诱惑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又像古希腊的那个哲人芝诺潜心于阅读思索,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于是,没有夏娃的一种生存境界被营造出来,这种生存方式充满诗意又充满诱惑,让后来的很多美国人向往不已,甚至在20世纪初引发了重返自然的生活风尚。
(3)
梭罗还有一件入狱事件,虽然和他的独身生活无关,但这件事一样可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是在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拒付这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走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州政府也看不到的丛林中。
(4)
梭罗之所以能孤独一生,跟他禁欲的生活态度很有关系。他几乎弃绝了一切感官享受,他用想象中的高处生活理想扑灭了人性中的七情六欲。
在梭罗看来,放纵性欲是不洁的,他写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它有着“官能的、像爬行动物一样”的本质,“也许难于整个驱除掉”,甚至它自身就很健壮,“我们可以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贞洁是人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
尽管极力压制,梭罗还是感到由于自己的性欲而产生的罪恶感,他公开坦白:
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究竟如何,但我发现很难做到贞洁。据我看来,在我同别人的关系中我可以贞洁,然而我发现自己并不干净。我有使我羞愧的理由。我很健康,却不贞洁。
对于梭罗来说,贞洁的生活是那种最严格意义上的节欲和禁欲。
梭罗的一个朋友哈里森·布莱克在新婚时曾收到梭罗关于《贞洁与肉欲》的一封信。在信中,梭罗除了夸大了异性爱的尴尬外,还声称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性行为都是“淫荡”的。可以想象,和妻子沉浸在蜜月中的哈里森·布莱克读这封信时是何等的尴尬与无奈。这样的梭罗如果有了妻子,那真是两个人的痛苦与尴尬了。
梭罗对味觉的享受极端反感,味觉几乎成了他不乐意说出口的胃口的代名词。在瓦尔登湖畔,他把食物的烹调降至最简单原始的方式。他的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套被褥,有几件简单的炊具和几件换洗的衣服。1849年,梭罗写道:如果我听从了我的天性的虽然最微弱,却又最持久的建议,我就知道这些建议将不会把我引导到什么极端去,或者把我引导到疯狂中去;可是当我变得更坚决更有信心时,前面就是我的一条正路。
禁欲生活虽然获得高洁感,但因为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跟自我中的本我做斗争,难免让人感到疲惫与绝望。社会学者经常发现,许多前半生坚持过清教徒般禁欲生活的人往往在人生的后半段突然丧失理智,极端放纵欲望,难以自拔。梭罗似乎也有过出现这种情况的迹象。1852年,有关性的困扰重新出现在梭罗的日记中,他似乎一度出现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怀疑、失望,精力衰退、冷漠、僵化,这些词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直到1852年晚期到1853年的日记中,有关性的困扰才在持续数月后消失不见了,梭罗又回到了禁欲矜持的状态。
(5)
到了1854年,终于有出版商同意出版《瓦尔登湖》了。但开始的时候影响并不大,甚至还有人公开讥讽作者的写作姿态,但乔治·艾略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认可了他的生活方式和著作。
1862年,梭罗由于肺病的复发而去世。但肺病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的独居生活给他的健康带来了损害,以至于45岁就离开了人世。
现在,不但是美国人,全世界身处闹市的人们都向往瓦尔登湖,甚至某天也会有一种梭罗一样真诚的冲动:以瓦尔登湖了却一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能是由于某件事的失败而引起的失意而已,说说而已,并不当真,也并没打算实现。某天,那件事成功了,瓦尔登湖又被抛在了脑后。所以,通常情况下,瓦尔登湖只是失意的人们为自己找到的貌似潇洒的开脱词之一,毕竟那也是一种著名的不失身份的生活方式。
直到今天,能像梭罗那样去过整洁而素朴的生活的人还是屈指可数,但这种结局可能正是梭罗所期望的。他跟某些传教士不一样,他从不想为所有人树立一个生活的榜样,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