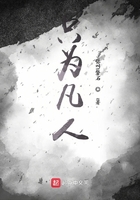端阳节划龙舟,在当地很盛行。一般的,一个村子一条龙舟,一条龙舟十个桨手,一个鼓手。桨手是本村挑出来的好汉,代表本村的形象,去参加划龙舟竞赛。谁被选中为桨手,那是一份自豪!也有的在划龙舟中大显身手的,被姑娘看中,结为秦晋之好的。心头荡漾着春波的姑娘,胸中燃烧着情焰的小子,都把端阳节当做一个快乐的节日。
城被选为石湾的桨手,是最近两年的事。石湾的桨手暗暗下了决心:这第一今年还得拿回来!
早饭时,叶子给父亲和城各斟了一杯雄黄酒。自己则将雄黄酒润湿太阳穴。说是雄黄可驱蚊虫,就连毒蛇也不敢叮咬。
“你去不?”城问。
“爷爷呢?”叶子分明想去,但又怕自作主张,惹得父亲不高兴。
石磊想了想,说:“想去就去吧!呆在山里也闷得慌。只是外面兵荒马乱,要格外小心才是。”
叶子点了点头。
不至于太惹人,叶子换下了那件红衬衣,穿上一件白色棉绸短袖褂子。裹在人群中,也不怎么出众。只是那身段无法改变,身上总有热辣辣的目光。她拂也拂不落。
划龙舟要开始了。
长江正是汛期,江面宽。龙舟赛场设在一个很大的水湾,起点和终点均插着小黄旗。叶子站着的地方,正处在终点。终点距起点大约千步之遥。岸边上都是看热闹的人,皆勾了脖子,等那鼓声咚咚擂响。
岸边突然骚动起来。
三个日本鬼子横背着长枪,摇摇晃晃向岸边走来。他们东瞧瞧,西望望,眼睛滴溜溜乱转。
年轻一点的妇女,赶紧往人丛里躲。
一个鬼子直向叶子走来。看见她窈窕的身躯,发出一种古怪的笑。他一笑,众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声刚落,后面的两个便咧着嘴走上前来,贪婪地盯着叶子。
叶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只感到浑身有虫子在爬。她很恐惧,不由得哆嗦起来。
叶子正要往人群里钻,便被鬼子拦腰箍住。这个鬼子正是在她家挨了两记耳光的大平和田。村里人也认出他来了。叶子想挣脱大平和田的手臂。大平和田箍得很紧,她一时挣脱不得。他腾出一只手来,伸进叶子的胸脯,随即发出一阵淫笑。
村人被激怒了,一齐吼道:
“放开她!”
如雷霆,在大平和田头顶炸开。大平和田被这声音震慑住了,松开了手。另两个鬼子面面相觑,气色很虚。有一个鬼子竟面孔发白,不知所措。当鬼子发现所有的人只不过瞪着眼睛,两手空空,一根根柱子一样立在那里的时候,自己的手便得意地握紧那枪,便壮了胆,黑色的枪口在人前晃来晃去!
叶子见鬼子松了手,拔腿就跑。
正在这时,划龙舟开始了。
只闻岸边“咚咚咚”三声鼓响,江里八条龙舟的八个鼓手,站在船头,几乎是一齐擂响了各自的铜鼓。一瞬间,鼓声震天,像落地雷“砰”地炸开,轰击着江岸。那鼓声如漫天洪波狂涛,裂岸而去,一下子淹没了岸边站立的人群。
这突然的鼓声,使岸边所有的人都受到强烈震撼。他们的眼睛突然一亮,有了绚丽的色彩。他们和那鼓声一齐吼,“加油!加油!”声音铺天盖地。
鼓声显然构成一种威慑的力量,使三个鬼子在几分钟之内惶惶不安!他们东张西望一阵,确信对自己构不成实际的威胁时,便又哇哇乱叫,追起叶子来。
大平和田正要抓住叶子时,一个汉子伸出腿,将他绊了个嘴啃泥。他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咧着嘴,“呀呀”直叫。他慢腾腾地端起枪,又慢腾腾地拉开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又脆又亮,周围的人都听得耳根发麻!那汉子猛扑过去,大平和田这时抠动了扳机!子弹像水里的蚂蟥,一下子咬住那汉子的腿,那汉子扑倒在地。大平和田怪叫着爬了起来,对准那汉子,又开了一枪。那汉子痉挛了一下,就一动不动了。血在弹孔处汩汩涌出,咕嘟咕嘟冒着鲜红的血泡。
大平和田哼了一声,向正在与叶子扭打的那两个同类走去。他走到他们身边,见他们扭打毫无结果,很蔑视地盯了他们一眼,嚎叫了一声,那两个鬼子便住了手。
大平和田慢腾腾地打开刺刀。刺刀白花花如一条僵硬的毒蛇,顶住叶子丰满的胸脯。叶子从刚才愤怒的挣扎中渐渐平静下来,她以为他要把她挑死。鬼子把刺刀用力向上一挑,那件白棉绸短袖褂子“嘶啦”一声撕成两半,叶子正在惊恐之中,鬼子又用刺刀挑碎了那件贴身的背心。叶子“哎哟”一声,忙用双肘靠紧,遮住裸露的胸脯。她的细腻而富有弹性的肌肤和那圆滑柔润的双肩,在阳光下闪耀着白瓷瓷的光泽。
大平和田把枪交给另一个正在淫荡地大笑的鬼子,一步上前,把叶子按倒在地。
在黑洞洞的枪口威逼下,人们不敢近前。大平和田吞噬着叶子的生命和尊严。叶子竭尽全力抗拒着他,那喘息和臭气喷在她的脸上。她想大叫一声,但她无力开口。肢体像被切开不复存在了。
江上的鼓声越来越近。鼓声轰轰隆隆,在人们头顶擂过。
生命的蹂躏不死的力量支撑着她,叶子奋力推开了已经瘫软的大平和田。她爬起来,向江边跌跌撞撞地跑去。
大平和田举起了枪。
八条龙舟呼啸着,翻动着浪花,正要压过来。
枪声响了!
叶子应声倒入江中。
枪声激怒了八条龙舟。八条龙舟如一条巨龙,前后一线,倒海翻江般扑了过来。桨手哪还顾得上什么龙舟竞赛,纷纷跳下水,朝叶子游去。
江水已经染红了一片。
五
一丝风也没有。头发丝儿也不动一下。天空像烤得冒烟的锅盖,闷得人要死。
城不吃不喝,已有三天了。
石磊颠踬着,摸到城的床沿:
“你该吃点东西了。”
“不想吃。”
“这样闷着不是个事。”
“这日子没法过!”
“谁说不是?叶子,你姨,都死在日本矮子手里。”
“这口气我咽不下!”
“谁能咽得下!”
父子都不说话。静了一会儿,石磊拿来一把蒲扇,为城一边扇风,一边说:
“可我们还得活命啊!这么大热天闷在屋里,还不闷出病来?!”
“这样活着不如死了好!”
“这是什么话?没出息!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仇,总有一天要报!”
“爷,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你想说,你就说!说错了,爷也不会见怪!”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爷不要说伢不孝!爷可要挺得住。”
“你想搞么事?”
“寻日本矮子去!”
“你用什么家伙?”
“拳头!”
“那不行!你没拢上他们的边,他们就先把你搞倒了。他们有枪!”
“他们发现我了,我就跑!”
“跑?你能跑得过枪子儿?”
“……”
“你岳母屋里有铳!”
“你是说用铳?”
“不用铳用么事呢?”
“只怕是岳母不肯。”
“你说打猎用。”
“山里又没什么好打。”
“就说打狼!”
“……”
城翻身坐起,几口喝尽了父亲给凉好的稀米粥。用手掌在额头抹了把汗,再一甩,一串汗珠成一线砸在地上。他忽然来了精神,从床上一跃而起,借铳去了。
六
土地被烤裂,村子里连狗都不叫,那是七月八月的事情。
石磊父子一直在寻找机会。
那根老铳,很有了些年头。据说还是叶子的曾祖父传下来,只是多年未用,到处是锈。那锈点点块块,如同老者脸上暗紫色的老年斑。石磊毕竟摸过五年枪,擦枪还有些办法。他用一块纱布,蘸上煤油,几经擦拭,老铳霍然一亮。
那铳被城背着,形影不离。
九月来临的时候,一阵阵的凉风也就吹到了龙首山。正当人们对残夏厌倦时,秋天又以它的果实散发出芬芳馥郁的草木气息,唤起人们的希望。
那些日子,站在半山腰,可看到长江上游漂下来一只又一只日本兵船。那船头都飘着一面白旗。船上没有什么躁动和喧哗。
“为么事挂白旗呢?”
“挂白旗挂红旗,还不是由他们高兴!”
“是从汉口下来的?”
“可能是吧!”
“这是去哪儿呢?”
“哪个晓得!”
“你看你看,那只船斜了!”
“好像要沉!”
“沉了才好哩!”
“这几天每天都有沉的!”
“这才叫报应呢!谁叫他们造那么多孽!”
“江上漩涡多,只怕是他们来得去不得!”
“全沉了才好!”
“你看真沉了。”
“哈哈!沉了,沉了!”
“狗日的也有今天!”
石磊那些日子没有出村,看不到那些日本兵船和那些白色的旗帜。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日本战败,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七
石磊父子在郁悒中等待的机会,也终于来临了。
那天,云彩很淡,天空尤显其高。日头照到茅屋顶的时候,三个日本鬼子背着枪,沿着石板小路,嘻嘻哈哈上了山。
村子里便有人喊:“牛吃麦子啰——”
村子里一阵鸡飞狗叫,一会儿就空了。
鬼子们站在村头,把步枪取了下来,三杆枪呈三角架在一起。那个高个子鬼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正在东张西望,这是他第二次到石湾了。大平和田来过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另一个鬼子是第一次来。
他们正准备照相。
石磊和城一早就上了山。锤声钎声石头声响了好一阵。突然听到村子里有人叫喊,晓得是鬼子来了。立即丢掉那锤和钎,提起铳,城搀着父亲,沿着竹林小路,急急忙忙地溜下村来。
三个鬼子在照相。
快门咔嚓咔嚓响过一阵,两个鬼子头碰头在一起嘀嘀咕咕。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指指,最后走到石磊门前,大平和田从裤兜里取出洋火。
手提照相机的高个子大喝一声,大平和田捏着一根洋火,不敢擦。
另一个鬼子叽里呱啦,带着讥笑的表情,显然是在怂恿那个手捏洋火的大平和田。
手捏洋火的大平和田显得颇为得意,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擦着了洋火。
手提照相机的鬼子又大喝了一声,显然是在阻止他。
另一个鬼子也干嚎了一声,分明是在怂恿他。
大平和田依旧吹着口哨,那火苗飘忽着,舔着了一把茅草,茅草呼呼燃烧着。手提照相机的鬼子急忙跑过去,要从他手里接下来。大平和田连忙将燃着的茅草扔在石磊的茅屋檐上。那火顿时呼哧哧而起,屋顶的竹梁烧得啪啪脆响。炽热的气浪使周围的树叶、竹林发出恐惧的簌簌声。火舌卷曲着,如一条蛇,在房顶上窜来窜去。
鬼子们被火光映得通红。高个子鬼子站在那儿,像发呆。另两个鬼子得意地吹着口哨,高个子鬼子不肯跟他们照相。他们把照相机拿去,以燃烧的房子为背景,幸灾乐祸地做出各种丑态,自顾自地照了起来。
石磊和城这时离鬼子大约十来丈远。看不清鬼子的脸孔,只看见房子在燃烧。父子两人的脸都憋得通红,城就趴在地上,催父亲快装铳子铳药。石磊一言不发,找了个地势开阔、便于放铳的土坎趴了下来。
铳子铳药上好了。城把铳要了过去。
城把铳伸了出去。
城的手战栗着。
父亲低声地说:“还是我来吧!”
“不,我来!”
“看你,手抖得邪乎!”
“不碍!”
“那就快放!”
城瞄准着鬼子。高个子鬼子走到一棵老槐树下坐了下来。槐树背后是一个茅棚。茅棚四周全是堆起的干茅草,那两个鬼子仍在照相,刚好对着城的铳口。
“只能套住两个。”
“三个都要套进去!”
“先干掉两个!”
“莫!放了一铳,再装铳子铳药来不赢!那一个就能去捡起枪打我们。”
“那就等等?”
“我来看看!”
“不!这一铳我打定了!”
“你可别慌!”
城咬着牙。腮帮子格格响。
石磊见另两个鬼子照完相,也走到老槐树下,坐在高个子鬼子身边,便问:
“可以了吧?”
“可以了!”
“扣扳机!”
……
“么事扣不响,爷?”
“要扣到位,还是我来。”
“不,我能行,再来一次。”
“手莫颤。”
“嗯。”
“扣。”
“砰——”铳响了。沉沉的、闷闷的声音如同浑厚的男低音在山谷回荡。铳子儿雨点般洒去。三个鬼子大约全淋湿了,齐齐鬼叫了一声,倒了下去……四周空旷而寂静。只剩那房子劈劈啪啪地燃烧,浓烟横在空中,像倒淌的一条黑河。
这一铳响的那一瞬间,父子俩头脑里只有铳响的声音。打那一铳,城像是耗尽了多少年的精力!他散了架一样,无力地扑在地上,额头冒着豆大的汗珠。用铳打人,毕竟他还是第一次。
这一铳终于打出去了。至于打着没打着,城心里实在没底。
“打着了吧爷?”
“好像打着了。”
“去看看吧爷?”
“去看看。”
城只晓得,在扣扳机的一刹那,自己用力很猛。不晓得那铳托就很自然地压下了一点,铳口便翘起,铳子就打高了。
三个鬼子果然没打死。但都被铳击中了,只是没打在要害处。鬼子被突然的铳响吓瘫了,不知道是什么武器在对他们射击,那种声音他们没有听过。他们不敢抬头,趴在地上如缩脖子乌龟。
过了一会儿,鬼子见没有动静,就开始向架枪的地方悄悄地爬行。那三支枪离他们只一丈远。
这时父子俩一前一后走了过来。
石磊一看,鬼子没死!他迅速取过一支枪,端在手里,把另两支枪向后扔得老远。他端枪的动作那样熟练,三个鬼子以为是遇到了新四军,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哆哆嗦嗦。那个高个子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求饶:
“开枪的不要!开枪的不要!”
石磊晓得手中是一根日本三八大盖。他从容地拉了枪机,把子弹推上了膛。城见父亲会熟练地使用那杆枪,很是有些意外:
“你会用,爷?”
石磊微微点了点头。
石磊一句话也不说。紧咬着牙齿,面孔如岩石。他稳稳地平端起枪。
那三个鬼子突然平静了下来。
“开火吧,爷!”
石磊眯缝着眼睛,进行瞄准。
“哇……”那个高个子鬼子突然大声哭了起来。
“开火吧,爷!”
“开枪的不要!开枪的不要!”鬼子急促地呼叫着,并摆着手,“开枪的不要!饶命了的我们。开枪的不要!我们就要从中国的离开!让我们回家的你的大大的好!”
石磊鼻子哼了一声:“让你们回家?”石磊捏紧了枪,“你们这些畜生,还记得有家!”
高个子鬼子哭丧着脸:“有的有的大大的有!我家有七十岁的妈妈!你的开枪的不要,放我们回家的,你的大大的好的!”
石磊平端着的枪,晃动了几下,仍旧一言不发。这时候求老子放你们回家?你们杀人放火的时候,怎么不想到我们也有家?你们这些两条腿的狼,喝了我们多少中国人的血!把你们千刀万剐也不解我们心头之恨!晓得吧畜生!
高个子鬼子看着石磊的脸。他从石磊愤怒的表情看出,石磊对他们恨之入骨!他突然认出来,面前这个拿着不知是什么武器的中国人,不是别人,正是那燃烧的茅屋的主人!他没有认出石磊的脸,却认出了石磊那只飘摆着的空裤筒。几个月前,自己还喝过他儿子的喜酒啊!他突然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擂着身边那个放火的大平和田,还哇哇地说着什么。大平和田也不动,由着他打。
石磊看在眼里,鬼子的话虽然听不懂,可以看出是在埋怨那个鬼子。石磊趴在地上的时候,看见是那个矮鬼子点的火。石磊就想:你点我那茅屋算得了什么!我会到山上去砍茅草啊!你也可以把山烧光,但那雨一落,逢了春,新茅草还会突突冒出土啊。日本矮子,你们虽恶,虽毒,可你们总不能把这山这土如何得了吧!石磊见鬼子停住了打,也不再哭,右手食指放在枪的扳机上。高个子鬼子突然大叫:
“开枪的不要!开枪的不要!”
“开吧,爷!”
“我到中国的,也是不愿意的!”高个子鬼子说。
城大喝一声:“不愿意怎么来了!”
“抓来的。”
“抓来的?”城和石磊有些惊异。
“是抓来的!那时我正在大学读书,抓来当兵了的!”
石磊把平端着的枪缓缓放了下来,一只手提着。
高个子鬼子见石磊放下了枪,轻轻嘘了一口气。他对石磊说:“我在你家的米西过的。”
石磊听不大懂。
鬼子用手做成一个酒杯模样,往嘴唇边一放,成喝酒状。
石磊顿时记起来了,这是那个喝了三杯酒就哭起来,说他正准备结婚被抓来当兵,未婚妻不知如何的鬼子。
另外两个鬼子一声不吭。城盯着他们,一个满脸横肉,年龄也就二十一二的样子,吓得粗气都不敢喘。另一个就是大平和田,年龄大约二十七八,留着两撇八字胡,下巴上有一块黑痣。
城脑袋像是被人砸了一下,天旋地转,似要爆炸:这不就是七年前害死母亲的那个日本矮子吗?
“爷,把枪给我!”
“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