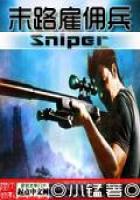后来我们知道,并不是老兵的枪法差,而是中队长这个家伙为了历练我们新兵的胆略,而故意制造给我们补枪的机会。
战争是残忍的,人类也是残忍的,如果撇开死刑犯的罪恶不说,那么中队长就是让我们从此沾上杀人的鲜血,让我们彻底撕破心底间的那层柔软的纸。
那个时候,法院还没有法警,枪决死刑犯就是我们武警机动中队的事。作为机动中队的长官,他必须培养我们这样的射手。何况,1983年开始的严打,到84年时,已经愈演愈烈,不说每个月有死刑犯枪毙,也是隔三岔五地要执行。第一次动枪了后的我们,自然下一次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正射手。
如今,法警第一次执行了死刑犯的枪决后,第二天就会有心理医生给他抚慰和咨询,而那时的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
那天我在回去的路上,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一般难受。中午,我没有吃午饭。晚上,我又没有吃晚饭。不是我故意不吃,而是吃不下。我为什么吃不下,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不想吃,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干,脑海中老是出现刑场的画面,老是出现那个“校长”,以及那个带血的死刑牌。多少次强迫自己不去想,可它偏偏就不听使唤,像秋天最后一轮投胎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但我是班长,即便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可我还要去关照和关心周彪悍。我明明中午、晚上都没有吃饭,却装着很有精神地跟周彪悍去说话。
周彪悍蔑视地看着我,对我的讨好话不予回答,最后被我弄烦了,呛我一句说:“你画胡子一边歇着去!比我还没有承受力,居然还来劝我!要不是我不想当这个狗屁班长,早就没你的份!”
我心底冒火,心说你就是嫉妒我当了班长。我本能地站了起来,想回击,但最后还是控制住了,我一思量,得!他是我们班唯一和我执行过死刑犯的战友,真正的战友——唯一啊——难得啊!
于是在第三天,真正能吃点饭的时候,我将母亲寄给我的苹果选一个最大的,诚诚恳恳地送给周彪悍吃。
第七节 指导员让我明天清早去采访一个死刑犯
一个月后,中队第二次执行死刑犯,我虽然过了那段“周期”,对下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了心理准备,不会再像怀了孕似的。但这一次,中队长选拔8名副射手时,并没有用我和周彪悍这样的“老手”。
我原本以为就这样“没事”地过去了,谁知当天晚上,排长大声喊,说指导员找我。
指导员是管全连的思想工作的,当然,也管宣传工作。但我当时想,是不是某个新选的副射手冒着遣送回家的危险死活不去,而要我替代呢?
那如果那样的话,指导员也就太把我当一根葱,太“关照”我了。
可进办公室后才知道,指导员原来是让我明天清早和中队的副射手一起去看守所,但不是执行,而是去采访一个特殊的女死囚,拍几张照片,回来后写篇报道,反映社会现实,歌颂严打成果。
指导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我们连的战士几乎都对他有好感,此时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心里即刻产生了知遇之恩,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当指导员询问我有什么问题时,我才鼓足勇气地说:“指导员您让我做这么重要的工作,可我从来没有写过通讯报道呀!”
指导员呵呵笑两声,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第一,你的钢笔字写得还不错,我喜欢。你每一次写的思想汇报,条理清晰,语言顺畅,错别字也不多。你初中毕业,文化不是很高,但写作这个事情,不是凡是大学生就能写的;第二嘛,你哥哥是乡政府的干部吧?他有一次跟我的一个朋友来找过我,说要我关照你。我怎么关照你呢?只能从你的特长中寻找。现在这是个机会,就看你的了。”说着,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型照相机,是海鸥牌的,又从堆在办公桌上面的一堆书里抽出一本书,是《新闻写作学》,将书和相机一并递到我手中。
确实,写作这个功课并不是读了大学就一定做得好的。我尽管只有初中毕业,但因受父亲和哥哥的影响,各种故事书、小说看了不少,钢笔字也确实写得可以。因而虽然在指导员面前谦虚,但其实还是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美差的。再说,我从进部队的第一天起,就有上军校的想法。要上军校,而现在这样历练的机会自然是少不了的,也最能给自己加分的。
不过,哥哥跟指导员打过招呼了,哥哥的朋友跟指导员还是朋友,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但现在指导员说了,说明假不了,也说明哥哥对他弟弟的前途是很上心的。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采访任务,但我还是傻乎乎地对指导员说:“写材料、写稿子是文书的工作,我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
指导员不回答我的问题,像压根儿没听到我刚才的话似的,反而问我会不会使用照相机,我回答了参军前哥哥有照相机,教我用过后,他才抓住我刚才话中的那句成语,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还知道越俎代庖?不错嘛!”看我没有积极反应,又说:“做文书工作是要通过努力争取的唷!”说着,鼓励地看着我,然后一笑。
我心里乐开了花,朝指导员敬了一个响亮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