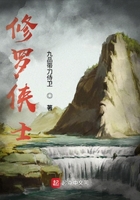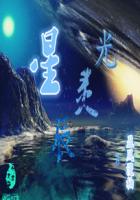霁兰心思纠结,神情恍惚难定,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吸了口气,跪在了脚踏上,一手托着手里的托盘,一手去扶玄烨的身子。不知道是不是玄烨发烧的缘故,霁兰才一接触到玄烨身子发出的滚热气流,就给烫得缩回了手。
“怎么了?”玄烨感觉到了霁兰缩回去手,虽然霁兰的指尖只碰到了他身上散发的气息,却还是有股奇异的感觉已经传了过来,到了玄烨身上。玄烨形容不出,却感觉应该是给天上的电打了般的感觉,全身像给这种感觉走了一遍,四肢百骸脱胎换骨般清爽起来。
“主子,奴才还是唤梁首领来吧。奴才只跟高嬷嬷和雅利奇姑姑练过,从没有在贵主子跟前侍候过茶水的。”霁兰端着托盘跪着,挨着床沿,头也磕不下去,只能把头更低下了,以示恭敬。
“哦,那你们贵主子有麻烦了。”玄烨开玩笑般,却故意做着深沉样。
霁兰的头抬了下,还没看清玄烨,头又赶紧低了下去:“奴才该死。这是奴才的错,跟贵主子可没有关系。”
“你是该死。主子说话,你还敢犟嘴。”玄烨自已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被子划到了腰间,遮盖着。玄烨想着不要吓坏了这只小猫,自己把被子又拉上去了些,遮盖着身子多些,却也只拉到了胸口。
“嗻。”霁兰应着,不敢说话。全身上下已经紧得像根绷紧的琴弦,没有一丝的松懈。只要稍微一弹,怕是就要断了。
玄烨看霁兰没有动作,只能自已伸手从茶盘里取过了漱口的茶,喝了口。等着霁兰把托盘递过来,好吐在渣斗里。没想到霁兰的心已经慌透了,觉着汗水似乎沿着脸颊在往下淌,更是大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含着一口茶水的玄烨又不好说话,又不好咽下去。想笑,又怕把一口茶喷出来。玄烨实在没有办法,先把空了的茶盏放到托盘上。
这一下,霁兰回过了神,身子动了下,却是茫然地动,不知道该往哪儿动,然后才猛地明白,托盘递了过去,头却不敢转过去。
余光还是扫到了玄烨没盖着的胸前脖劲下,心突突地跳,那扫过去的余光赶紧往边上移开。余光是移开了,就是像是有道白影儿在眼前划过般刻在了心里。脸是红着,突突跳的心却慢慢稳了些。
玄烨笑着把嘴里的茶水吐在渣斗里,又拿起喝的茶,揭开茶盖喝了两口,放到了托盘上。
霁兰站了起来,把托盘和茶盏放到了桌子上,心里却悔得要命,觉得她这个御前的差事当得差极了,“扑通”就跪在了那里:“奴才该死。”
“你就只会这么一句吗?”玄烨的心情现在很好。
霁兰不知道怎么回了。她自然不只会这一句。她会的很多,可是在主子面前怎么说,她说不出来。
玄烨抬起了手,指尖点了下脚踏:“过来。”
霁兰走了过去,跪在脚踏下。她不敢跪在脚踏上,跪在那上面,身子就要跟靠坐在床上的玄烨平着了。这是不能想像的,怎么着她也只是一个官女子。
再说玄烨身上只有一条锦被,霁兰的心揪着,真怕那条锦被滑落了,或者掉下了床。这些她都怕,跪着远点、低点,她就觉得会舒服些。为什么会舒服些,她不知道,反正她就是觉得会舒服些。
玄烨的手指尖又点了下脚踏:“坐在这上面,我有话问你。”
霁兰吃惊地抬起眼,才一抬起,那道白影就要闯进了眼里,立刻觉得不妥,又忙垂了下来:“奴才不敢。”
“你连板子都不怕,动不动就‘该死’,让你坐倒不敢了。”玄烨没猜到霁兰的心思,他已经习惯如此赤身睡觉了。霁兰的胆怯小心,让他觉得好有兴致,甚至觉得嗓子也不是太难受,说话自如了许多:“知道不,这叫抗旨。”
霁兰不敢不坐了,却也只敢侧着身在脚踏上蹭着点,把头往床的反方向,窗那边侧了侧。虽然这姿势不舒服,心里却舒服。
只是这么坐了一会儿,霁兰就感觉玄烨的眼睛在自已的脖颈间搜寻。前面干了的细密密的汗珠子好像又要往外冒出来,却不敢躲,也不敢动,就这么僵硬地坐在那。
“你真不怕挨板子?若是说了,不就不用挨了。”玄烨好奇地问。
霁兰的心抖了下,又定了下来,终于还是扯回了那根“针”的事。看来今儿个还是为了那根“针”,前面因为白影的心乱现在倒不乱了。这么多日子,她就想主子们给个定论,可是却一直不给,让她觉得好冤,却是有冤无处伸。人都没说你有罪,你哪有伸冤的权利,霁兰就是这样的感觉。
霁兰的眼睛微微红了,头低了下去:“回主子话,奴才怕的。”
“怕,还不认?”玄烨的声音里充满了调侃,他现在对这个小身子里装的东西很好奇。
霁兰不敢抬头,声音因为有些激动已经带着颤音,可是却透着股坚定:“回主子话,奴才没做,就是给打死也不认的。”
玄烨想到了板子是怎么打的,心里一动:“那挨了板子,若是没死呢?”
霁兰的小脸白了,打板子她没挨过去,也没见过。可听说过,是扒了裤子打的。当众给人这么羞辱,她不死反倒不如死了的好。紫围子里不能自我了断,她只能忍辱偷生,等着一离开紫围子就自我了断,断不能因自己害了阿玛额捏。
霁兰的心里是在这么想,嘴上却回答不了玄烨的话,不能说她想求死,那是犯了忌讳的;更不能说她等着出了紫围子再去死,那就是大不敬了。薄薄的小嘴唇抿得紧紧的,两排小牙咬得紧紧的,低着头闷声不说话了。
玄烨的头侧了过来,仔细地审视着霁兰的侧影,冬日里的阳光隐了下去,朦胧看不清楚,只看到垂着的几缕发丝,在那似微微摆动,却又似凝神不动。
玄烨伸出了手,想把这几缕发丝拨开,好看清楚些,手才伸了一半,恍然间明白了,手就缩了回来:“你若是存了那样的心思,可不光是你的命,你的父母命也没了。就算你日后出了紫围子,这事牵扯起来,难道说还能跑了去。”
霁兰只觉一阵阵汗冒了出来,气血上涌,小脸不白反而红了,这活路没有死路也不给,脱口就说了句:“回主子的话,难道朝廷就没个章法?打奴才板子,是逼着奴才承认。奴才的命是贱命,可是也不能硬逼着奴才承认奴才没做过的事。打了人板子,这天大的冤屈,又不许人以死抗争吗?难道朝廷只许屈打成招,就不许人以死抗争吗?”
玄烨“噗嗤”笑了出来:“好一张利嘴,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那日就你碰过那丝棉,才有的针吧?”
霁兰把头往窗那边又微微扭了下:“奴才是抱过那丝棉,可不代表奴才就在丝棉里藏过针。碰过丝棉的又不止奴才一个,为什么就只怀疑是奴才呢?”
玄烨的笑收了,霁兰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若霁兰真做过这事,佟氏也不会这么随便地跟自已说。看来这是个无头案了。
这“针”的事说不定就是个无意之举,那些奴才怕牵扯到她们,才想着找个人来垫背。既然扯了,定然就要咬死了。回头看是什么奴才,让她们的主子好好教训下就是了。奴才偷滑固然可恨,但也不能事事揪着,若是这样,岂不是无可用之人了。
玄烨又笑了,想着那日瞧着的模样,挺温顺和婉的,怎么今日看上去却是这么个犟性子:“你不记得我是谁了?”
霁兰还在那为自个儿的不白之冤有点愤愤不平,哪曾想玄烨转到了这话题上。细细地思量了下,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回主子的话,奴才只知道主子是主子。”
这话说的,他不主子,难道还能是奴才了。玄烨伸出了手,勾住了霁兰白玉般的小下巴,轻轻地往自己这边带着:“你好好瞧瞧,我是谁?”
霁兰的身子抖得厉害,为什么要让她看主子是谁,难道是因为刚才她说那番话?细细地在心里过了遍,看来真的是主子要让她明白她错的有多离谱了。
不敢抗拒,不敢求饶,霁兰被动地由着玄烨的手勾着转着头,
玄烨的手停止不动,却不放开霁兰的下巴,反而轻轻地托了下:“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霁兰低低地开了口:“奴才该死……”
“怎么又说该死了,让你看,你就看,这是旨意。”玄烨温柔地说。
霁兰的神经放松了,只是一放松,眼帘还没抬起,那抹白影仿佛就在心间里晃着了,隐隐绰绰,知道一抬眼定然看到。不抬眼,都已经觉得在眼前晃着了。
“怎么了?看看,我是谁?”玄烨的声音更加温柔了。
玄烨自己都没有发现,这是他从没有用过的一种语气。他用过恭敬孝顺的语气,那是对太皇太后和太后;他用过平和的语气,那是对后宫;他用过威严的语气,那是对臣子和仆从。他用过各种语气,独独没有用过这样温柔的语气。
霁兰的眼慢慢抬了起来,在这种温柔的话语间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