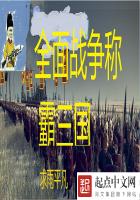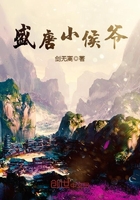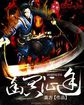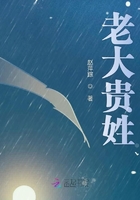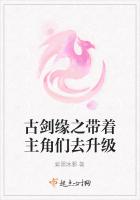上回说到那刘焉谏议灵帝重置州牧,以增地方兵权,众官及十常侍皆纷纷附议,那灵帝自思亦是一条万全之策,恰待拟诏传檄全国,只见一人站出,大叫“不可”众人视之,乃是王允,时任御史之职。那王允乃名门大族,世代官居要职,自幼随父出入官场,及至弱冠出仕,与之结交者甚多,是时王允在朝上连说不可,灵帝便问缘由,那王允不紧不慢,说出一番道理来。
“陛下,周时武王分封诸侯,初时尚听周室王命,然幽王之乱,平王东迁后,遂成春秋、战国乱世,究其深因,皆因王室日衰,无权亦无力管辖矣,故而嬴秦一扫六国后,始称皇帝,统文字、齐金银、平度量衡、所有制度,皆以六数,以为集权,故而海内能称一统,然秦筑长城、修阿房、建甬道,严刑苛法,不恤民力,故而高祖起义,推暴秦而建汉,汉之分封,非刘姓而不王,以为血脉相承,可保汉室矣,然七王之乱,亦使天下震动,概而论之,皆分封之祸也,今陛下重置州牧,释兵权于地方,无疑于另类分封也,况兵者国之大事,岂能随意予地方州牧?若如此,则春秋战国之祸不远矣,望陛下善察之。”
灵帝听罢,亦觉有理,那刘焉反驳道:“王御史只知论,而不知战,浅见也,若论当下之兵事,臣以为当速战速决为上,如今黄巾贼为乱天下,遍布幽、冀、豫、徐,此四州皆乃重地,若不及时剿灭,待贼会师一处,西向洛,宛,则洛阳、长安危矣,届时人心不蛊,天下只知黄巾,而不知陛下也。”
那张让暗自听罢,觉得刘焉之见颇有道理,但见王允也不甘示弱,当下两人就在那朝堂上争论起来,乘乱之时,他便上前往灵帝耳旁底言几句,暗示灵帝支持刘焉,灵帝默默点头。
当下王允又说道:“黄巾之乱,一是天灾,二是民生凋敝,若太平之日,防灾得当,岂有天灾之后而出人祸之事?况天下之民,多乃愚者,秦之谓:‘黔首’也。男有耕,女有织,仓廪实,衣食足便可,至于他求,则可无视之。周之国人暴动,秦之陈胜、吴广,今之黄巾之乱,统是民无地可耕,无粮可食,古今一理。究其深因,统是十常侍祸乱朝纲,导致民生多艰,望陛下及时除之,以正朝纲,黄巾之乱,当不攻自破也。”
在朝众官听罢,面面相觑,要知那十常侍可是在朝中一手遮天,稍有违他们的意思,轻则贬官流放,重则刑罚加身,为乱之始确有几个正义之士大胆上书,一数那帮宦官劣迹,但皆被张让等人暗中使坏,或被刺杀,或贬官,或入狱毒打,弄的朝堂之上,人心惶惶,所以日后朝堂议事,众官为保自家性命,噤若寒蝉,只来当个观众,看着十常侍和灵帝演戏,只需退朝时口称附灵帝、十常侍之议而已,久而久之,众官麻木不仁,那十常侍却愈发气焰嚣张。
那王允乘着年轻气盛,只指十常侍罪状,众官依旧犹如梦中,王允孤掌难鸣,只好作罢,那边张让原是个狡猾之徒,见王允指着骂自己,岂能轻易放过,然灵帝尚在,不好发作,便哭哭啼啼的做妇人状,自言对陛下汉室忠心耿耿,所作所为,皆是为民为朝,岂有祸乱朝纲之理?
灵帝是个心软的人,见张让等众宦如此,便让张让等先行退下,也没有怪罪的意思。王允、刘焉一看此景,不觉摇头,两人虽在平乱事上政见不和,然十常侍之乱却是心照不宣。
灵帝见张让等退下后道:“众官勿言,朕意已决,打算重置州牧,速速招兵平乱,不知众卿有何人选?”众官默不作声,此时刘焉见灵帝采纳己见,便应道:“此议既是臣提出的,便由臣先做表率,臣愿做州牧平乱。”灵帝闻之甚喜,当下嘉奖之,那王允自思刚才之言已得罪张让,若再留在朝中,恐遭暗算,便也请缨,愿为州牧,灵帝准奏,当下命尚书处拟定任命诏书,择日发布。
众位看官你道那尚书令是谁?便是那十常侍之首的张让,退朝后灵帝独召其进殿,将重置州牧的指令传达,张让领完旨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放权出去,各自为政,国库便可消减开支,以后自己又有多余钱财支配,忧的是惧地方权柄渐重,外加刘焉、王允,一为豫州牧,一为益州牧,一武一文,任命的恰到好处,万一那位打着清君侧的名号,自己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张让思虑至此,不由得叹息起来。
时赵忠在旁,见张让忧思,询问其因,张让便实言相告,赵忠笑道:“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既怕王、刘二人,何不矫诏让其互换官职?刘焉武官,益州天府之国,蜀道艰险,易守难攻,可守成而不可作为也,汝可暗派刺客跟随,待到罕迹之处杀之,王允文官,可使之为豫州牧,若是被黄巾所破,则可加罪于彼,若是能平乱成功,则以拥兵图谋不轨为名,罢官乡里,此两全其美之策也。”
张让听罢大喜道:“君之所言,正合我意。”于是张让先拟了一道诏书让灵帝过目,此诏命刘焉为豫州牧,王允为益州牧,待灵帝玺印敲过,回去又拟了一份,大致与原诏相同,只将刘、王二人对调,至夜半使人秘将玉玺偷出,私自盖完后便派人将诏书宣至二人住处。
刘焉、王允二人听见诏书内容,心中虽有些疑心,然看见敲着灵帝玺印,遂以为真,便收拾行装,安心出发。
先说刘焉进蜀,因怕十常侍搬弄口实,遂轻装简从,单人单骑,一路通行无阻,至葭萌关五十里处时,遭张让所派刺客数人,自称黄巾乱贼,来取焉之首级,那刘焉颇有些武艺,正待拔剑酣斗之时,忽然间飞沙走石,辨不明东西南北,原来那伙贼寇知刘焉颇有能耐,故而先做起妖法,扰其心智,好从中下手。
众贼见妖法见效,便乘势一拥而上,将刘焉团团围住,那刘焉正遇千钧一发之时,忽然又天地开朗,晴日当空,众贼心下疑惑,正不知谁破了自家法术,刘焉乘势横劍上前一击,砍倒一人,众贼见状欲上前奋力一搏,只听得背后有人大喊一声道:“疾!”那伙贼子各个便如死了一般,纷纷倒下。
刘焉回劍入鞘,便见不远处立着一伙客人,为首一人,气宇轩昂,颇有仙风道骨,焉料想定是那道士解救自己,便先上前作揖谢恩,那人也急忙回拜,互通姓名,便答曰:“某姓张,名鲁,字公祺,汉之留侯十世孙也。”
刘焉大惊,连忙施礼,问道:“足下莫非天师道教祖张凌之孙也?”张鲁答曰:“然也,祖父自幼教某家,道家主题虽不问世事,然为教者当为天下舍生取义,为天下驱,今奉家父之命,入蜀传道,闻大人已为益州牧,入蜀筹备粮草已资前军,不想在此遇见。”
刘焉大喜,当下便与张鲁合在一处,投成都路上来,于路两人论起刚刚那伙贼寇,张鲁道:“此伙贼人,想是十常侍派来的刺客,预谋行刺大人,况此类法术,乃旁门邪道,唯有入黄巾者方可习之。”
那刘焉顿时醒悟道:“十常侍暗派刺客乃是常事,不想竟与黄巾贼沆瀣一气!那我军布置情况,岂不是知晓的一清二楚?”随即大叫一声:“不好!”顾不得张鲁,便快马加鞭赶起路来。
再说那王允上任豫州刺史,豫州地方本就贼患猖獗,加之官军连连战败,州库县府,劫掠一空,沿途百姓嚎哭哀鸣之声,不觉于耳,统的是凄惨之状,不忍言表,那王允上任第一件事,便是安抚百姓,将难民集中一处,又把那所剩不多的军粮分出一半,发给百姓,各级军士如有私自克扣者军法从事,一面又向朝廷汇报情况,望乞发兵援粮,百姓得食,稍稍安定,豫州地面,渐起生机。
那十常侍接到王允奏报,偏偏不发一兵一卒。不送一粮一饷,整日陪伴灵帝玩耍,那灵帝偶尔问起时,便道王大人与贼激战正酣,生死未卜,胜负未分,待有捷报,自会报知圣上,灵帝遂不疑虑。
那王允在豫州等了月余,不见朝廷发来一兵一粮,自思定是那十常侍暗中作梗,在此期间自己倒是跑了好几家商贾豪门,用了卖官鬻爵的法子,周转兵马钱粮,方才弄得军稳民定,没想百姓互相奔走相告,言王大人治理州郡有方,那深受天灾、兵灾的冀、幽难民闻之,蜂拥而至,一时沿途道路满塞,官兵不能止也。
一日王允正在府内思量难民一事,忽有信使从蜀中而来,说是送来刘太守手书,王允急忙唤入,那人递上书信后,自回去复命。
允暗思虽与刘焉同抗十常侍,然向来与彼政见不同,何故突然会寄信到此,当下便打开观之,一块小虎符,一封书信。
其书曰:
汉中郎益州牧刘,再拜于豫州牧王子师足下
今内朝纲混乱,十常侍蒙蔽圣聪,欺压百姓,搜刮民脂,十恶不赦,又闻黄巾乱贼,横行中原,汉军节节败退,各级官吏,望风而逃,此内外交困之时也,余当日议重置州牧一事,乃欲借一安身立命之所,以图后举,待黄巾灭后欲行清君侧之事也,届时内外呼应,十常侍迟早归西矣,不料公竟不解其意,奈何!奈何!
然公继豫州牧后,开仓赈济,安抚民心,身先躬行,以整军纪,余远在西蜀,仍闻逃难百姓赞王太守之名,由此观之,公实乃明大义,知大体者也,余自愧不如也。
今书此信,为一机密事也,余至蜀中上任时,遇黄巾贼,彼使妖法困之,幸遇贵人相助,得脱此难,今余细思,暗杀官员乃十常侍惯用之计,余之所遇恐亦如是也,至府中后即命人搜其尸,得一小虎符,察之乃十常侍惯用之物也,今十常侍,****也,黄巾之流,反贼也,若使二贼合流,互相勾结,则吾等外不能御反贼以安天下,内不能清朝纲以忠事君,如此汉室覆灭之期不远矣。
今余远在成都,蜀道艰难,不能通跋山涉水以通消息,故遣人至豫州,望足下存留为证,日后若遇大变,可将此书与虎符面呈圣上,至于豫州难民,可南下荆州,再向西溯江而上,入蜀为居,益州天府,粮食足备,自由安排难民之处,望明察之。
王允看罢,不禁喟叹:“嗟乎!难得刘君郎(刘焉字)如此深明大义!若不从之,岂不坏了其一番好意?”当即回信,派人快马至成都府,自此两人前隙渐消,虽异地为官,仍长通书信,保持联络。
刘焉至益州后,整饬吏治,各级上下,焕然一新,又兴修水利,开辟荒地,真个是国泰民安,道不拾遗,比起那中原的受难百姓,有天壤之别。待至稍稍安定,又想起汉中乃益州屏障,不可不派人坚守,但又苦于无人可用。踌躇之际,又蓦地念起一人,便急忙派人想请。
若要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