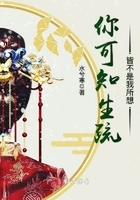清晨,王猛已候在承明殿多时,连夜从始平县赶来,面色依稀还蒙着烟尘。
“爱卿平身,坐。”苻坚搀起王猛,扬手指了指一侧的棋盘。君臣相视而笑,双双落了座。
“始平县如今一片祥和之气,更现路不拾遗之风,爱卿居功至伟,着实该赏。”苻坚嚅唇一笑,落了子。
捻着白子,王猛拢在掌心旋了旋,抬眸望一眼对坐,道:“陛下谬赞,微臣只是尽臣子的本分罢了。微臣此番未得召便入京,想来陛下亦知来意。”
“嗯……”点头,掠过一抹忧思,苻坚淡淡道,“阳平公请调雍州牧一事,孤已准奏。爱卿的忧虑,孤也知晓。可……身为兄长,当惜手足之情,身为国君,当显容人之度。”
王猛索性把白子撂回棋笥,抚膝道:“陛下之仁,乃苍生之福。然,阳平公请调戍边冀州不成,才退而求其次,请了雍州。雍州富庶,更是陛下起兵之地,举足轻重啊。微臣以为,不妥……至少,当下不妥。若不能收阳平公之心,留他在长安方是万安之策。”
苦涩一笑,苻坚凝着王猛,问道:“爱卿可有兄弟?家中排行第几?”
“微臣是家中幼子,有两个哥哥。”王猛垂眸,轻叹一气,犹豫一瞬,些许为难,“陛下既与微臣闲话家常,微臣便斗胆僭越。为成全手足之情,陛下已割舍所爱,如此,已是仁至义尽。”
面色唰地一变,苻坚却并未动怒,笑愈苦:“孤亏欠的……何止融弟?罢了,爱卿此番与孤推心置腹,孤甚感欣慰。可,调任一事,孤心意已决。爱卿亦不必过度心忧……”
指指棋盘,苻坚解嘲一笑:“孤既敢走这一步,便留了后招。孤唯想尽力化解融弟的心结,如此,即便……孤也没什么后悔的了。”
王猛不好再多言,只好无奈地点头。君臣二人对弈一局,王猛便匆匆请退,赶回始平县。
“你说,孤……是不是……太狠,太过分了?”拨弄着棋子,苻坚捂着额,轻叹一气,分明在问近侍却似自言自语。
一怔,方和撅着嘴,摇摇头,片刻,又为难地点点头,终是支吾道:“陛下的……心思,奴才都知。可……可,气得郡主……吐血,或许,这话……确也……重了些。”
眸子微沉,苻坚苦苦地嚅了嚅唇,拿不定主意的忐忑:“过门便是客,孤去探病,尽尽地主之谊,可妥?”
方和更是愣住,顷刻,嘿嘿道:“妥,如何不妥?奴才这就去置备。”
“唉,慢着。”苻坚招了招手,道“吩咐御膳房备栗子糕,她……喜欢。”
“诺……”
凉亭沾染秋露,不免有些清冷。颜儿倚着廊椅,伸手去接片片凋落的红叶,秋至,冬不远……落寞地耷下头,搁在凭栏上,痴痴凝着落红,颜儿只觉四下悲凉,徒增伤感,四季更替,终有春暖花开一日,然,心头的严冬恐是一世都走不出了。
瞥见黯然神伤的莹白身影,苻融不由住步亭外,眸光顷刻柔了柔。唯是一瞬,摇头不以为然,苻融快步进了凉亭,依旧孤傲模样:“怎样?郡主天资聪颖,肺鱼中毒一事谁是主使,不肖我多言,你也知晓。你……需要这门亲事。”
玉靥未见波澜,颜儿摊开纤细五指,瞟了眼掌心落叶,轻轻吹了一气,眼见叶坠无踪,淡淡道:“你……能应我一事吗?”
微怔,苻融漫然地落座石凳上,倒也不瞧颜儿,漫不经心道:“说说看。”
星眸一颤,颜儿解嘲般扯了扯唇角,毫无底气地轻声道:“今生……只……娶我一人,不纳妾,可好?”说罢,回眸直直地望向苻融,眼神却无期盼,唯剩探究。
愣住,继而蹙眉,苻融玩味一笑,唯是凝着娥眉黛玉一瞬,又没来由得敛了笑:“郡主倒真有意思。古往今来,但凡有本事的男子,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况且……”
咽回了话,苻融倾着身子,凑近些许,半认真半打趣:“或许我会是个情种,可……那也得看你有无本事抓牢我的心。你可知,问这种话的女人……愚蠢得很。”
落寞地垂眸,解嘲一笑,笑得叫人心碎,颜儿振了振,道:“我知,这段姻缘,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如此,倒也好办了。”
抬眸,颜儿坦然地望着苻融,胸有成竹模样:“既如此,若有一日,我对你没用处了,或是……你遇到了心仪的女子,我愿意让出嫡妻之位……”
愕然,苻融直起了身子,满目疑窦,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竟一时不知所以,可心头却隐隐泛起一丝酸意。
“只望你答应我……”顿了顿,星眸蒙上一抹氤氲,颜儿抬眸望一眼阴蒙蒙的天,向往道,“帮我……重获自由。”
“自由?”苻融低声嘀咕。
“嗯……”噙着泪,颜儿点点头,重复道,“自由!我不愿再受制于人,像……而今这样。至于怎么帮……需要时我自会开口。”说罢,问询地捎了一眼。
阴着眸子瞧了瞧,苻融翘起二郎腿,背倚着石桌,直勾勾地凝着颜儿,只想把眼前的女子瞧个明白,一瞬,心底自嘲,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管她那么多作甚?于是合手一紧,道:“成交了。”
半点不意外,颜儿伸出手,摊开手掌,强装莞尔:“聘礼……给我吧。”
苻融又愣了住,活到十七岁还不曾见哪个女子这般脸皮厚的,伸手索要聘礼竟也脸不红心不跳,却是莫名失落,自己的姻缘如何就沦为了一场交易?于是悻悻地从袖口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锦盒,不情不愿地送了出去。
伸手去接,刚要够到,哪知却被那人收了回去,颜儿不耐地往凭栏上倚了倚,别眸他处,冷冷道:“本就是为势所迫,才勉为其难收下。你若改了主意,我求之不得,不送了。”
“呵呵……”苻融爽声一笑,嘭地开了锦盒,低瞥一眼翠玉簪子,戏谑道,“到手的猎物我怎会轻弃?”
禁不住冒火,每每见他,每每来气,颜儿便要起身离开,肩却被死死摁住了。
一手摁住颜儿,一手捻起玉簪,苻融起了身,贴近一步,瞥一眼云鬟雾鬓,歪头嘟嘴,玩世不恭模样,随手便把玉簪插在了黛髻上,喃喃道:“送玉簪子,不过贪它温润,下回你再用簪子来戳我的喉,怕是不能得逞了,它可比不得金簪,钝得很。”
发线轻轻一扯,头皮竟是一麻,心瞬即飘上了雍山之巅,颜儿垂眸,腕子上空空如也,玉簪戳的哪里是他的喉,分明是自己的心,落幕了……从今往后,他是妹夫,是大伯,还是……仇敌,这颗曾为他跳、为他喜、为他忧的心,贴上了诅咒,再不会爱了……手木木地紧着空荡荡的腕子,晶莹润了乌睫,甸甸如叶尖的秋雨,滴落,断了线般滴落……
心一紧,手僵在半空,苻融凝着泪眸,心没来由地泛起一丝酸楚、一丝淡淡的疼,手指不听使唤地凑近凝脂,轻轻拭了拭。指尖的清润轰地唤醒清明,眉梢紧蹙,苻融缩手,冷厉道:“既是我的妻,往后便容不得你为他落泪。”
惊醒,颜儿抬眸,苦苦一笑,倒半分不示弱:“你既对我无情,我笑也好,哭也好,与你何干?若要我不落泪,那也得看你有无本事。”
毫无征兆地捏着颜儿的下巴扬起,苻融俯身凑近,唇不由分说地贴上了泪眸,轻轻一吻。
“你……”始料不及,颜儿猛推一把,厌嫌地揉了揉眼,刚要开口……
苻融已摊开双臂,耸着肩,退出凉亭,大声笑道:“我有无本事,重阳夜,你自会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