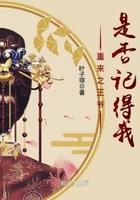公元三六九年,燕都邺城人心惶惶。秦国围燕势如破竹,世人皆道,燕国国运已尽,不出一年邺城怕是要易姓更主了。
茶寮里,一片愁云惨雾,连耍贫嘴的泼皮都噤了声。
方才入秋,天气并不寒冷。可店铺角座茶歇的女子却不合时节地披着长长的黑斗篷,时不时还扯着篷帽遮脸。
多事的店小二趁着添茶的当头,勾头偷瞟女子半遮的脸,顿时吓得猛退一步,手中一壶滚烫的开水差点惊落。
女子嗖地弹起身,双手扯着篷帽把脸捂了个严实,只露得一双澄亮的眸子在外。那眸光如刃,尽是怨怼,她狠剜一眼店小二,茶钱都没付就冲出了店。女子歪歪斜斜,横冲直撞地七拐八弯。直到冲到木桥底下,她蹲跪在石板上,双手捧水使劲洗面。歇斯底里一番,她缓缓抽开手来。秋水波光粼粼,午后阳光把水面打磨成一面偌大的明镜……
“啊……”痛苦的呻吟哑在嗓子眼,低得几近无声,女子捧着头,惊恐地睁大眸子,死死盯住水面。左右脸颊的刺青倒映水面,一横一撇都清晰无比,倒影竟是反扣的“静心寡念”四字。
“马韵如……你个贱人!”嘶哑近乎无声的咒骂隐没在幽漆的秋水里。女子扑着身子,双手搅乱水面,眼角凄凄全是泪。假死逃出凉宫后,她不知抓着花簪,戳花了多少面铜镜。
“贵妃娘娘训诫,望姑娘牢记心底,好自为之。”当日老嬷嬷把她撂上东行的马车,甩下的就是这句。
斗篷都被水浸透了,冉儿才爬起身。她平静地盯着水面,远远看着,刺青变得模糊。她抚着曾经的月貌花容,唇角勾起一丝残忍冷笑。她仰望苍天,她不懂,上苍为何如此薄待于她。同为绝色,张杞桑霸了司马曦的心,又受尽苻坚的宠,如今已贵为一国之后,儿女双全。马韵如侍张天锡时早非完璧之身,却照样得尽宠爱,那个男人为了她竟甘负乱伦谋逆骂名。哪怕是早死的一一,竟也得慕容垂惦念一世,直恨得九儿咬牙切齿却有苦难言。
而她呢?她永远记得那个凄冷的夜,那个男人掀开锦衾,瞥见床单后的表情,震惊,暴怒,怨恨却独独没有怜惜。可她分明记得,那个男人也有似水柔情。他曾默默地站在书房窗前,盯着一枚断玉簪发呆,那眼神……她苦笑,身为嫡妻的她从不曾拥有。她曾嫉妒过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子。
那是她今生唯一的一次姻缘。她暗自追悔过许多回,若是她当初不那么矫情,花重金请青楼老鸨想想法子,或许就能顺利糊弄过那夜。可惜啊,她那时还心怀少女情丝,总想着凭借美貌和柔情打动那个男人。
“苻融……”她揪着斗篷,滴滴答答拧出水来。她接不了下句,那个曾是她丈夫的男人,如今在她心里只剩的一个名字。她曾恨他恨到牙痒,可是,也许是她今生恨的人太多太多,以至于到了此刻,她对他竟没了恨,独剩荒芜的空。
倘若非得恨谁,她必是要恨那个早已掩埋黄土多年的卑鄙小人。“张祚……”她揪起斗篷襟角一丝一寸地拧水。她使尽了浑身气力,好似掐着的不是衣袍,而是那个男人的脖子。她最恨他,是他生生把她从千金公主重新打入十八层炼狱。他说,张重华疑她有假,他塞给她药瓶,他教她下毒,他甚至霸了她的身子……那年,她不过十二岁啊。她还记得那药粉惨白惨白,她的裙襟血红血红,她这辈子永远忘不了那耻辱的一幕。她早该知,从她弑父失身那天起,就永生不得翻身……
是以,她才会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那个同样永生不得翻身的男人吧。他们唯一的默契,便是……弑父。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悠悠地爬着石阶。她苦笑,哪怕顶着刺青,哪怕她恨不得钻进地缝,她竟又冒着生命危险回了断风崖。可惜,三月之约早过了,好几个三月都过了,那个男人早不在了。
这几年,她正如面上的刺青所训,当真是静心了。不,她有怨,有恨,却无可奈何。女人狠起来,真能折磨得人生不如死。马韵如那个贱人,算准了她冉冉最大的本钱就是这张脸,毁了脸,她就永无翻身之日。当真如此,她拿着那个贱人假好心塞下的银两,穿梭于三国,这双眼也曾勾过几颗男人心,可面巾一落,那些男人便落荒而逃,她从他们眼里,只看到厌恶。
“马韵如……”她想咒骂,每每心存愤恨之时,她都忍不住开口,可每每只会令她跌入更深的痛苦。她哑了。那个贱人在假死药里掺了哑药,药得她的声音低若游丝。
她扯着斗篷掩面。看来,明日她得再备一张面纱了。此来邺城,她知危机四伏。可她顾不得。这些年支撑她活着的唯一念想,只剩得那个男人的消息了。她惊奇,当真是惊奇,贪生怕死的自己,竟然也会为了一个男人一而再地铤而走险。而那个男人莫说爱她,甚至连个好脸色都不曾给过她。
对着她,他只有冷漠,甚至鄙夷。她不懂,当真不懂,为何他对着那个女人可以痴情成那副样子。她和他何尝不是识于微时,两小无猜?她甚至比那个女人识他更早,离他更近!他们同拜白马寺,同住齐云山。他怎么就记不得她曾是他的妞儿?
她更不懂,这么个男人有什么值得她爱。可她还是傻兮兮地爱了,何时开始的,她都道不清。她想,她当真是因为毁容到生无可恋的地步,不得不找点儿念想。她能想到的就只剩那个男人。听说道安大师来了邺城布道,她便千里奔来寻他。可刚抵邺城,竟又得了道安折往洛阳的消息,她便又想着随去洛阳。
可经了今日,她忽然不急于去洛阳了。她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从凉宫知晓的那个秘密,或许能为她换得某种好处,比如……呵,她苦笑,她竟沦落到损人不利己的可笑地步了。她搜肠刮肚竟想不到自己还能捞到何种好处,可她就是想去,哪怕是报复下那个女人,叫她平白伤心一遭也好。
她勾起一抹冷漠笑意,挺直腰杆幽幽朝龙城方向而去……
秦国宣室殿,苻坚掂着燕国来的讣告和家书,敛眸沉思。“云夫人……缘何暴毙?”他捻着麒麟菩提,菩提珠许是被婆娑得久了,澄亮澄亮地泛着柔光。
方和回话:“禀陛下,听密使说一直在龙城守墓的云夫人,日前忽然面见了一位女访客。那访客居士打扮,面刺‘静心寡念’四字,自称是前朝赵国石虎的姬妾李菟。”
“李菟?”苻坚蹙眉,昔日赵国第一女官该是颜儿心念的师父莫愁,如何……指节扣着御案,他折起家书纳入屉子,面色冷峻:“云夫人暴毙一事,不得泄露半句,尤其是皇后那里。”
“诺。”
苻坚绕着菩提缠在腕子上,眸光冷厉:“密令王猛,令他追捕李菟。李菟有悖人伦,为图‘百金’不义赏钱,出卖赵王墓,令一代英主暴尸荒野。前赵王于我苻家有恩,李菟一经抓获,就地正法,以敬赵王先灵。”说罢,他起身:“吉时将至,备撵椒房殿。”
今日是宝公主的满月礼。宝公主是天王陛下唯一的嫡女,自是尊贵异常,礼部不敢怠慢,清早便已前赴太庙告上告祖。椒房殿的悬帨礼,亦是天王亲力亲为。
苻坚郑重地捧着佩巾,悬于殿门右侧,紧接着又行射“天地四方”之礼。杞桑抱着襁褓里的奶娃娃一路随着,略显丰腴的腮颊清浅含笑,一双美眸泛着涟漪柔光。夫妻不时对望一眼,虽是无声却胜却蜜语万千。
“东边战事吃紧,满月礼而已,陛下不用特地抽空主礼的。”从殿门踱回内室,杞桑揪住须臾间隙,轻柔低语。
苻坚体贴地接过女儿抱在怀里:“才出月子,即便是欢喜孩子,也别总抱着,劳伤筋骨。”
杞桑不自觉地撑着腰,不以为然地娇笑:“臣妾哪有那般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