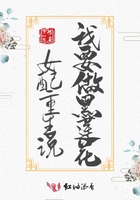颠了一路,忽的,颜儿只觉头一仰,透过蒙头衣袍刺面的冷气瞬即褪了。入了步辇?果然,轱辘,轱辘,步辇动了。
眼前的蒙纱依旧遮着,她的视线一片模糊。忽的,她只觉脸颊拂过一抹冷意,该是他的掌。他的手从未这般冷过。她忽然想起,方才他只穿了一件单衣。忽的,她只觉额际、眉心熨过一团烈焰。扑扑的,她闻到了他的气息,听见了他的喘息。
“颜儿。”他低低地只吐了两字。可她却似听到了一切,有怒、有痛、有爱、有怜……只是她已毫无气力理会。她幽幽地阖了眼,由着车轱辘轱辘,又由着他颠着自己在肩头。她不知自己到了哪儿。直到头上的蒙纱被扯了去,烘烘暖气裹了面,她才发觉到了承明殿。那曾经布满星辰的帐顶,此刻,就倒逼着她的眼。
苻坚依旧紧绷着脸,木然地扯着绳索。
“陛下,”方和如履薄冰,好不小心地递上了剪子。
铰开绳索,苻坚解开了蚕茧,却是冲着外头:“炭火煨热一些。传御医院,外殿候着。”
哗——哗——他放下帐帱,顺势落了座。他倾着身子,俯了过去,头先冷冰冰的眸子似一瞬被暖气炽化了,蒙了一层水雾。他没有言语,唯是重重地吻上了她的额。良久,他都没移开唇。
这样的亲昵,自那夜再不曾有。颜儿原就精神恍惚,此刻,愈发恍惚。
额抵着额,他掌着她的肩,眼几近贴上了她的眼:“听着,从今日起,除了孤,谁都入不得这间屋子。吃穿住行,除非是孤给你的,旁的人,谁都别信。听清了吗?”
错愕,这般近,近得颜儿看不清他的脸。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怕自己会死吗?还是怕谁要来杀她?
“听清了吗?”他轻轻地晃了晃,额蹭着,增了几分力道。
颜儿不置可否地垂了睑,闭了目,下意识地紧了紧怀里的紫檀木。
剑眉微蹙,苻坚掀开锦衾,一把夺过紫檀木,嗖地起了身。
“还……我!”颜儿惊得几近弹起,攀手便要夺,却嗖地软瘫了回去。她太虚了,虚得只剩得最后一口气了。
“孤先替你存着。”他回眸定定地看着她,语气柔和却不容拒绝,“孤不知这里头是什么,也没兴趣知。眼下,你万事都听孤的,懂吗?”
不听可有旁的法子?颜儿睁也睁不开眼。借着最后一丝清明,她强撑着睑,瞧见他捧着紫檀木,随手塞进了角落的箱柜里……
承明殿正殿,大半夜的,却黑压压坐满了人。诚惶诚恐的,漠不关心的,惊疑错愕的,还有幸灾乐祸的。
苟太后眯着眼闭目凝神。
“母后,不如您先回宫歇着吧。”苟曼青关切地覆了覆婆婆的手。
苟太后冷笑,摇了摇头。
“这是怎么了?她滑了胎,难不成要累得整个宫都遭殃?说不准就是她的苦肉计。”这般不经大脑的话,除了颜双又还会有谁。
“咳咳……”吕玉彤好一阵佯咳,眸子睃向殿门。
颜双循着望去,只见丈夫黑口黑面地杵在门口,那眼神噬人般狠。她赶忙低了头,怯弱地挪了挪。
苻坚冷冷地盯着她,一步一步踱向了主座,幽幽地,又移眸扫向每一个人。他甚至没向母亲行礼问安,便径直落了座。
“淑妃骄纵成性,目无尊长,降为小仪。”
从淑妃至小仪?那可是从正一品啪地打落至从五品,无异于被废。颜双只觉晴天霹雳,僵作了石雕。四座皆惊。苟太后蓦地睁了眸。
“陛下,双儿妹妹素来有口无心。她没有恶意,求您收回成命。”苟曼青端着副老好人的模样,率先开了口。
“陛下……”“陛下……”几妃异口同声地开了口求情,勿论真心还是假意,面上倒做足了。
嘭——冷拳瞧得案几一记闷响,苻坚漠然地凝着前方的殿门,冷冷道:“求情者同罪。”
嗖地,殿宇寂静了。
“陛下!”颜双噗通跪了下来,泪落连珠,“臣妾犯了何等大过?您要这般罚臣妾。表哥,我是您的亲表妹,您怎么可以为了那个下贱胚子这般罚我……”
苻坚不曾看她,唯是稍稍抬睑,睨了眼近侍。方和急忙招来两个宫女,把撒泼的小仪架了下去。
这晌,众妃的心底都打起了鼓。这样的丈夫,无疑陌生得可怕。那淡漠的面容,瞧不出雷霆怒意,却凛凛透骨寒凉。她们只觉当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故而,且怯弱地屏气噤声。
而苟太后一直冷冷的。她几度似想开口,可终究忍了住。
苻坚没再言语,唯是冷冷地望向嫡妻。那眼神叫人摸不清头脑的纷杂。他微微抬起手。
“带上来。”方和传了令。
苟曼青不慌不忙地直了直脊梁,那沉稳背后隐着成竹在胸,甚至是一丝幸灾乐祸。
噗通——椒房殿宫女翠儿颤抖着跪下来去,连连磕头:“陛下饶命,饶命。”
“招吧。”苻坚依旧看着嫡妻,那双眸清晰地簇着恼意,甚至恨意。
“不错。”苟曼青嗖地起了身,顺势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她颔首:“是臣妾做的,但臣妾如此,全然是为了陛下,为了未央宫。臣妾斗胆……”她抬眸,笃定:“求陛下见一个人。陛下见了,便能识得臣妾的一片苦心。”“把她带上来!”她喧宾夺主地扭头下令,那气势真真不同往昔。
苻坚漠然,唯是凝着她,眸底的恼恨隐隐又添了几分。
一个熟悉的声影被甩在了殿中央。众人皆是一惊,怎会是她?
小草恭恭敬敬地叩了叩。
“你说,把你说过的,都一五一十地对陛下再说一次!”苟曼青跪得直直地,扭头趾高气昂。
见来人是小草,苻坚有一霎微怔,顷刻,便朝近侍睃了一眼。
“请太后娘娘和各位娘娘移步偏殿。”
众人虽是好奇,却不敢多留,急急退了去。苟太后不过睨了一眼,也随着退了去。
“陛下,”小草又叩了叩,“当日,公主从陛下手中盗走了龙门璧的印模。她本是要交给燕皇的,后头之所以没给,不是她念及陛下,才打消了念头,而是……”她微微抬头,睨了眼苟曼青,道:“蜡模不小心给毁了。”
眉结微微搐了搐,苻坚倚向椅背,双眸隐隐掠过一缕失落,却蓦地低眸俯视:“龙门璧为聘,孤心甘情愿。这就是你理直气壮的借口?”
“当然不是!”苟曼青捉急,“臣妾之所以……那孩子压根就不是陛下的,那是个孽种!”
轰地,当头一棒,苻坚只觉头脑猛地一空,顷刻,胸腔的怒火薄喷而上。他倾着身子,却是冷厉地勾唇苦笑:“你就那么恨她?连带着孤都恨了吗?孤说过,今生再不会信你。”
“陛下!臣妾没撒谎!”苟曼青红着眸,跪着挪了挪,一把揪住小草摁了摁,“你说,把你说过的话,清清楚楚地向陛下再说一回!说!”
“娘娘,”小草木头人一般,懵懵地抬了头,看着她,“奴婢知道的,全说的。不知道的,奴婢怎能瞎说?你即便杀了奴婢,奴婢也不敢瞎说。”
“你——”苟曼青摁着她的颈,戳着手指直搐。她恍然:“哦,你算计我,你们主仆撺掇着算计我。”
“陛下,”她扑着跪伏下来,“真是她说的,她说那是贼和尚的孽种。所以,臣妾才……臣妾是为了皇家的血统和陛下的颜面,才铤而走险的。陛下都已恩准,把她的孩子养在椒房殿了。倘若那真是陛下的血脉,即便臣妾再丧心病狂,也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呀。臣妾冤枉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