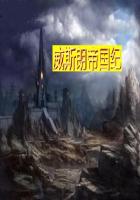“你们敢!”轻飘飘却傲气凌人,颜儿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半分,幽幽扭过头,依稀瞧见太监抱在胸前的木棍,足足拳头粗,回想头先那句“用心打”,心下半点不慌倒是假的。
廷杖有“用心打”与“着实打”之分,“着实打”不过皮肉之苦,最不济亦不过落下个伤残,而“用心打”则是九死一生。小太监那厢得了令,这厢却被刑凳上的主子威吓,愣在当下倒也失了主意。
“怎么?连主子都认不得了?难不成要皇后娘娘亲自动手?”
祁嬷嬷阴阳怪气地在殿门后撂下这么一句。啪——头一声震在耳畔,却未落在身上,颜儿扭头,只见小草紧咬牙关,脸涨得通红。刚想开口喝退宫人,啪——嗓子一哽,颜儿只觉骨头散了架,周身的毛孔嗖地竖了起来,一个激灵,竟觉空气里粉尘浮杂的细微之音都清晰可闻。
“公主!你们不要命了?公主也敢打,皇上饶不了你们,饶不了……”小草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挣扎地刑凳轻晃。
拧紧拳头,颜儿依稀感觉到指甲陷进了掌心里,却不见疼,只因腰骨以下似绞入水车卷起的漩涡,绞心的痛。周身冷栗,牙床直打颤,舌尖腥涩,颜儿知,强忍着不出声,这嘴唇怕是咬破了,眼角潮润不堪,伴着涩涩的刺痛,那不是泪,却是发线处渗落的细汗。
“二……三……轮刑!”
小太监尖细地唱着刑,忽的,水车似卡住了,漩涡骤止,可须臾,疼痛又铺天盖地地袭来。原来,小太监使了吃奶的劲执刑,每三杖便得轮换一人。
“四……”
尖细的娘腔越飘越远,知觉模糊,头脑却愈发清醒,爹当真把自己摆上祭台,由得可足浑家族鱼肉?被绑上刑凳那刻,木棍尚未落下之时,颜儿尚心存侥幸,可这刻……汗津津的,脸颊一片冰冷潮润,分不清是汗还是泪,颜儿死命地晃着脑袋,死命地挣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耗尽最后一点气力来吐出满心的苦水。“放……开……我”,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浑身一软,汗珠甸甸地压得眼睑幽幽阖了起来。
“五——”
“皇上驾到!”
早春料峭时分,村子东头二驴子家,那架水车嘎吱嘎吱唱个不停,引着碧粼粼的水入田。捋起裤管,褪下布鞋,踩着湿滑的踏板,和着二驴子的傻笑,自己踩得飞快,咯咯笑得正欢,噗——脚下一滑,身子一歪,一头栽了下去,落水前那刻,领口一紧。幸好外公一手把自己揪了起来,“淘气!卷入水车,不死也残,还敢吗?啊?”
吓得魂儿都快散了,脑勺儿暖暖的,外公轻轻地拍着,拍着,喃喃着“不怕,不怕,有外公在……”
脑勺儿暖暖的,轻轻的拍啊拍,怎听不见外公喃喃?颜儿迷糊地睁开眼,呃……脖子僵硬,尚不及扭扭脖子,嘶……凉意从头浇灌而下,周身紧裹的却是辣辣的痛。
“醒了?”慕容俊歪着头凑了过来,抚在云鬓上的手亦停了下来,“御医瞧过了,伤了筋骨,休养个十天半个月的,落不下病根,尽管宽心。”
下巴磕在枕上,颜儿迟迟地偏过脸去,直直地望向父亲,细细地在那双眸眼里搜寻关切,可掘地三尺也见不得一丝疼惜……
慕容俊不自在地缩回手:“可足浑毅死了,朕总该给皇后一个交代。再者——”眸眼冷了下来,慕容俊疏离地直起身:“朕虽宠着你,却容不得你自作主张,更容不得你……心向外人。你莫忘了,你姓慕容!”
“爹!”屈肘摁着床榻,颜儿急切地撑起半个身子,疼痛似火油顺着脊柱倒灌至脖颈,脑门一嗡,冷汗便浇了下来,“我是为了——”雷击般,颜儿摸索着袖口,又摸索着腰间,亵衣空空无一物,肩头一坠,闷声伏在榻上便不言语了。
面色阴冷,慕容俊冷冷地起了身:“朕心如明镜,收起你那点小心思。”
明黄晃眼,飞絮般飘走,颜儿只觉心头的温度亦随之飘逝,不解、委屈、不甘纷纷杂杂地攀缠得心绪不宁……
“他是怎么死的?”揪着锦缎,颜儿微仰着头,明知故问却偏不死心。
明黄顿了下来,却不曾扭头,那声音冷过三尺寒冰:“贪得无厌的下场。”
闷头歪在枕上,颜儿摊开手掌,掌心苍白,衬得纤细的血管透着幽冷的绿光。是血是孽,颜儿苦苦一笑,逃也般合拢了手,可足浑毅算不算是自己害死的?算吗?他知道得太多,又野心勃勃,不能为父亲所用,便只能是这般下场。父亲……心幽幽沉了下去,颜儿只觉身不由己地坠入了无底黑洞,骨肉亲情不该是最亲最近吗?却为何与父亲之间分明隔了道屏障?无法逾越的屏障,一切似回到了相认时分疏离陌生的起点,甚至较之那时,更叫人沮丧,不,是心凉。
“公主……”近侍捧着一团洁白的锦帕,怯生生地挪了过来,“奴婢给您换洗时,腰封里发现这个……”
锦帕摊在榻上,纤细的指尖捻起帕角,颜儿迟疑,松开手指,掌心覆上帕子,碎了,正如此刻自己的心……揭开帕子,乳白的蜂蜡碾碎得七零八落,半点瞧不出蛟龙的痕迹,天意!颜儿涩涩一笑,泪啪嗒浸落蜂蜡,滑腻腻的泪,凝固般挂在蜡上。为了骨肉亲情不惜负心负情,假意归还龙门璧,暗地里却浇了这个蜡模……天意!颜儿释然,苦笑着阖了眼。
休养大半个月,日日翘首以盼,颜儿却再未盼来父亲。宫人倒不敢怠慢,虽然仍是锦衣玉食,颜儿却渐渐觉得,芙蓉轩已沦作了一处冷宫。若非云姨寸步不离地守在榻前照料,这帮势利的奴才怕是早要甩脸色给自己瞧了。
六月天,暑气窒闷,伤口难于照料。颜儿庆幸,总算赶在立夏前伤愈了,只是这心伤却难平。
这日,总算得了诏,可宫门前却未见步辇,行踪亦分外诡秘,若非慕容俊的贴身太监莫公公亲自来传,颜儿怕是不会肯随行,回宫当日的下马威多少慑住了自己,今夕不同往日,在这皇宫里也该小心为上。
“小草,委屈你了。”颜儿搀着小草的手紧了紧,满脸愧色。
“不委屈,我自小练功,身子骨硬朗着呢。”小草拍拍胸脯,笑了笑。
莫公公偷瞥一眼,在一处宫门前,不动声色地挡住了小草,对着颜儿恭顺请道:“公主,皇上有令,这院落唯您和奴才入得。”
这处院落地处宫门最北角,偏僻得生人勿近。跨入院门那刻,颜儿便觉到鞋底踩着厚厚的灰尘,越朝里走,鼻息便越胶着,空气似经陈年,沉淀着数十载的腐朽气息,难以入鼻。
“啊嚏——”颜儿禁不住打了个喷嚏。
哐……当……
隐隐听见屋里传来铁链声响,颜儿狐疑地望向莫公公。莫公公自顾自地开着房门的锁链:“公主您请。”
腐朽、腥涩还夹着丝丝恶臭……颜儿捻着帕子捂了捂鼻,探头瞧了瞧,昏暗的屋子里空空无物。
“公主请!”
跨过门槛,余光盯住身后的莫公公,颜儿强装镇定地缓缓踱步,气味越来越刺鼻,哐当的铁链声越来越清晰……
内室愈发昏暗,颜儿敛眸,循着铁链声望去,屋内唯剩一榻,榻上直挺挺地躺了个人……若海?颜儿蹭蹭走近,一尺外,再迈不开步……
她平躺着,满身血污,腰间捆着铁链,腰身抽搐般扭动,晃得铁链作响,四肢却木头般一动不动。她嘴里虽塞着布团,颜儿却依稀听得见忿恨的叫骂,那双暗滞眸眼里燃烧的熊熊烈焰,烤得自己心焦。
莫公公漠无表情,厌嫌地抽开她口中的布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