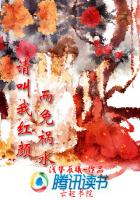慕容泽寻到君窈时,她正在鹅卵石幽.径上打转,捧着脸苦闷地嘟囔:“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左西右东上北下南!”话音未落,她便坚定地用食指指着地面,痛苦地哀嚎:“下南!下!南!”她灵光一闪,直起身子,手指顺势指向了前方,她洋洋得意地笑着,笑着看到慕容泽也正浅笑着盯着她看,她脸上的笑容顿时烟消云散,板着脸道:“你为何发笑?”
慕容泽笑面温润,款步走到她身旁,嘴边噙着一丝揶揄地笑,指了指前方:“喏,南在那。”
君窈窘迫的脸红,真是丢人丢到南召来了!她踮起脚,一个刀手比在慕容泽的脖颈处,威胁道:“不许笑!”
“好,我不笑。”慕容泽忍俊不禁。
君窈气的直跺脚:“你说了你不笑,还笑!”
慕容泽见她真的生气,敛着笑,启唇道:“迷路了?”他用的是疑问的语气,却是一脸笃定,执着她的手指着天上的太阳:“旭日东升,夕阳西下,正午为北。”
君窈铭记于心,兴奋道:“那南呢?”她猛地扭头,晶亮的眸子闪着笑意,慕容泽的心猛地一颤,舒展笑颜,虚拥着她,呵气若兰:“坐北朝南。”
君窈按他所言,举着手指逐个对应,心里叹为观止,却佯装不服气:“此等辨别方向之法,如此麻烦,不如直接抓个人来问省事。”她躲避他,别扭地在手指上缠着一缕青丝,心却比一团麻还要乱。
“时辰不早了,我们回家吧。”慕容泽携着君窈离开,从容却不失分寸地挽着她的手,夕阳西下,残阳如血,白衣衣袂飘飘,红衣缠绵相随。
回到东宫,慕容泽便吃了闭门羹,君窈进了殿内未等慕容泽进来,便把房门反锁,殿内隐约透进些许晚霞,晚霞中的一切器皿都泛着流光潋滟的色彩,小香炉里焚着不知名的香料,闻着清香怡人,君窈闻着闻着便昏昏欲睡,眼皮强撑着没合上,她哈欠连连地扑到榻上,懒散地蜷缩着身子,翻了个身便睡着了。
丫鬟煮了红枣薏米粥,慕容泽亲自送了来,轻叩着门扇唤道:“君窈,该用晚膳了。”连唤数声,殿内出奇的安静,慕容泽却仿佛洞悉一切,熟稔地从袖中取出一枚飞刀,顺着门缝一挑,那门栓便开了,他蹑手蹑脚地推开门,翻身又把门关上,款步朝内殿走去,轻缓地把汤碗放在案上,又朝榻边走去,榻边陷下去一片,他坐下抬手为君窈搭脉,眉头紧拧又缓缓地舒展,凝重的神色却并未有多少的缓解,他掀开被褥一角,把君窈的手又放了进去,重新为她掖了掖被子,俯身脱掉她的鞋子,从容地拎着走了出去。
慕容泽拎着君窈的鞋行至池边,认真地清洗着鞋面上的泥,他若僧人敲木鱼般拿着君窈的鞋一下下在石头上磕着,甩掉上面的泥,脑海里却浮现当时的情景。
昨夜方下过雨,御书房近日又在修葺,有一片未来得及铺地砖的地面显的有些泥泞,若是小心自然不会踩到,可若是逃跑时慌不择路,不注意脚下定然会遭殃,他低头盯着君窈鞋子上的污泥,眉眼平淡地甩着,污泥点点溅到水中,打出一圈圈的涟漪,而鞋子上却了无痕迹。
慕容泽身边的太监疾步走来,压低声音不知同他说些什么,寂奴远远地看着,只见向来气定神闲的慕容泽神色一紧,拂袖快步离去,同时那太监也紧随他离开。
打进东宫第一日,寂奴便墨守成规,只懂“听命行事”,从未好奇过主子的私事,她冷眼旁观着慕容泽不顾自己太子之尊为君窈洗鞋,看罢,举着酒坛子豪饮一口,转身晃荡着离去,这酒名唤“竹叶青”,是她师傅最爱喝的,如今师傅不知所踪,他珍藏的那些美酒佳酿便统统成了她的。
寂奴喝的醉眼迷离,忽瞧见宫中的莫太医急匆匆离开慕容泽的书房,脸色不是太好,酒使人乱性,也能使人失了分寸,她上前拦住他,一把弯刀抵在他脖子处,问道:“殿下召你所谓何事?”
莫太医是宫中老人,对后宫见不得人的事了如指掌,却向来守口如瓶,他冷汗涔涔,哆嗦道:“太子妃身体欠安,殿下召我前来送些补药。”
寂奴放了他,却敏锐地觉察到有些不对,莫太医走时的眼神不对,他眼神飘忽、疾步若飞,分明是害怕!更何况宫中事务繁忙,若只是送药,又怎劳烦年迈的太医院院首亲自跑一趟?寂奴留了心,便瞧见慕容泽从君窈房内出来,手里端着药碗泼向了花坛,神色冷淡从容,转身便离去了。
寂奴走过去扒开花丛,捡起一些残药渣嗅了嗅,并未有任何收获,她不懂药草,但直觉告诉她,这药有古怪。
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繁华的街市同寂奴格格不入,她心事重重、脚步虚浮地往前走着,想起郎中所言。
“这药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女子保胎的药罢了。”
是保胎,不是安胎。
寂奴追问:“同安胎药有何不同?”
郎中笑了笑:“安胎是为了孩子顺利出生,这保胎嘛,自然就是为了保住孩子。”
寂奴神色不明,紧紧的抓着腰间的弯刀,满脑子都是王君窈有孩子了,不可能,太子同她成亲不足一月,她怎会有身孕,而且是两个月的身孕。
“从这药量来看,此女子约怀孕两月,开药者倒是有心了,明知这胎保不住,却仍绞尽脑汁去延长胎儿的性命。”
寂奴回到东宫时,听闻慕容泽曾来找过她,她心中欢喜,转身便去寻他。
书房内,慕容泽目光清冷,抬眸道:“影卫本就是刀口舔血,若你后悔·······”
寂奴揉了手中的密函,抬眸与他目光相对,坚定道:“我从未后悔。”她躬身退下,潇洒地掀帘而出,在慕容泽看不到的地方,她却泪如雨下,ya抑着悲伤,克制住撕心裂肺的痛,憋着声音低唤:“师傅!”她紧紧地揪着衣襟,仿佛这样才能喘过起来,心啃噬般疼痛,她难以相信这个事实,她的师傅,南召第一影卫,以极其残忍的死法惨死在滚滚黄沙中,被寻到时,连尸身都是不完整的,可他的嘴角却上扬,仿佛在做一个美梦。
君窈醒来时,星光璀璨,月光映着翠竹的影子,在地上形成一幅绝妙的水墨画,她这一觉睡的格外舒服,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她疑惑,室内焚香的味道貌似淡了,不过很快她就释然了,肯定是快染尽了。
天刚亮,她便迫不及待地要出去,被守卫拦住,慕容泽不知何时行至此处,隔着一段距离,笑问“君窈这是要去何处,我可否有幸与你前往?”
君窈顿了顿,呲着牙笑着回过身:“今日阳光正好,宜出行,整日闷在东宫着实无聊,我想去外面走走,不知殿下可有空?”
慕容泽笑着走近:“愿为爱妃效劳。”
君窈暗笑,这可是你说的!待会有你好受的!她面上却笑意盎然,温顺地等小厮架着马车靠近,慕容泽翻身上车,探身朝她shen出手来,她欣然前往,手搭在慕容泽的掌心,任由他握着,顺势朝马车上跃去。
“王子皇孙多娇贵,除了读书便是骑马射箭,幼时所做之事全是围绕诸君之位,当了储君之后,所做之事又皆是为了帝王之位,待做了帝王,回顾人生才幡然醒悟,这人生着实无趣,还不如平民百姓活的自在潇洒。”君窈拔了个冰糖葫芦,大口地咀嚼着感慨道,那平民自然说的是她自己,她这一生,目前看来,过的还算潇洒惬意。
慕容泽静静地听着,没有表态,从腰间取出一锭碎银抛给买冰糖葫芦的小贩,那小贩感恩戴德,认出慕容泽便是当今太子,旋即把所有的冰糖葫芦呈上,慕容泽无奈,只能拔了几串作罢。
君窈幽幽道:“东宫俸禄当真少的可怜?”
慕容泽闻声抬头,顺着君窈的目光看去,她的目光落到他的钱袋上,里面装了不少的银子,慕容泽笑:“我这俸禄乃辛苦所得,他那冰糖葫芦又非价值连城,等价交换即可,我又岂能白白便宜了他,又岂能因太子之尊欺他小本买卖。”
君窈笑的揶揄:“看不出,你还是个好太子呢。”
慕容泽行礼:“多谢爱妃盛誉,为夫定当竭尽所能,去做一位好太子,不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为今之计我还是先做好一位好夫君,进而再做一位好太子吧。”他话毕,不知从何处得了一把伞,烈日当头,他为君窈撑着伞,笑的宛若谪仙,琴瑟和睦,羡煞旁人。
慕容泽行礼:“多谢爱妃盛誉,为夫定当竭尽所能,去做一位好太子,不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为今之计我还是先做好一位好夫君,进而再做一位好太子吧。”他话毕,不知从何处得了一把伞,烈日当头,他为君窈撑着伞,笑的宛若谪仙,琴瑟和睦,羡煞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