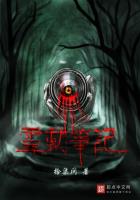他边说边带头走到前面去了,周宇方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俩立即陷入数不清的野猪之中。数不清的野猪们如捅烂了一只蚂蚁窝,他们似乎要在野猪之中穿行。野猪们虽然大都很是壮硕,看到的一般也有好几百斤,结实而彪悍。无论哪一头猪,只要对着他们俩的任何一个低头撞去,都会被撞倒在地,被这一群畜生踏为泥浆。但是,却没有一只猪敢于这样做。所到之处,所有的野猪全都抬起它们蠢笨而凶猛的脑袋,睁着两只莫名其妙的大眼睛,眼里飘动着疑惑和凶残。它们眼看着比它们高出一截的修长的两脚怪物,在它们的身边挤过去,毫无一点惧意,就像它们仅是一群家养的猪,它们当然是不可容忍的。但是,似乎猪怕人是一种天性。即使不怕人也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挤进它们之中,显然它们是没有想到的。因而更没有商量怎样来对付突然发生的情况。没有一只野猪企图要对这两个胆大包天的两脚怪物采取什么行动。它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在它们中间挤过去。其实,这两个人并不是以特别轻松的心情走过它们身边。他们知道野猪的野蛮和凶恶,不能掉以轻心。他们越镇定,野猪越是不敢轻易对他们怎样。他们时刻想着身上隐藏着的武器。隐藏的武器比公开的好。隐藏的不会激动对方的情绪,而公开的则处处招致危险。一般的动物不会使用武器,只会利用自己身体上的某些部位进行搏击,即使是最为柔弱的动物,在受到最凶猛的野兽的猎杀时,也能够顺利逃脱。人体的任何部位虽然不会对动物构成强烈的威胁,但人所掌握的武器却能致任何动物于死地,要想逃脱也不容易。
他们俩仿佛也变成了野猪的同类,因为他们周围全是野猪,就像捅翻了的一只蚂蚁窝,四处爬满了蚂蚁。他们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野猪?平时在人的世界里怎么就见不到这样的阵势?如果这里的蚂蚁都去了人类集中的地方,一定会大大多于人的数量,人要想使用自己的武器来对付也不可能了。
一路之上,除了满眼的野猪外,也看到了许多用粗大的树木搭起来的窝棚。这些窝棚四周直径十余米之内没有一根树木,全被齐根处截断。这些被截断的树木朝中间地带倒过去,互相撑持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空间,就是人们在野外搭建的所谓简易窝棚。人搭建的窝棚却比不过野猪们在这里搭建的。这里的每一个窝棚的上部由许多枝叶遮盖得严严实实,阳光不能进,雨水不能渗,世界上人搭建的从来没有这样密实厚重。野猪的工艺似乎比人的还要高明。他们俩仔细察看了树木截断的地方,既非人的斧锯所断,也非火药爆炸所为,而是经过动物的牙齿啮咬后的结果。在这样的野猪集中的地方,也没有看见别的任何动物,毫无疑问就是野猪的杰作。他们俩面对这样的事实,实在叹为观止。这不仅需要体力,更是需要智慧。这就是野猪的住所,完全打破了人之前以为野猪住在山洞里,顶多在土坎下打一个洞的粗浅的认识。原来它们也是可以利用自己的劳动进行创造的。白天它们全都在野外觅食,夜晚就走进这样的能够遮风挡雨的棚子里,对野猪这样的动物而言,真是够幸福的了。他们还看到一些野猪在窝棚里卧着,见他俩走过来,并不理睬,就像人坐在自己的家里,门前走过的行人与自已并不相干。它们也许是老弱病残之辈,也许是待产的母猪,不能去光天化日之下享受天然之乐,只能在棚里忍受孤寂。他们俩不想去干扰。
他们对它们的生活作了浮光掠影的了解。不过,那些操练和喊话,以及唱歌的野猪令他们觉得异类。冯奇飞对周宇方说,这样的野猪已经不是野猪了,像人又不是人,像猪又不是猪,总有一天要闹事。这就是人妖猪。正说着,上来几只彪悍的年轻野猪,竟然像人一样的站起来,用前肢指着冯奇飞,哼哼地叫着。冯奇飞听出来,它们说这个人就是它们的仇人,也是个很厉害的人,杀了它们许多兄弟,现在又潜伏到它们的的大本营里来,是来侦察情报,做间谍的,一定不要放过他,一定要冲上去杀死他。有一只野猪反身朝后跑去,也许是要去召集更厉害的野猪来对付这个它们认为的劲敌吧。
冯奇飞一听笑了,他俩本想离开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何必自寻烦恼!没想到这里还有与他作对的野猪。这些作对的野猪怎么会认识他的,他是没办法想明白了。他看这些野猪只有大小和颜色的区别,从面貌上实在是分不清谁是谁,就像中国人看外国人,似乎全都是一个脸模子。大约外国人看中国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野猪为什么就能在他们俩之中辨认出他来呢?既然被它们认出来,要想顺利地走出此地也就不那么容易了。难道还要与这些漫山遍野的野猪作一场决斗吗?这么多的野猪涌上来,其后果是可想而知。但他们并不害怕,只要这些野猪真的敢于与人作对,人也是有办法对付它们的。这几只野猪尽管叫得厉害,却没有一只冲上来。大约它们知道冯奇飞的厉害,只是吆喝着别的野猪向前冲,而自己却不敢上。冯奇飞讥讽地对这些野猪们招招手,意思是你们上来呀,上来试试,看看是谁杀死谁。
这时,离去的那一只野猪带来了一只黑色的更壮大的猪。如果说他对一般的野猪分辨不出谁是谁,那么这只黑色的更壮大的猪让他似曾相识。他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这是野猪里的那个所谓司令。猪司令站住了,而且如人一样的站立着,对冯奇飞似乎声色俱厉地喊叫,意思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闯到我们的猪世界来,难道不怕死吗?赶快滾出去,不然要将你踏成泥浆。
冯奇飞说,你既然是个猪司令,你就要对你的种族负责任,不要让你的种族作无谓的改变,不然便有灭绝种族的危险。他说他当然不屑到它们这个猪世界来,它们的猪世界也许并不是特别的糟糕,因为他们看了这个世界,猪们似乎都在自得其乐,为什么不好好地在你们自己的世界呆着,享受上帝赐予的快乐,而偏偏要闯到人类的世界去,祸害人类呢?还要散布颠倒黑白的无耻言论,用报复去恐吓,用迷信去麻痹,实在是罪大恶极。如果不赶快反省,必定会得到人类的清算。
猪司令听了呵呵大笑,说你真是井底之蛙,没有看到地球上的大势。地球上的大势明眼人有目共睹。当今的世界是强者的天下,什么道德礼仪之类的说教都进了厕所,成了解手纸。它让冯奇飞将眼睛睁开一点看看,它们的野猪的势力将要覆盖天下,谁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它让他等着,就是在不久的时间里,它们就要灭掉人类的世界,普天之下都是它们野猪的势力了。
冯奇飞说,好吧,那就等着,未来的世界看是谁的天下。他推了周宇方一把,朝回去的路上走。冯奇飞自然没有听清野猪们说了些什么,不过,冯奇飞的话他是一清二楚的。从冯奇飞的话里,他可以推测出野猪们说了些什么。他很奇怪冯奇飞怎么会听得懂野猪们说的话。在这紧张对峙的时候,他不能提出这个问题。他自然很紧张。他原本跟着冯奇飞走进野猪中间去就很担心,但冯奇飞走进去了,他不能不去,更不能退后。尽管有漫山遍野的野猪,但没有带头的野猪,大群的野猪也不会向他们进攻,而他担心的就是有一小部分野猪会冒险向他们俩发起进攻,这样便会带动全体野猪。事实上,确实有这么几头胆大的野猪带头了,他的担心成为了事实。如果不是冯奇飞懂得野猪的语言,也许他们俩就要面临巨大的危险。不过话也说回来,要不是冯奇飞成了它们的仇人,这许多的野猪也许就与他们相安无事的。
冯奇飞拉他离开,而且所有的野猪没有猪司令的号令,也没有向他们进攻的意思。它们都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赶快与冯奇飞往回走。他明白那些野猪是害怕冯奇飞的,只要有野猪冲上来,冯奇飞那把柳叶尖刀便会神奇地一眨眼的功夫,在一批野猪的咽喉处捅上一个小小的却致命的窟窿。不过真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俩最终不会有好的结果,必定力战而死,很可能要被这许多的野猪踏成了泥浆。他们俩不可能杀死这漫山遍野无以计数的野猪。而且,真要杀死这许多的野猪,一定会血流成河,岂不是太凄惨了。他看见大部分的野猪并没有成为冯奇飞说的异化为所谓的人妖猪。
他们仓促间也不可能去寻找哪一条路是正确的。许多的路都没有明确的标志。他们走了一段时间,还在蛛网似的似有似无的路上徘徊。周宇方说他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难道现在迷路了吗?难道是那个猪司令在捣乱,给他们设置了路障吗?不过这时候早已看不见野猪,脱离了那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冯奇飞站住了,不再跟着周宇方瞎走。他将小指头放进嘴里,鼓足气,一声尖锐的哨音从他嘴里飞出,像是一支响箭冲向远方。周宇方听着这奇怪的哨音,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他想这一定是冯奇飞在招呼自己的黑炭头。黑炭头能听见这声音吗?它能找到这个地方吗?黑炭头也许会来,他的那匹马也会跟着来吗?他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