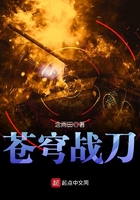他觉得一道强烈的电筒光直射到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皮猛烈地颤抖了一下,他只能闭得更紧。紧接着又听到那种猪死之前的咕噜声,明明白白是冲着他来的。他想,你们这些死猪叫唤什么呢?我反正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杀了一辈子的猪,我在每头猪的喉咙里捅上一刀,猪都要发出一阵这样的声音,我从来就没有听懂过,早知道你们也是发出一种这样的声音,我应该早就要研究它的。如果研究好了,我现在也就一定听得懂了。
他觉得有一只手在枕头边搜寻,野蛮而凶狠。这是他们这一群东洋人吗?东洋人不是很讲文明礼貌的吗?他听人说,东洋人见到人了,都会鞠躬行礼,他们今天不给我行礼倒还罢了,怎么反倒在主人的枕头边搜寻起来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人吗?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人就是强盗,土匪,不管哪个政府,都会要剿灭他,抓住了,没有任何理由,就要杀头的。难道东洋人就是这样的强盗,从他们遥远的国度,一路抢劫到了我们祁山县的吗?我的枕头边有我的烧饼袋,是我的儿子买来给我作粮食的。烧饼也是我的所爱,是曹胡子铺子里的烧饼,是有名的好东西,怎么随随便便让你们这些强盗抢走呢?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了烧饼我吃什么?我就会饿死。我饿死不要紧,心里这口气憋不住,就是死了,也不会舒服。但是,他虽然心里是这样的想像,但是一定要眼见为实,也许说不定是什么野兽跟着进来了,闻到了我的烧饼的香气,扑到我的枕头边,要吃我的烧饼也说不定。
他猛地睁开眼睛,借着那一道强烈的手电筒的光,一个浑身黄色军服的人,这种式样的军服他当然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国军的军服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想必就是穿军装的日本人了!原来日本军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比中国人也差不多。中国军人也有很凶恶的,但比较起来,没有对老百姓凶成这个样子的。他又想到了一种动物,那就是凶恶的狼狗。狼狗他见过,那是有钱人家里喂养的,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它一跃就会把人扑倒。那是没有一点人性的家伙。他见了都要避开的。但是,现在他面前的还是一个人形的家伙,不是狼狗。是狼狗他不说什么了,如果还是一个人形的家伙,他就不允许了。他听见他们——弯腰在他枕头边拨弄的军人,另外还有旁边站着的三个军人笑成一片。“烧饼的,好东西,很好吃的。哟西,全部的带走,统统的带走!”这些狼狗一样的人形,竟然也会几句几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在这里横行霸道。如果这些人不学着讲几句中国话,他也许只将他们完全当作了狼狗之类的动物对待,现在他们竟然还说着中国话来进行抢掠,他的气不打一处来了。
他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力量,一把就抓住已经被那个军人拎起来的烧饼袋,紧紧攒住不放。那个军人用尽了力气,就是抢不走。这时旁边一个军人嘴里骂着:“八嘎!死了死了的。”一边端起了枪。他看见枪口对准了自己。那枪口本来是很小的,但是,在他模糊的眼瞳里,竟然放大得有如一个巨大的炮筒。他觉得那个大炮口就要放射出一发巨大的炮弹,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会被炮弹轰炸得粉碎。就在一刹那间,他的右手一下了就摸到了褥子下的那把杀猪刀。杀猪刀被手电筒黄色的光照着,映出令人惊悸的寒光。就在那一瞬间,也许在场的所有的人的眼睛都被杀猪刀的寒光刺盲,也许他们慑于杀猪刀的雄风,那些日本人还在呆楞着的时候,他的那把杀猪刀就如他平日杀猪一样的快速,捅进了在他身边弯着腰的那个军人的喉管里。杀猪刀长约一尺左右,却捅进去深及刀柄,很可能捅穿了那个军人的肥脖子。那个军人说不出话来,但又要努力说出什么,而喉管已经破了,声音到喉管处漏了风,变成了真正的被捅破喉管的猪发出来的咕噜声。他已经好长时间不杀猪了,也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被杀的猪那最后发出的咕噜声。他现在听到了。他感觉很过瘾,露出了笑容。
经过这一番折腾,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想放下自己的一双手,甜蜜地睡一觉。但是下意识里他觉得不能就这样放松了手,两只手都不能放松。他左手攒紧的是他的一袋烧饼,是他的粮食。他不能让他的粮食去喂一群像人一样的狼狗。他的右手攒紧着一柄刀,他虽然觉得已经深深地刺进了那只人形的狼狗的咽喉里,但是他担心一松手,那只人形的狼狗又会活过来。那人形的军人已经躺倒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力气去捅另一只端着枪的人形的狼狗,他能够捅一个也就够本了。就在这时,枪响了,另外的几两个人的枪也响了。接着每个人还开了第二枪。枪弹的硝烟在窄小的地洞里弥漫,发出呛人的辣味。他一时间身上中了数弹,就像有人开玩笑,在他身上捶了几拳,一点也不痛。但是他知道自己会死,只要被枪打中了不痛,死有什么要紧呢?他将力气留在两只手上,自己闭上眼睛走了。
那几个日本人没想到进城的时候没有遇到一个抵抗的军人,反而被一个躺倒在病榻上的骷髅人杀死了一个帝国的军人。八嘎牙路,一定要报复!他们抓住那个已经死了的同伴,想要抬出洞去,但那把奇怪的刀子被刺进了脖子,而那把刀子却无法从病人手里掰开了拿出来,只好抓住同伴的脑袋,从那把刀子下拨出来。
他们又用手电筒朝地洞里乱晃了一通,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病人手里攒紧的那一袋烧饼,对他们发出诱人的香气。他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了。连日的打仗行军,现在只感觉肚皮贴到脊背上了。本以为进了城能找些吃的,可恨这里的老百姓将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带走了,或者埋起来了。好不容易发现了这个病人的烧饼,让他们大喜过望。他们一定要将这一袋烧饼夺到手。他们将同伴的死尸暂时丢在一边,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烧饼上。“烧饼的,快快的拿过来,米西米西的。”他们去扯那个烧饼袋,但是那个死老头却把袋子捏得铁紧。他们不甘心折腾了半天还吃不上一个烧饼,何况中国的烧饼是那样的美味,而且还是用一个帝国的军人的代价换来的。他们岂能就此罢手。他们用刺刀挑开袋子,将烧饼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每人叼一个在口里,一个劲地咀嚼,连声说:“哟西哟西,中国烧饼大大的好。”上面的二、三个烧饼溅满了老人的血,他们也一并吃进了口里。尔后,每人分了几个,才心满意足地抬着同伴的尸体走出了地洞。
走出洞来,想到要报复,却想不出怎样报复。那个老人已经死了,另外屋里也没有别人。日本人上了吊脚楼,来到堂屋里,然后走到大街上,将几颗手榴弹拉开了,丢进屋里,轰的一声,将房子炸塌。
冯奇飞他们商量,决不能让冯伯伯就这样窝窝囊囊躺在在地洞里,要让他老人家风风光光地入土为安。现在日本人不是贴出了告示,要老百姓回家,与皇军大东亚共荣吗?死了人总是要发落的吧。为老人办丧事,也是向鬼子示威。如果有人来找麻烦,就齐了心对付。大家统一思想,准备行动。
冯奇飞对父亲说:“爸爸,我们都是来看你老人家的。但是,儿子来迟了,没能救出你老人家,是儿子的不孝,但是,罪责在日本鬼子。你的形象已经清清楚楚将你是怎么与日本鬼子搏斗的经过详尽地告诉了我们。我们都知道了,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你是我的好父亲,我也要做你的好儿子。我们大家都会在你的鼓舞下,好好活下去的。你老人家就放心地去吧。”
然后,他从老人手里,轻轻地抽出了那把杀猪刀,又轻轻地拿下了那只已经被刺刀撕开了的烧饼袋。江冬琳很是奇异,原来无论是奇飞还是她,费了很大的劲也无法从老人手里拿下这两样东西,现在竟然就这样轻轻地拿下来了。她仿佛看见老人在笑,平时见了他一惯的那种笑。他的笑很神秘。她感到自己身体轻微的抖动。她很快就明白了这里面的道理。她觉得老人是同意儿子说的话的,更是希望儿子这样做的。大家将老人蒙上白布,抬出地洞,放在吊脚楼上面堂屋里的地面上。收拾好地面上的废料瓦砾,扎了一个灵堂。因为老人久病不愈,棺木早就准备好的,找出来,入了敛。
但是一时找不到吹鼓手,还有念经拜忏的道士。本来河街这一条长街就是集结的手艺人,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早些天听说鬼子要来,差不多都走光了。近些年,由于鬼子飞机轰炸,县城里人死得多,人们手头又紧,许多人也就没有按照习俗举办丧事,草草地找一付棺材,抬到山上埋了。那些办丧事的职业人员反而没事干,日子过得很艰难。尽管艰难,日子还是要过的,生命还是保的,日本鬼子不能不躲。找了不少的人打听,找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罗师傅,一个叫崔师傅。两个人还是不够,一个乐器班子,至少也要五、六个。但是这二个人劲头很足。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重操旧业了,肚子饿着,手也发痒,只是一直没有人请他们做丧事。现在听说冯奇飞要为日本鬼子杀死的父亲办事,就来出主意,说专业人员凑不齐没关系,只要找到锣鼓响器,有了打鼓的定调,还有会吹唢呐的,别的人跟着敲打就行了。他们两个人,一个会打鼓,一个会吹唢呐,一整套响器他们家里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是了。为了把气氛搞起来,又临时找来几个街上看热闹的,跟着两个师傅敲敲打打。开始并不成调,洋相百出,慢慢的也就好了,象那么一回事了。
江冬琳找到关了门的布店,叫开了,买了好些白布。周宇方和丫姑、兰芝用白布将灵堂围了一大圈,还扎了一朵大白花,缀在灵堂上方。气氛布置得甚是庄重肃穆。同时,她用针线简单地为冯奇飞缝了一套孝服,也为自己做了一套,立即穿在身上。周宇方提出,他们也一样的要穿上孝服。江冬琳接着做了三套,五个人一片缟素。冯奇飞不同的是身上系了麻绳,这是区别孝子的唯一标志。
不太成调的乐器一旦敲打吹奏起来,原本如一片荒漠的县城竟然有了一丝活气。乐器的声音传得很远,也许整个县城都传遍了。之前人们只听到飞机的怪叫,枪弹的呼啸,日本人巡逻部队铿锵的脚步,似乎要踩死一切生命的威胁,间或有凄惨的哭叫和悲怆的呼喊,除此以外就是惨淡的日光和死寂的炎热。这一切宣告世界已经进入了末日,不要对明天抱有任何希望。如果这座县城里还有别的生命存在,也只是一时的苟延残喘。冯奇飞家办丧事的乐器敲打起来,人们立即竖起了耳朵,脸上露出了活泛,好像太阳重新放出了热能,在天宇上开始移动起来。这座原本已经堕向地狱的罪恶的城市,被这一阵突然暴发的热烈而冲撞的力量所制止。地狱之路被截住了,堕落的滑行被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