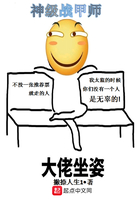这个晚上有星光,给大地蒙上一层模糊银灰色。冯奇飞与周宇方在树木里穿行的时候,模糊的光亮被层层的树叶遮敝,但是,他们凭着超凡的夜视功力,视黑暗如白日,根本不需要担心撞在障碍物上。来到这一片无遮无碍的空地上,更加增添了他们视力的亮度。冯奇飞清楚地看见了野猪身上如短箭一般的黑毛,在星空下发出油亮的光。那两只红色的眼睛也许是这种动物特有的色彩,以便于在漆黑的夜晚,如两只冒着红焰的火炬,照亮它们能够准确地找到猎食的地方。也许那两只眼皮重叠的眼睛原本就不是红色的,因为想着要侵入人类美好的家园,去啃食那美味的果实,但又一定要遭遇人类无情的驱赶,便先红了眼睛,决心与人决一高低。
但是,人渐渐地来得多了,从四面八方来,紧紧地簇拥在敲锣的人的周围。伴着敲锣声,所有的人口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手里挥舞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农具,声势浩大,似乎只要一瞬间,就可以将六只野猪捕杀。要是别的一般野兽,早就被吓得骨软筋麻,只要有一处没有人,一定会撕开四蹄逃之夭夭。但这六只野猪就是不走。它们并不像众多的人类一样紧紧地簇拥在一起,还有人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生怕前面的六只畜生有一只窜过来,冲向自己,将自己咬死,即便大家再涌上来,七上八下的打死它,还有什么意思?他作为一个人已经被咬死。他出人头地只有死亡。他一个人没必要冲出去。他不出面,应该还有别人出面。因此,这一大堆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冲向前去,首先向野猪进攻。
六只野猪并不互相靠拢,它们还是一个一个地站在原来它们的位置上,好象并不需要依靠别的野猪的力量。它们没有一只随便就向后退,而是向前踞着两只爪,似乎随时有可能朝后一用力,就会像一支飞箭般射向人群。人群簇拥着,呐喊着,铜锣敲打着,工具挥舞着,与六只野猪对峙。而六只野猪像六块黑色的大石头,分散在空旷的前方屹立。野猪们在提高警惕的同时,不像人那样高度的神经紧张,它们有时候还戏弄般地低下头,咬一根地上的包谷棒,叼在嘴上咀嚼,意思是,我偏要吃,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的上来啊!它们时不时地抬起长长的鼻子,鼻子下的嘴向着人群嚎叫着,就是向人类宣战。
冯奇飞看见,那六只野猪的眼睛比先前更红了,简直没有了眼白,全变成了一片红,红得像要滴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会有这样的野兽,疯狂起来全改变了原本的形相。其实,它们的本质还是一头猪,是猪的形相。他是一个杀猪的。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杀了好几年的猪,究竟杀了多少头,他记不起来了。他闭上眼睛也能看清楚一头猪的全身结构。他这时没有像别人一样跟着呐喊起哄。他站在一旁,默默地仔细地研究这六头野猪,无论大猪小猪,老猪幼猪,其生理结构完全一样,只是生性的不同。他杀过的家猪愚昧疲癞,而这些野猪狡猾凶残,如此而已。他没有杀过野猪,不知道这种野猪是不是真正皮厚肉硬,刀枪不入。如果真正刀枪不入,他就杀不了它,他身上锋利的柳叶刀也成了一把废刀。据说一般的猎枪还打不死它,冯奇飞就有点费踌躇了。
这六只野猪中,有一头是为首的。它处在另外五只野猪的中间,显得十分的高大凶猛。其它的五只野猪似乎都看它的表现行事。它这时不再站立,而是整个身子坐在后面两只脚爪上,用前面的两只脚爪支撑着上身,高昂着它的猪头,既不乱动,也不乱叫,两只红得滴血的猪眼,像小孩玩耍的滚动的玻璃珠,不断转动着,观察人群的动静,以便于采取相应的措施,指挥另外它率领下的五头猪,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冯奇飞想,他如果真要冲过去杀掉这些畜生,他开始不会理睬另外五只,而直奔那只中间的指挥官。只有先杀掉那只控制者,其它的五只就好办了。他相信他一定能一刀就插进那只首猪的致命要点,就像他已经杀了的许多只家猪一样。
这时,村长三爷来到他身边,说:“冯奇飞又来了?你还真把我们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了?”
“是呀,村长不是欢迎我将这里当作我的第二个家吗?”冯奇飞高兴地说。他他和江冬琳两个家里的人都住到这里来了,难道这里还不算他的家吗?即便是三爷也没有理由说这里不是他的家。“您看,我来了也不起作用,只是凑凑热闹罢了”
“嘿,我知道你想杀死它们。你武艺高强,也许杀死它们没有问题。但是万一杀不死,野猪又活过来了,就有危险了。”
“没关系,让它们找我好了。”
“不过,”他迟疑着,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呢?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
“你虽然将我们这里当成了你的第二个家,但毕竟是第二个。你的第一个家,也就是你真正的家还是在县城,而不是我们这里。负伤逃走的野猪不会到县城去找你,它们还是会找到这里来。它会邀来更多的野猪到这里找我们的麻烦,破坏我们的生活。因此,我还是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三爷的话说得冯奇飞很不好意思,就好像他冯奇飞是个沽名钓誉,只顾自己出风头,而不管别人死活的无耻之徒。他的一颗心骤然冷下来,想要当场去杀死那些畜生的想法放下了。他说:“好吧,三爷,我现在不杀它们好吧。等以后你们想通了,或者我不得不要下手的时候,我再出手。”
三爷客客气气地与他分手,说:“你也不要跟着他们叫喊,那样叫喊是很要力气的。你就站在这里看着。说实话,我们山里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玩,你就当看一场把戏吧。嘿嘿。”
这时,周宇方有点不耐烦了,拼命地敲响铜锣,朝前面冲过去,许多人就簇拥着他,向着蹲踞着的野猪们前进。各种工具高高举起,就像从天而降的暴风骤雨。野猪们终于害怕了,它们毕竟势单力薄。那只为首的老猪首先爬起,向后退去。其它的五只也纷纷后撤,一溜烟跑得不见了踪影。山民们乘势追赶,声震夜空。然后各自收兵回家。
冯奇飞与周宇方走在路上,将三爷对他说的话学说了一遍。周宇方说:“三爷素来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什么事都想求稳不乱,总是担心出乱子。不过,他还是个好人,在人们心里威信很高,大家都拥护他。”
冯奇飞鼻子里哼一声,说:“如果有一天山里所有的野猪都来吃你们地里的包谷、红茹、甘蔗等农作物,你们也让它们吃?它们吃光了,糟蹋光了,你们什么都没有吃,就等着饿死吧,到那个时候,我看他还能不能稳定。”周宇方没话说。到家后他们赶紧睡觉。
早上,大家吃了饭,冯奇飞告辞去县城,大家送到院子的槽门口。
冯奇飞轻松地笑着,轮番与大家摇手致意。他的眼睛停在江冬琳脸上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他的眼里似乎有着特别的意思。他想江冬琳应该从他的眼里能够看得出他的想法。昨天晚上他嘱咐了她的一些话,他要求她不要忘记。还有别的一些意思,她心里明白就行了。但是江冬琳却没有特别的表情,平平常常,就像他出去挑一担水,一会儿功夫就回来的。她现在就顶着个男孩子的寸发头出现在人们面前,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的人,还真以为她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男孩。只是皮肤白净了一些,动作文雅了一些。这样的男孩不是没有,少一点而已。不过一眼看去,她还真不像一个山里的男孩。
在冯奇飞眼里,她不管是辫子还是寸发,不管装束是男还是女,他还是看她就是江冬琳,他看她的眼神就是与别人不一样。大家七嘴八舌,要他早一点到县城,早一点见到父亲,早一点回来,有危险的事不要做。周妈妈一再对他说,一定要将父亲接过来。
他转身朝出山的路上走去。他两手空空,连一个简单的包袱都没有,这样走起来轻松,速度也快。他心里焦急,恨不得一步就进了县城。他本可以迟一点走,即使很早就到了县城,他也有可能白天进不去。江冬琳的话有道理,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晚上进城,不要让日本鬼子发现,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他大可不必走得这么快,完全可以慢慢地走,看看山景,想想心事。但是他忍不住,一双脚走起来飞快。他的头脑是清醒的,有时候也下意识地放慢步子。他不想到了城外没地方去,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岂不是更难受?他走在路上就觉得难受了,甚至于还没有前天来山里逃难时有意思。
前天他一直背着江妈妈,当然很辛苦,但是冬琳陪在他身边,安慰着她的妈妈。他耳里听着冬琳轻柔的说话,眼里看着冬琳亲切的身形,就一点累的感觉也没有了。哪怕就是昨天他一个人在登天门上打坐看县城,他也没有觉得孤单。他想到就在峰下,冬琳在等着他,她在等着见他。他只要飞身下到峰底就能见着她。他感到他的一颗心有着寄托。何况还有周宇方,他的多年的好朋友,这两天也守在他的身边。他与他在一起,就几乎是与一个世界在一起,与整个社会在一起。江冬琳和周宇方对他来说,各自有着不同的意义。现在却突然一个也不在身边,心里怪怪的,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还有那个丫姑,他以前来过一次,也见过她,她几乎就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丫头,跟在哥哥身边,用着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她好像一直没有与他说过话。这一次竟然如此大大不同,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不相信现在的这个丫姑就是之前的那个丫姑。现在好像什么事都明白似的。昨晚他去她与江冬琳的房间,她就借口磨刀出去了,让出空间与他和江冬琳单独相处。她一口一个飞哥哥地叫,叫得他心里甜甜的,她还非逼着他带她作徒弟。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资格带徒弟,但是他带着她练功难道还不可以蚂?这之前他早就教周宇方这样做了,难道周宇方就是他的徒弟吗?这是他不能承认的。只有好朋友他才能这样,不是好朋友,他才懒得这样做哩。不是还有舅舅师父的规定吗?为了朋友,他已经违背了师傅父的要求。不过,他自认为并没有违背,他只是为了帮助他的好朋友而已。他现在又在帮助丫姑了。说实话,他是喜欢丫姑的,也是真心实意想要帮助她。一个年龄不大的女孩,练功的时间并不长,还是她哥哥为了解脱她对他的纠缠,随随便便地教教她,也许就是为了好玩,她却当作十分重大的事情认真对待,练得很有成效,某些方面甚至比她哥哥还要强。在冯奇飞看来,丫姑还真是一块练功的好材料。有丫姑在,气氛就热闹,严肃的事情也变得轻松了。冯奇飞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的,但是,好好地相处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一天多的时间,他与他们又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