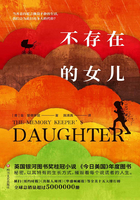曹姥爷蹲靠在他那口漆得黑亮的棺材旁,用仅有的几颗黄牙咬紧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吸一尺以外的烟火。烟锅里的火亮儿一闪一闪映照着他树疙瘩似的脸。
知道做棺材哈料好?当然是槐木——见过棺材粗的槐树没?俺见过……
曹姥爷说,那棵老槐是清咸丰年间栽的,老黄河堤上就这一棵哕……
无人知晓它是谁栽的,它就在这满是黄沙的故堤上慢慢长起。赶到民国初年,它已是干粗枝壮,巨伞般地撑在天地之间。过往行人走到树下必驻足歇汗。坐在裸露的树根上仰望稠枝茂叶,清凉之气通身贯体。
这里压着三省地界儿,便有一小庄悄然诞生于堤下——先是外省的几个卖艺者搭庵小住,于是茅屋瓦舍衍起。四方流民歇息之后,瞅着下边是个好去处,便投庄落户。这庄儿便有一个很怪的名儿——自留庄。
自留庄的后生早早就练武,这老槐树下的三分荫凉地就是他们的习武场。秋后冬闲,这里就摆上擂台,轮番叫阵,哄然之声遥响半里之外,招惹得邻村外省的高手都到这里一试身手——自留庄由此扬名三省。
曹姥爷说,庄里面留郎当为第一擂主……
民国九年,庄里人在老槐树下捡到一男婴。这男婴被锦缎所裹,身缠一白带,上书几个字。庄里识文断字的不多,又看那些字洋不洋汉不汉的,只认得一个“郎”,便叫他“留郎”。
留郎落身在自留庄,这个来瞧,那个来看,都道是老天送来的。正奶着孩子的小媳妇便解开怀让其饱吮一顿。留郎头发稀,眼睛倒有神,双手紧捧丰乳,吮一阵便丢下奶头,愣愣地仰看,眼仁里亮亮地涌动着一丝丝泪花……
到了五六岁,庄里人便教他习武练功。打着、吵着、摔着,竟十分长进。十八九岁,留郎便在老槐树下摆擂。可怪,他在这儿摆擂没栽过,横竖都能赢。有他这杆旗立着,自留庄平添了几分豪气。
那目天刚亮,一队鬼子突然包围了自留庄。全庄的人都被赶到老槐树下。鬼子头是个胖少佐,颇有几分学者风度。他骑在高头大马上,挎着指挥刀,双目被血色晨光染成腥红,目光老是在年轻人脸上扫来扫去,好像要考究出什么。少佐的侧后是个“二鬼子”。
看着阳光里浮起一片人头,少佐的嘴角全泛起野猫似的微笑。他下了马,将指挥刀戳在地上,戴白手套的右手轻轻在半空中文雅地一挥,“二鬼子”便泥鳅似的滑到前面。“二鬼子”发话了,他说皇军知道自留庄人会武功,今儿个专来领教。
少佐一摆手,四个武士装束的鬼子兵昂头挺胸地站到了场子当中。一式的模样,都将两臂叉于胸前。
你们谁出场?“二鬼子”对着人群喊。庄里人看着,无人应。
“二鬼子”又吼了一遍,人群里便有了骚动。
留郎从人群里出来了。
那日,他刚剃过头,样子很憨。阳光在头顶上溜溜地亮。
再出来几个!“二鬼子”对着人群喊。
俺一个就中了。留郎说,拿眼瞅瞅那胖少佐。两人的目光撞作一堆儿,少佐扶指挥刀的双手便颤了一颤。
是文打还是武斗?留郎冷着脸问。
少佐说来文的,不用刀枪,留郎就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
留郎脱下汗渍渍的粗布褂儿丢在身后,将裤带煞了又煞,身上的肌肉便鼓暴成树疙瘩。好了。他说。
少佐打了一个手势,搏杀就在万仞阳光中开场了。
那边是一个一个上的,留郎不慌,避实就虚,一阵拳脚便撂翻一个。
打倒一个,便喝喝笑几声,形如往常。笑到最后一个,他的声音特别大,庄里人都替他害怕:留郎恐是疯了。
鬼子羞怒了,将留郎绑在老槐树上。那些被击倒的武士便歪歪跌跌地爬起来,朝留郎身上乱击。留郎早运足了气,竟不伤筋骨。
少佐的目光冻住了似的透出吓人的寒气。“二鬼子”贴着少佐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少佐嘴角便翘起一丝冷笑。
留郎又被双手合抱地捆在槐树上。脸贴树干,眼光撒向堤下的原野……
“二鬼子”上前搔留郎的胳肢窝,笑啊,笑啊!
留郎忍不住,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笑,人们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少佐阴着脸,将指挥刀交予手下,拽下手套,在留郎背后细细地看。
他“嘿”地叫了一声,猛地朝留郎宽厚的脊背上击了掌,一股鲜血便从留郎的嘴里直喷出来,顺着粗皱的树纹往下淌。再一掌,又一股……
鬼子走后,庄里人上前去解留郎。绳子全脱了,留郎还是紧紧地拥着老槐树不动,罩血的眼珠子睁睁地瞪着。几个人扒不动他,一瞧,手指头像抓钩似的深插进树皮里。
曹姥爷说,留郎死得惨,精魂不散……
当天夜里,黑云盖顶,惊雷吼鸣。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将天空撕碎了再撕。有人瞅见,一条银蛇从老槐树顶上蹿起,与半空中的闪电咬住,随着“喀嚓”一声炸响,老槐树刺啦啦被劈成两半,呼隆隆倒下一壁。风雨中,留郎的笑声敲震着庄里人的耳鼓:哈哈哈,哈哈哈……
留郎的笑声钻进了人们的脑髓,搅得自留庄不得安宁。有人说,留郎的魂儿被老槐树夺去了,不刨掉它,全庄都会疯!
一说刨树,锛、锨、镢都上了故堤。只几袋烟工夫,老槐树的根全被斩断。明明是刨透了,却不倒,用绳子拉也拉不动。
几个上了年纪的就跪下了,留郎,留郎,你走吧……
就见老槐树颤了一下,发出尖裂的声音。又颤了一下,吓人的断裂声更紧了,细听起来倒像留郎的笑声……
树是倒了,可几股粗大枝干就像手指似的撑着。
夜间,再也听不到留郎的笑声。老槐树被肢解,做了两副好棺。
翌年春,一场春雨过后,树坑里长出一圈圈毛蓬蓬的嫩芽。有人听见,留郎的笑声又在这嫩芽丛中复生,只是很细很细……
曹姥爷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