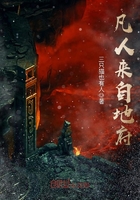冬季的到来意味着北京城一年中最糟糕的时光拉开序幕。当然这个所谓的最糟糕并不具备客观意义,只是对陈非个人适用。他很害怕寒冷,害怕窗玻璃上凝结的水汽,害怕地上冻成冰的脏水,害怕在寒风呼啸的早晨硬生生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去时的无奈,尤其害怕挤车。
北京城的冬天很冷,人们个个裹得像狗熊,想像一下几百万头狗熊硬往公车里挤的场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上车之前,所有人在公交车站冷得像冰坨子,只能靠原地跳健美操来取暖,车子一来立刻调动起全身之力,挤、压、按、顶、推、踹十八般武艺齐上,到最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每个人的体积都比夏天增长百分之三十,但居然所有人都能最终挤上车,可见中国人的弹性天下无双。
陈非自从长胖之后就变得爱出汗,冬天挤完车尤其出得厉害,被车上的暖气一催,能感觉到汗水顺着背脊往下流。等到下了车,温度一下子下降了二十多度,冰冷的秋衣贴在背上,被风一吹别提多难受。陈非冬天总是感冒,有一大半原因都是这个。再加上处长一听到请病假就一脸死了娘的德行,生病的痛苦总会成倍增加。
这时候陈非就会想起家乡,那里的冬天其实未必比北京好受到哪里,因为当地没有暖气,所以室内外温度差不多,走在路上会感觉挺好,回家坐下一会儿就会开始发抖——和北京正好相反。如果没有早起挤车上班这回事,他没准会觉得北京的冬天其实挺美好的,但由于该前提不成立,所以故乡的冬天在记忆里被大大美化了。每到感冒时,陈非就开始怀念故乡的冬天。
这一年冬天陈非还没来得及感冒,却已经开始计划把年假用了,在冬天的时候回一趟家。这一小半是出于那段被美化了的关于故乡冬天的偏差记忆,另一小半是最近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防止过劳死,一大半的原因还在于回去拜访一下亲友。过去陈非很不乐意拜访亲友,总觉得那种满面堆欢嘘寒问暖的场面活像在演话剧。但现在他不得不去试试水,兴许哪个亲戚金口一开就能借他几个平方什么的。太后不怒自威的面容依然压在心头,那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哪怕要为此演话剧陈非也非得硬上不可。
此外陈非还有一个用心:冬天回家看看,春节就不必回去了。陈非的家族擅长生育,他还不到三十岁,膝下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已经有一个加强排。这些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平时见不到,一到春节就都从地底下钻出来了,一个个挂着天真无邪的笑容向你伸出细嫩的小手。陈非每过一次春节就好像遭遇一次鬼子进村,那点年终奖都填到压岁钱的无底洞里去了。所以陈非想到春节就眼前一黑,能逃过一次算一次罢。
好在进入冬天之后,基本上也是展览业的淡季了,没什么展会值得费心的,所以处长虽然还是一张死了娘的脸,好歹批准了这趟年假。
陈非买了火车票,坐上了火车。这时候正是旅游淡季,而春运高峰还未来到,所以火车上人并不多,可以选择经济的硬座票。春节的时候可不一样,陈非动用一切关系都非买到卧铺不可,否则那就是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春节时,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来到了硬座车厢,其中一大半只买到站票,于是就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或者行李上,摇摇晃晃几十个小时,下车时个个小腿浮肿精神恍惚。在那种车厢里,上厕所都要排一小时队,吃饭时全车厢混杂着各种品牌的方便面味儿,闻多了这种味道就会让人反胃。
现在总算不错,车厢里并没有坐满,有让人伸展筋骨的充裕活动空间。陈非看着窗外每年都要看上两次、早已烂熟于胸的风景,间或和苏小麦发两条短信,觉得这三十多个小时也不是多么难熬。但后来又开始变得难熬,是因为在中途某一站——陈非已经记不清是哪一站了——上来了一个话篓子。上来一个话篓子本来没什么,如果该话篓子碰巧坐在你身边,那就有些要命了。
后来的十多二十个小时该话篓子就在陈非的座椅对面聒噪不休,谈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保护、大学生就业、我家隔壁养狗的那家人真是太恶心了等诸多方面。陈非面带微笑如拈花听禅的老僧,手里不住发着短信向苏小麦抱怨:操他祖宗,这傻逼的嘴简直是用宇航材料打造的,怎么不说死了他丫挺的!
苏小麦的短信很快回来了,一张暧昧的笑脸之后接了几个字:听了你的形容,我想起你妈了……
这话把陈非噎得够呛,想起很快要面对自己的老娘,回家的喜悦登时淡成了白开水。他把视线从手机上挪开,转到对面话篓子的脸上,目光中充满愤怒。话篓子看了这眼神知道不妙,连忙住了嘴,不然说不定陈非真的会一拳给他揍到脸上。
提到陈非的娘,那是一个绝妙的人物。前文提过,陈非小学五年级时,为了争一张乒乓桌,被二年级小孩打得脸上开了花。二年级小孩的娘十分得意,掏医药费时无比爽快,那副得意的笑容把陈父气得够呛。陈非娘听闻此事,二话不说,当夜直奔对方家,堵在门口叫骂了两个小时,最后派出所民警来了才把她劝走。
从各方面看,陈非娘和太后都是两个阶层的人,相比太后的风度,陈非娘基本就是个锱铢必较的市井家庭妇女,拥有吝啬、嘴碎、泼辣、强悍,绝不吃亏等诸多优点。由于摊上了这样的老婆,陈父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喝闷酒生闷气,听陈非娘唠叨不休。
陈非此前曾经带苏小麦回过一次家乡,后来苏小麦就再也不肯去,因为“你妈输入的信息量太大,我处理不过来”。这一点陈非打小就深有体会。老娘光是数落单位里那个讨人嫌的工长就可以一口气说上五六个小时,还不带重样的。她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两分钱可以磨整整一中午,磨到卖菜的哭笑不得跪地唱《征服》为止。
但最可怕的是不要让她提起她儿子,也就是陈非。陈非爹娘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钱,至今还住在单位分的陈旧的福利房里,此生唯一的指望就是儿子。而陈非还算争气,读书时成绩一直不错,于是就总被陈非娘挂在嘴边。等到陈非考上航院,那可不得了,在老娘的认知里,北京的大学一定是好东西,恨不能在脑门上用红墨水涂上“我儿子考上航院了”。
但近两年老娘的态度有了一些转变,因为她发现陈非在北京工作后,似乎也并没有一夜之间大富大贵,相反连结个婚都结不起,这离她的期盼实在相差甚远。她想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陈父还想弄辆车开,在陈非面前暗示过好几次了,但陈非头顶压着太后,已经足够焦头烂额了,实在不敢再加大补贴家用的数额,这让老娘更加不满。
陈非扳着指头数数,自己的一生好像都在让别人不满,上小学老逛电子游戏室让班主任老师不满,上中学物理老不及格让物理老师不满,上大学总是逃大班会让辅导员不满,上班后因为不能做业务让处长不满、能做业务了又让35C的武宁不满,谈婚论嫁的时候买不起房让太后不满。现在回过头来,连生身爹娘都开始不满了,这经常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话篓子后来一路上再也无话,陈非在沉默中下了火车。家乡的空气扑面而来,有一丝凉爽,但不像北京的那样寒冷,让陈非觉得很舒服,尤其在刚刚摆脱了火车上过热的暖气的时候。他找到公车站,等待着公车,忽然觉得好像这一路火车的颠簸都没有存在过,似乎是自己跳上公车就回到了家乡,再跳一次公车就能回到北京。
接着他注意到自己有意思的用词,不管是北京还是家乡,自己用的动词都是“回”,但人不能回到两个地方,总应该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回”,而另一个地方应该叫做“去”。家乡和北京,谁才是最后使用“回”的终点,这是一个有趣的谜题。胡思乱想中,陈非坐着公车进了家门。
父母已经准备好一桌子菜,恰如其分地像是迎接归家游子的规格。陈非闷头吃着饭,耳听得老娘絮絮叨叨。老娘过去的絮叨是无主题的,和火车上的话篓子一样,可以从政治经济一直跳到我家隔壁养狗的那家人真是太恶心了,但近年来发生了改变,陈非发现老娘的中心议题总是离不开别人家的孩子。张三的儿子自己开了公司,孝顺给老爹一辆新车;李四的女儿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孝顺给爹娘一套新房;王二麻子的儿子年薪三十万,刚刚把父母孝顺到欧洲玩了一圈,从希腊的女神像到荷兰的橱窗女郎都看了个遍……显然老娘有所暗示、有所渲染、有所针对、有所影射。陈非没办法,只能装傻充愣,饭碗边沿正反射出太后那张优雅的脸。
晚上睡觉时陈非被冻醒了,然后醒悟过来自己忘了开电热毯,他把家乡当成了北京,以为会有暖气片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热量保持室温。但实际上这里是家乡,没有什么暖气片,不开电热毯的话,被窝会凉的像冰。陈非打开电热毯,一边哆嗦着等待电热毯发热,一边想,我是不是已经很像一个北京人了呢?
这一年回家陈非没能借到一分钱,这甚至低于他的最低预期。在此之前他对苏小麦说,他有可能从他的二舅那里借到几万块钱,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陈非来到二舅家时,没有看到二舅,只看到哭哭啼啼的二舅妈。二舅妈见了陈非——确切说,是见到来了一个人,她才不管见到什么人了呢——哭诉说,二舅涉及商业诈骗,已经进去了,现在自己一个孤零零的弱女子,面对着一屁股债,真不知道如何是好。陈非陪上一声叹息,虽然二舅妈体壮如牛,体型酷似肯德基的外带全家桶,外貌怎么看也和弱女子不沾边,他还是留下了五百块钱。后来他才知道,其实这时候二舅妈已经递交了离婚申请了,但她还是守在家里,来一个人就哭诉一番,等哭诉到了足够的钱之后,才施施然离开,并且一分钱的债也没有替二舅还。苏小麦听了这个故事,惊为天人,连呼“女英雄!”
其他亲戚家里大同小异,不是老爹闪了腰就是儿子长了水痘,总之中国人的习惯是,只要有人来借钱,家里就一定要出事。陈非每走访一家,就听到一堆悲惨的故事,自然是借不到钱的,听完这些故事他就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只觉得满眼望去,空气中的每一处都飘着“惨”字。
为了省钱,陈非这一段奔波都坐的是公交车。家乡这一点做的不错,公交线路四通八达,还往往有座,比不得北京的人山人海。陈非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些不再熟悉的街景从窗外次第掠过,忽然就觉得这座城市很小。他十八岁之前可一点没觉得家乡很小,除了送喜欢的女孩回家时会觉得这条路实在不够长之外,大多数时候他都觉得天地很宽广,每一天仿佛都能发现点新鲜的角落。但在北京一泡就是将近十年,他已经习惯了北京的硕大无朋,北京的无边无际,习惯了十站公交线路以内的距离叫做“近”,习惯了打车时司机总不认识路、还得现翻地图。眼下回到家乡,才觉得这座城市是那么小,小到让人有些呼吸不畅。
看来北京已经溶入到我的血液里了,他不无悲哀地想,虽然这座城市是那么庞大,那么忙碌,那么让人茫然无措,但我也许还是爱上了它。这个发现让陈非心碎。他很想摆脱这种爱,又觉得摆脱它就像放掉自己的血液一样困难。精子游向卵子,我们游向北京,一切的一切都不容改变。
陈非忙碌了几天,一无所获,看看年假的时间快到了,于是开始准备回北京。临走前的夜里,他在自己那间狭窄的卧室里来来回回翻看着十八岁之前购买的所有书籍,这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习惯。陈非十八岁之前,电脑这种东西还很贵,不是他所能负担得起的,自然也就没有电子版的图书可以看,想看书只能掏钱买。但他的零用钱不多,买的书也并不多,所以每一本书都被翻过十七八遍了,然而作为一种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还是只能翻书。老爹在客厅里看电视,追逐着所有的新闻栏目,仿佛漏掉一点国家大事就会让他这个月少拿一百块工资。老娘不在家,出门和一帮同龄的老年妇女跳舞去了,但陈非以为她很可能只是借着跳舞的名头打听各种张家长李家短而已。
除此之外,冰箱在他的屋子里嗡嗡作响,阳台上的衣服被风吹得互相碰撞,那是因为陈非家太小,只能让他住这间直通阳台的,而且还得把冰箱和大衣柜都塞进去。经常在陈非睡觉的时候,父母就会进房来开冰箱、开衣柜、开阳台门,让他有一种自己睡在过道上的错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陈非一直到了大学毕业,才算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房间其实不属于他,而是属于房东。
所以说,假如没有房子,陈非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陈非并没有任何区别。虽然现在的陈非是一个肉嘟嘟的大胖子,十年前的陈非瘦得像根柴火,二十年前的陈非比现在足足矮了三分之一、嘴上连绒毛都还没长,但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共性,可以放入同一个集合里,该集合就是:没有房的陈非。
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呢?陈非看啊看啊,只看到前方一片黑暗,完全望不到尽头的黑暗。
他无端地唏嘘了一阵子,打开电热毯准备睡觉,这时候来了条短信。他以为是苏小麦的晚安短信,拿起来一看却是胡二发来的。这条短信很简单,统共就六个字。
“我和她复合了。”胡二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