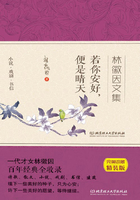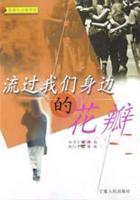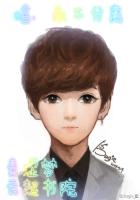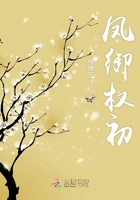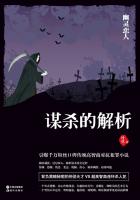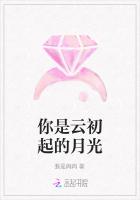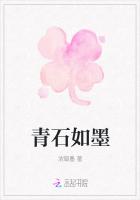一、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
陈寅恪1930年(庚午年)尝作《阅报戏作二绝》云: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石头记中刘老老,水浒传里王婆婆。他日为君作佳传,未知真与谁同科。(《诗集·附唐诗存》第20页)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原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后由外交部独管。新任校长罗家伦请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闽题写了“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立即令人刻成长牌,挂于校门。罗家伦走马上任后,身着少将制服,高谈纪律化,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有新气象,但仍不免“旧时代”之争权夺利。清华校长一职,就有三十多人争夺;甚至于还有比“旧时代”更“青出于蓝”之表演。陈寅恪作的《阅报戏作二绝》,就是对此一“新时代”略为表达的观感。
自清华学校易名后,国学研究院遂亦停办;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导师亦相继仙逝,陈寅恪成为清华园的泰斗,被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为教授。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传》中尝谓:“清华自易名后,先生任中文、历史、哲学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如‘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是时先生授课之余,精研群籍,史、集部外,并及佛典。”(《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19-220页)周一良也说:“1928年清华改制为大学,陈先生应聘为中文、历史、哲学之系教授。……”(《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1页)陈寅恪的教学和研究经常是相互配合的,从他给各系开设的课,即可知道他的研究方向已从佛教史研究,扩大到整个中国中古文史研究。自陈寅恪任教清华至“七·七”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计约十年。在这十年时间为其一生中,是陈寅恪最安静、最稳定之岁月,故也是读书最勤,研究最力,学术成果最丰硕之日子。主要是因为个人生活较为安定,图书资料较易获得,学术环境较佳之故。自1930年起,他虽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但并不负实际事务的责任,然于其研究工作却得更多之方便。陈寅恪此时的情况,由其长女流求的追忆中,窥知一二:
从记事起,我家住在北京清华园旧南院宿舍,与张申府伯伯、刘清扬伯母家为邻,……这段时期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的书房不大,窗前放下的那张深褐色书桌可不小,靠墙是高高的书柜,还铺设了一张小铁床,屋内很挤,孩子不可以进去玩,照顾教育孩子都由母亲担当,母亲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她自己在厚纸上写字,教我们认字、背唐诗。父亲每天出门老夹着一个夹层的布包袱,包着许多书本,大多是线装书,晚上照例伏案工作,家中时有老师、同学们来谈话,如吴宓伯伯、浦江清叔叔等。……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外国语言。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研究梵文。(《追忆陈寅恪》第411-412页)
陈寅恪每周必与爱沙尼亚裔俄国学者钢和泰作一两次学术讨论。钢和泰是俄帝国所属的爱沙尼亚之贵族,早年在德国专攻过梵文学,后复至印度任职。他为了论证古印度迦腻色迦之年代,欲从中国古籍中钩沉出证据,故而于1916年从莫斯科动身途经西伯利亚来到北平。随后,俄国爆发了革命,他家的财产被没收,遂无经济来源矣,只能在中国教书谋生。1918年,北京大学聘任他授梵文及印度古宗教史;当时从钢氏习梵文和藏文的于道泉,通过钢氏结识了陈寅恪。陈氏告诉于道泉,谓钢氏的梵文水平并不高,藏文水平也不太高,只能做初步指导。由于当时在城内通晓梵文的学人实在太少,像钢和泰那样具有一定梵、藏文水平的学者实属罕见,故陈寅恪每周与钢氏就梵、藏两种语文问题进行一两次学术讨论。这是后话。
另外,陈寅恪又经常乘车自清华园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许多机密文件皆用满文书写,陈寅恪边检阅边汉译,遇有疑难之单字与词句,则随手记录,以便查字典或请人代为解答。在课余时间,多博览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陈寅恪读书时,喜将有关资料以及自己的考证、注释与心得,写录在主要书籍的天头地角。长此以往,这些书籍即成了不可或缺的笔记和资料,一俟时机成熟,便可据此而撰著。谁知战事一起,图书受到空前洗劫,私家收藏更是大都云散;但对陈寅恪来说,不仅是许多宝贵私藏的损失,而且是许多尚未完成著作之流产。
二、深层的爱国情怀与人格之魂
陈寅恪不喜欢管理实际事务,也很少抛头露面谈政治。但这并非说他不关心国事。从许多著述及诗篇中可以窥知他有满腔爱国情怀;他的爱国心乃是植根于历史与文化中,并不是爱一党一派;他既不是慷慨激昂之政客,亦非学术与政治之间之风头人物。1940年春正月,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当时物价飞涨,他有感而发,作有《庚辰元夕》一诗:
鱼龙灯火闹春风,节物承平似梦中。人事倍添今夕感,园花犹放去年红。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剩有旧情磨未尽,且将诗句记飘蓬。(《诗集·附唐诗存》第29页)
诗中所写“淮南米价惊心问”即对当时物价之感叹;货币随之大幅贬值,即“中统钱钞入手空”句所指。3月份,陈寅恪从昆明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一是应胡适之请,为其所藏《降魔变文》作跋;二是陈寅恪也请胡适为其夫人唐之祖父唐景崧之遗墨题词。另外,参加中研院会议选院长,为的是投胡适一票。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及这件事:“先是,蔡先生去世后,大家在悲哀中,前两日未曾谈到此事。后来彼此谈,不谋而合,都说要选你一票,……此事,有若干素不管事之人,如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474页)陈寅恪到重庆后作有《庚长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一诗,邮给史语所的全体同仁,以示寄怀。诗云: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诗集》第30页)
吴宓在过录以上这首诗时,有一个简短之附注,不妨抄录如下:
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诗集·附唐诗存》第30页)
这首诗的第六旬是“看花愁近最高楼”,“最高楼”是暗指蒋介石,因为当时蒋介石在国统区是最高领导。陈寅恪初次见到,但认为“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矣。
据陈门第子石泉等先后谈到,陈寅恪有一次谈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欧美、日本都去过,惟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陈寅恪在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时的情况时,他认为,在他那个班上最好的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抗战时有一天他去上课,忽然发现很多平时学习好的学生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他们皆躲起来了。他感到共产党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追忆陈寅恪》第263页)1947年春节前夕,国民党军警特务以防共为名,在北平全市搞了一次深夜挨家突击搜查,逮捕了一些人,引起市民不安与各界公愤。随即出现了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的联名宣言,谴责这种行为,陈寅恪也列名在这十三位教授其中。陈寅恪当时对前去探望他的学生谈起这个宣言,并态度非常鲜明地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据石泉回忆,出处同上)从这些事例来看,陈寅恪虽不擅料理行政事务,但并非不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他很善于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中华民族之前途命运,有十分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之历史眼光和政治主张。即便是谈治学,陈寅恪也认为治学与政治紧密相关,他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学生王钟翰说:“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说,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耳闻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尝托以重金请陈寅恪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但对奉命写书之事,仍毅然拒之。此事可非常清楚地说明陈寅恪是言教身教相一致的典范,气节之高,由此可见。(《追忆陈寅恪》第253页)
罗家伦执长清华大学满打满算不足两年(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但陈寅恪对罗家伦在清华的工作却给予非同一般之评价。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有的人当时不同意陈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评价,但陈寅恪解释说:“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所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于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像罗志希这样对中外学术都知道途径的人,在清华的校长之中,实在是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陈寅恪认为“以后也不会有”并非后人无罗氏之天资,或缺少像他的学历,而时代之不可能。(刘以焕《一代宗师陈寅恪》第203—204页)罗家伦的另一功绩是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入清华大学。
三、欲著辨亡还阁笔
转眼间,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翌日胡适应陈寅恪之邀,为唐景崧的遗墨题诗。胡适的题诗是:“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二十春。”9月23日陈寅恪复函胡适,感谢他的题诗。陈寅恪的复信是这样写的:“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今日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专此敬叩著安。(杨天石《跋“胡适、陈寅恪墨迹”》,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7页)胡适之题诗及陈寅恪之复信皆见于胡适未刊日记。唐景崧(1841—1903年)乃陈寅恪夫人唐之尊祖,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1883一1885年)慷慨请缨,出关援越抗法,因功勋卓著被清廷擢升为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任福建台湾道员,后升任台湾巡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中日战争中方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唐氏遂回厦门。这样。日军占领了台湾,唐氏内渡后,闲居桂林,于光绪二十八年冬壬寅病逝于桂林。他著有《请缨日记》和《寄闲吟馆诗存》等。陈寅恪与胡适虽不在一校,但二位皆为中央研究院理事,在学术上常互相切磋。本年5月,胡适尝请陈寅恪为其所藏之卷子《降魔变文》作跋。胡适的信是这样写的:“寅恪先生:谢谢你的信。……朱延丰先生愿译历史书,极所欢迎。谢刚主说:你说孙行者的故事见于大藏,我很盼你能告诉我。匆匆祝双安。降魔变文已裱好,甚盼你能写跋。适。廿、五、三。”(《回忆陈寅恪》第103页)礼尚往来,陈寅恪遂请胡适为其岳祖唐景崧之墨迹题诗。“九·一八’事变之消息,胡适是在翌晨才得悉的,遂将唐景崧之墨迹检出,胡适读后感慨系之,特别是读到唐公的“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之句,更是感慨颇多,遂有以上题诗。陈寅恪与胡适之心情一样,对“九·一八”事变感到震惊和悲愤。“九·一八”事变不几日,陈寅恪的挚友刘永济从东北大学返回北京,陈寅恪与其联决游北海天王堂,陈寅恪写下《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永济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一诗:
曼殊佛土已成坐,犹见须弥劫后春。(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辽海鹤归浑似梦,玉滦龙去总伤神。(耶律铸双溪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诗集·附唐诗存》第20页)
陈寅恪这首诗抚时感事,悲凉凄切,表达了对“九·一八”事变的无限愤慨。“欲著辨亡还阁笔”句,与唐景崧诗中“一管书生无用笔,旧前投去又收回”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发出了共同的鸣响,也是胡适题诗中“几枝无用笔”之另一种表达形式。
四、《文通》,《文通》,何其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