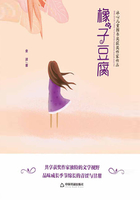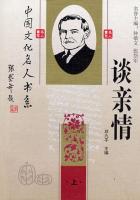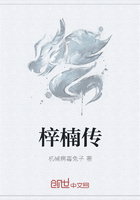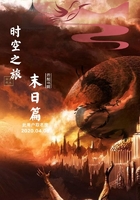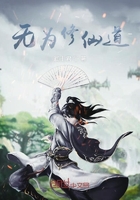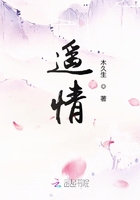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第二年,也即是1927年,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8岁,仍单身一人,住清华园工字厅。在春暖花开之季节,陈寅恪写了《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一诗:“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园林故国春芜草,景物空山夕照昏。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诗集·附唐诗存》,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11页)诗中含有淡淡之哀绪,亦些须自怨自艾矣!正是在这一年5月3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位声名显赫之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之昆明湖中,终年50岁。关于王氏自沉,迄今已70多年矣,他自沉之具体原因仍是个谜,尚无定论,而谈论王氏自沉之文章不计其数,因为本文不讨论王氏自沉,故不多引述。这里只提及陈寅恪写有七律《挽王静安先生》:“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言。王维《老将行》‘职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划向说苑)。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诗集·附唐诗存》第11-12页)为悼念王静安先生,陈寅恪还写有《王观堂先生挽词》,这是仿王国维的《颐和园词》而写成;在这篇《挽词》之前冠有长序,阐明王氏自沉之原由,述及清季掌故,又致以深切哀悼之忱。另还写一挽联:“十七年家国之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王静安先生的灵柩葬在清华园北西柳村七间房之原。王国维辞世后,日本学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立创建了“静安学社”,并筹备刊出《东洋学丛编》,以资纪念王国维。随即,“静安学社”出版了《静安学社一览》及《东洋学丛编》第一册,该册卷首刊有王国维的肖像及遗书的影印,陈寅恪撰写的《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即刊登在这一期上。就在这一年的9月,陈寅恪所授之课程除原有的外,每周加授一次梵文文法课。据浦江清回忆:“……民国十五年秋来北平,……初来清华,系吴雨僧(宓)师引荐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教授。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我曾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1-242页)浦江清尝是吴宓之高足,毕业于东南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浦氏初来清华拟给吴宓当西洋文学方面之助手,因陈寅恪需要助手,故吴宓只好割爱让浦氏当陈氏之助手。还是这年秋天,陈寅恪令学生戴家祥将孙叔平所校之孙仲容的《名原》录在自己的藏本上。到11月,国学研究院发生风潮,起因乃校长曹云祥怕梁启超取而代之,唆使研究院一学生上书,说“研究院教员旷职(梁启超因病回天津矣),请求易人。”曹氏借此欲将梁逼走。这个学生在受追问时说出了实情,最后曹氏干不下去而只得离开清华。此时国学研究院已开办两年余,所购之满、藏、蒙文图书及内典等皆由陈寅恪审定后方能购置。在陈寅恪初到清华时,校方即授权他审定图书之购置。
四、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1928年的春天刚刚过去,北京大学文学院组织就绪,陈大奇担任院长。北大历史系恢复上课,新聘陈寅恪先生讲课,授佛经翻译文学,劳于在《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是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译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追忆陈寅恪》第92页)陈寅恪授课与研究相结合,他撰写的许多论文,皆是在课堂上反复阐释、平日以各种典籍、不同语言文字比证后的结果。陈寅恪的挚友俞平伯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时,俞氏尝用楷书抄录了韦庄的《秦妇吟》,是以长卷的形式缮写的,而且注明了与流传写本文字之异同。俞氏乃专为陈寅恪抄录,也是八年后陈寅恪撰写《读〈秦妇吟〉》(后改为《韦庄〈秦妇吟〉校笺》)之远因。为此,陈寅恪写道:
戊展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独端己此诗所述从长安至洛阳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本写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而其晚年所以讳言此诗之由,实系于诗中所述从长安达洛阳一段经过。此点为近日论此诗者所未详,遂不自量,欲有所妄说。至诗中字句之甚不可解及时贤之说之殊可疑者,亦略申鄙见,附缀于后。兹请先言从洛阳东奔之路程。此段经过惜未得确知,是以于端己南游事迹不能有所考见。但依地理系统以为推证,亦有裨于明了当日徐淮军事之情势及诗中文句之校释也。(《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25-126页)
曹云祥走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志希)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与陈寅恪在德国相识,当时在德国陈寅恪与傅斯年是旧识,而罗与傅是同学,陈与罗当然也即订交了。罗家伦出长清华后,不管是私谊或是礼贤下士,皆要去拜访陈寅恪,遂即引发了有关陈寅恪的一段幽默趣事,为此,陈哲之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专门写道:
先生极其幽默。有天我们在座,他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全固统一后,政府派罗家伦接长清华,罗去看陈先生,我们也在座,罗送给先生一书,是他编的《科学与玄学》,记张君劢、丁文江辩论的旧事,陈先生翻了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罗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陈先生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罗大笑不止。陈先生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他才思敏捷,诙谐风趣大率类此。(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63页)
陈寅恪的这两幅对联的确颇有意趣。“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前句“南海圣人”说的是康有为,康氏有一别号为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乃指梁启超,梁系康氏弟子。“大清皇帝”暗指王国维,王氏来清华前系宣统之老师及溥仪南书房行走;“同学少年”,连起来看,就是清华学子乃梁任公、王静安之学生,乃康有为之再传弟子,乃溥仪之少年同学。至于“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一联,则巧妙地将“家伦”与“科学、玄学”连为一体,且上下句将罗家伦之名字镶入其中。1929年春季,清华研究院的同学立碑纪念王静安先生,他们恭请陈寅恪撰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由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拟式。陈寅恪在这篇碑铭中论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谛。碑铭不长,不妨录以备考———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莸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旺。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46页)
在这篇著名的《碑铭》中,陈寅恪所阐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止是王国维独自一人所追求,而是包括陈寅恪在内的整整一代学人在用学术生命践履这一真谛,并“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谁能说陈寅恪不是呢?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接着,这位在宣统三年(即1911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的大师,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又重复了《碑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论述,他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463、464页)陈寅恪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又“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安慰朋友。”(《寒柳堂集》第182页)这恰好证明陈寅恪先生是以学统自律,终身贯之的。陈寅恪借追思王国维,言及“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心谛,表白了自己学统人格中之生命轨迹,由此可见一斑。
五、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
王国维、梁启超相继去世,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忽失其二,对课业影响自大,而导师赵元任又经常在外调查各地方言,讲师李济经常搞田野考古工作,亦不能在校内指导学生及讲课,国学研究院的有关事宜惟有陈寅恪过问了。故研究院末期,有关指导研究生,安排助教之事,事无巨细,全由陈寅恪处理。因此,陈寅恪先生为发展研究计划,请校方拟增聘章炳麟、罗振玉、陈垣为导师,马衡为讲师。校方虽一一致聘,但章氏不屑继王、梁之后,罗氏亦不愿就,而陈垣则自谦不足以继王、梁二师,惟马衡应聘,因后继无人,学生人数亦骤然减少,1929年6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四届学生毕业时遂决定停办。校长罗家伦尝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是开风气之先”。说它的“研究空气,是极可贵的”,并劝勉学生努力发扬“在校研究的精神”。结束了一个极有学术风格而有希望的国学人才培养所,这应是国家之损失,也是王国维、梁启超二先生盛年早逝之不幸后果。当时的一位研究生,虽事隔近半个世纪,仍无限怀念:“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雩云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徒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逐步设立了与各院衔接的研究院所,到1931年设有文、理、法三个研究所,系称为“学部”,共有十个,在研究生数量上也为当时全国各大学之冠。这是后话。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其短暂的四年历程中,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他们大都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蓝文征语)他们本着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受之师教,或执教于各大学中学,或住职于文化学术机构,为中国学术文化而尽心尽力。其中陆侃如、王力、姜亮夫、刘节、周传儒、张昌圻、杨鸿烈、黄绶、宋玉嘉、蓝文征、王静如、吴金鼎等十多人先后赴欧美深造,或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仍执教于各高校,或在学术机构搞研究,这些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为我国文史哲领域的杰出人才。如姚明达,精于近代史,1942年执教于江西中正大学,率学生战地服务,途遇日军,壮烈牺牲;罗根泽,长于诸子之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长期执教于南京大学;陈守富,长于明史,执教于复旦大学;刘盼遂,以经学,小学著名,长期执教于北师大;刘节,以先秦古史著名,长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地理学、古代思想史和史学史,长期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蒋天枢,擅长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后成为陈寅恪遗著的主要编纂者,长期执教于复旦大学;陆侃如,著名文学史专家,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谢国桢,擅长明清史,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从事研究;王力,著名语言学专家,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高亨,擅长小学及周秦诸子,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王静如,著名西夏研究专家,专精于西夏语文,长期于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与教学;徐中舒,著名甲骨、钟鼎学专家,长期执教于四川大学;姜亮夫,著名楚辞、古典文学及敦煌学专家,长期执教于浙江大学;戴家样,长于契文金文学,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朱芳圃,长予甲骨考古学,执教于河南师大。他们毕生不衰的奉献和精研精神,令人崇敬,永为后学之表率。
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合聘教授,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还曾兼任一段时期的清华中文系讲师;李济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吴宓1926年3月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后,改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陈寅恪担任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后,一如既往,严谨执教。他常开的课程有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在授课之余,他精研群籍,史、集部外,并及佛典,而梵文、南北朝唐代制度则是其研究之重点,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后来陈寅恪在抗战时期出版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其内容大都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这些著作不仅根据我国古文献,而且参阅了大量中亚古文字记载的有关历史资料,开拓了历史研究之新领域,成为传世经典。
二十多年后的1950年庚寅年初,陈寅恪已执教于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写有《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一诗: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
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梁谋。
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已休。
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论集·附和唐诗存》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76页)1964年甲辰,陈寅恪又在《赠蒋秉南序》中写道: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寒柳堂集》第182页)
陈寅恪在以上诗中与文中皆表明了他的“河汾”之恩。什么叫“续命河汾”之路,其典出自隋代大儒王通隐居河汾讲学,守先待后,使传统文化如汾水之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过去,发扬光大。《新唐书·王绩传》云:“……绩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阅,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二十五史》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影印版,第596页)王通当年在黄河与汾水间设帐授徒,受业者达千余人,其中人才辈出。陈寅恪从1926年起始在清华“传道、授业、解惑”,直到1958年因受政治运动之冲击方止,达三十余年,桃李无数,遍及域内外。陈寅恪晚岁,目盲膑足之后仍怀有“续命河汾”之向往,可见他对于培育人才之理想和践履矢志不移。当然,我们应做广义解,“续命河汾”也不仅仅是设杏坛执教鞭,应有更深远重大之意义,那就是守住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构建起自成一体的知识价值体系,并在这价值体系内践履并完成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人生以至对人文学术传统的责任与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续命河汾”,可能或多或少能够传达出陈寅恪先生的现代精神之真谛。这不仅是后学对陈寅恪高山仰止之敬畏态度,而且有助于我们对百年中国学术精神及人文学术传统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