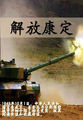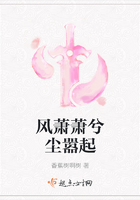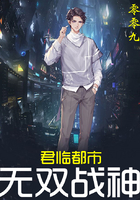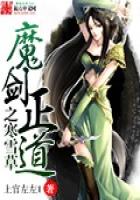1919年春末,罗振玉携眷由日本返国,暂寓上海,与王国维复度相聚。是年5月,罗振玉第三女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结婚。从此,罗振玉与王国维成了亲家,罗、王二氏二十年之学术交往与情谊,可谓又进了一大步。这一年的10月11日至12日,王国维患脚气病,罗振玉遂邀他前往天津休养。期间,罗氏复介绍陕西总督与王国维相识,正是此人在三年后推荐王氏走进清官,成为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另外,经罗振玉之介绍,王国维受聘为乌程蒋汝藻(孟)纂修《密韵楼藏书录》、《密云楼藏书志》、《传书堂记》等。王氏由此便利条件而阅读海内善本和孤本,亦大为方便了他之学术研究。几个月前,王国维还为罗振玉修改送丁衡甫挽联。丁氏为江苏山阳人,清末官至山西巡抚,系罗振玉之内从兄。“联中‘不二十载’拟易为‘廿载中’,‘曾几何时’拟易为‘数年来’,因‘曾几何时’四字与‘斯民畴复帱’五字不甚相贯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84页)1921年6月,罗振玉第三子罗君楚在上海患病,王国维非常关心,尝给王潜明写信详细谈病情。直至10月,年仅26岁的罗君楚病故。王国维十分悲痛,便写下《罗君楚传》一文,对君楚之为人与学术均作了详细之描述。王国维写道:“余初见君楚时,君楚方六、七岁,盖亲见其自幼而少、而长、而劬学、而著书。君楚为学,有异闻必以语余,余亦时以所得告之。余作《西胡考》,君楚为余征内典中故事。君楚所释《华严经》刻本,今于其殁后数月始得考定,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经》之一,恨不得以语君楚。然则余亦安得复有闻于君楚耶?将突厥、回鹘、修利诸史料不能及今世而理董耶?即异日有继君楚之业者,如君楚之高才力学,又岂易得也。君楚没,海内知参事及君楚者,无不痛惜,嘉兴沈乙庵先生与余言君楚,辄涕泗不能禁。然则君楚之死,其为学术之不幸,何如也?”(《观堂集林》外二种下册,第707页)王国维复拟为罗君楚编印遗著,还拟将罗君楚编译之巴黎、伦敦两种敦煌书目印入蒋汝藻所刊丛书之中,并为之撰写序言。半年后,王国维复撰写了《罗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铭》,与此前之《罗君楚传》一并收入《观堂集林》。
1923年5月,经升允推荐王国维接逊帝溥仪之谕旨,动身前往北京就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8月,罗振玉亦入值南斋。一时间,他们二人皆成为“皇帝”身边之近臣。进宫后,罗振玉奉命检查内府古器,他要求王国维与他一起检查,故他们又一次在一起,进行密切之合作。在这一特殊之环境里,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人格表征明显不同。王国维书卷气很浓,完全是学人气质;罗振玉更热衷于政治,完全是政客面貌。罗振玉当时家在天津,每至京,即寓王国维家。罗振玉经常往来京津两地,不常去宫里,他还要求王国维把他不在宫中时所发生之事告诉他,并且陷人深深的派系斗争之中。王国维对宫中派系斗争十分厌恶,尝写信告诉过罗氏,表达了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心愿。但此种情绪并没有影响王氏对逊帝溥仪之忠诚。与此相反,罗振玉却深深地陷入了宫廷之派系斗争中,而且愈陷愈深,最终成为这个派系斗争中之重要角色。特别是1925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逼出官以后,罗振玉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为了各自不同之目的和利益,发生了激烈之争斗,罗氏乐此不疲,并且表现活跃,上蹿下跳,显得非常有活动能量。关于罗振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详细之描述,不妨录以备考: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贴贴,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01页)
王国维青年时期受过罗振玉之帮助是事实,但并不存在王氏为了报答罗氏而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罗振玉的问题,而罗振玉之学术著作里渗透着王氏之心血倒亦是事实。关于此一点,笔者尝在写王国维的其他几篇文章中有所述及,此处不赘。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还描述道,罗振玉到官里来之时候,约五十出头,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脑后垂着辫子。由于升允之推荐,亦由于他的考古学之名义,溥仪接受了陈宝琛之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溥仪说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之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大,更受到溥仪注意。此时之王国维十分清醒,他在1925年3月,就给好友蒋汝藻写信,表示准备离开这一龌龊之地。王国维反复表示还是要以教书为业,充分显示了他之学人本色。不同的是,罗振玉仍在“恶浊”环境中。此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已明显表现出了不和谐之矛盾。这种不和谐之矛盾在他们近三十年之友情间首次凸现了出来,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这一年4月,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专任国学研究院导师。8月,王国维赴天津为罗振玉庆祝六十大寿,并献贺诗二首:“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响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赢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伦。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致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王国维文集)第588-589页)王国维在诗中认为,知遇之恩,当永远难忘;但惭愧的是与罗振玉同为南书房行走,王氏却不能同去天津陪伴圣上。这“惭愧”一词,颇富深意。从此面解,乃是自责;从彼面解,可能含有另外之意。一方面对圣上有所不满故不能像罗氏那样随其左右;另一方面便是对罗振玉不满,罗主张溥仪出洋,故愿意跟去天津,欲极力促成,此与王氏意思相左。只因双方相交既深且久,故反而不好明讲。相互抵牾,只在心中。王国维之人格独立,不为人拘,恰如他之学术独立。读这两首贺诗,亦足能窥其一斑。
七、断交与“遗折”
1926年9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享年28岁。王潜明为王国维第一位夫人莫氏所生,深得王国维的喜爱。王国维亲赴上海,直到丧事处理完毕,乃离沪北返。由于家庭琐细及误会,罗振玉与王国维发生矛盾,他们的交往至此破裂。1926年10月至12月,王国维与罗振玉互致书信,谈儿女细故,终因发生误会导致两人数十年之通信至此而绝。一直到1927年2月2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做寿时,王国维与罗振玉那天皆前往拜寿。两人相视而过,没有接言,似已情断义绝。(参见拙文《王国维最后的岁月与学术辉煌》一文)
对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失和一事,陈鸿祥先生作《王国维年谱》有一独特看法。陈先生认为,王、罗失和是出于一种误会,此说较为可信。陈先生认为:王潜明不幸病亡,罗振玉可怜爱女,而迁怒于王氏夫妇,罗曼华亦确有不满舅姑之处。但此种迁怒与不满,决不是因为所谓钱关系,亦与别人的其他揣测无关。
5月,国内政局发生激烈动荡,王国维急促不安。冯玉祥之部队直逼北京,王国维怕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冯玉祥之黑名单,遂留下遗书一份,于1927年6月2日上午,来到颐和园昆明湖畔,扑通一声,自沉而死。一位中国学术史上之绝代天才,就这样结束了自己。遗书上之主要内容,只有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6月7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关于这封“遗折”,溥仪所记: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于忠悫,派贝子溥价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谣”。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202页)
溥仪自道他尝为罗振玉所写的祭文而“迷惑”,但罗振玉极力要使人相信的是,王国维之死是“殉清”。据后来的学者说,原来“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做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罗振玉代递“遗折”目的,学界不少人皆有猜疑,但此事在深悉内情之其嫡孙罗继祖看来则毫不奇怪,他在《跋〈观堂书札〉》一文中尝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及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祖父对于王先生身后,特别是遗书的编纂刊行,不超过一年,遗书四集赫然在案,是尽了心力的。”(《读书》1982年第8期)几年后,罗继祖复在一部回忆其祖父之书中写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只有不忘久要,而自己反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愧对,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庭闻忆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8—99页)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又写道:
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份,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继而以要休退他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见该书第201页)。这其实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的“委琐龌龊”之传说。罗振玉之“逼债”说,恐怕亦是言过其实。即便是罗振玉真的逼债,王国维亦不会为那一点钱而投湖自尽。自陈寅恪在1927年6月写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后,罗振玉大加恭维:“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84页)罗振玉之赞词是出于衷心感激。因为是陈寅恪在无形中帮了他的忙;此并非陈寅恪有所爱于罗振玉,而是为了要解释王国维之死,陈寅恪在挽词中使用了多处曲笔,暗示死因之复杂。关于王国维之死,直到胡适之晚年,还保留着印象。1961年9月20日,胡适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才谈到了这一印象。胡适在谈到梁启超与王国维之死的关系,说北伐及大革命向北京挺进时,梁启超的情绪影响了王国维。他说:“那时他(按:指梁)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人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5页)不管怎么说,王国维之死,最紧张的人当是罗振玉,为此,罗振玉亦下了一番功夫。诸如设灵公祭,代“遗折”,编文集等,不一而足。在整理王氏遗著期间,罗振玉在王国维家中找到《论政学疏》草稿,遂将公之于世。罗氏还编印发行了《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高度赞扬与评价王国维之学术成就。王氏赴水远行之后,罗氏主动承担后死之责,为亡友料理后事,应使王氏在九泉之下感到有所安慰。总之,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位国学大师的学术与人生交往是真诚的,朴实的,是富有深刻内容的。两人近三十年之交往与合作,导致形成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罗王之学”,我相信,将会永远造福于后世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