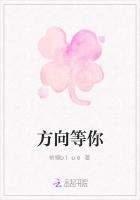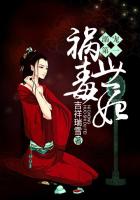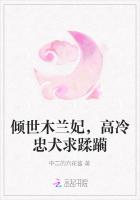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史新证》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一生最后的日子。在这短暂的岁月里,他潜心学术,日昃忘食;在担任文史哲领域多学科的授课导师之余,撰写了数种的学术专著,在海内外影响巨大,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古史新证》。此乃王国维一生治学经验之总结,亦是王国维一生学术事业的最后辉煌。
清华大学出版社于十年前影印出版的《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自《古史新证》至《西吴徐氏印谱序》凡二十九篇,首篇,《古史新证》共分五章,是一部完整的新式史学论著,与其他务篇写作形式不同,可视为独立的一篇。《古史新证》是专为给学生授课而撰写的,在这部讲义中篇幅最长。这部论著是王国维辛亥东渡日本开始研究国学以来的一部综述性的论文,是其以经史小学为基础,研究殷虚甲骨文字之新发现,以阐明新史学的创立及其研究古代历史的新方法,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专著。据北京大学已故名教授季镇淮先生回忆说,这部讲义他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图书馆的柜台上见过,可能即是裘锡圭先生所考证出来的来薰阁旧书店的影印本。对于这部讲义,甲骨学家陈梦家先生在解放后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中尝有所论及。兹不具引。此篇以后之二十八篇,无显明系统,体倒不一,内容亦非一致。殆后来讲课随时补发之单篇讲义,较多为西周铜器铭文释文与考释,亦有文物考古和周秦间古文字研究论文。其著作时间,亦先后不一。其中《史籀篇疏证序》、《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毛公鼎铭考释》、《桐乡徐氏印谱序》、《散氏盘考释》、《毛公鼎铭考释》、《盂鼎铭考释》、《克鼎铭考释》,以及《释乐次》、《记现存历代尺度》等见于《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其他各篇均不见于《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或《王国维遗书》其他部分。《毛公鼎铭考释》有前言,复作序,乃王氏特别看重之一篇,作于1916年,则系旧作。其他四篇论著,无著作时日,亦当作于此时前后。目录中有《莽量释文》、《小盂鼎释文》、《兮甲盘释文》、《虢季子白盘释文》等十六篇无“考释”,殆是以白文讲授,尚未写定成文。唯《克鼎铭考释》早写定,故与其他四篇“考释”同发。《释文》诸篇,《观堂集林》及《观堂别集》未收,《王国维遗书》其他各部亦未收。《古史新证》一篇亦如诸《释文》,《王国维遗书》各部俱未收,唯见于杂志及单行本。据说,《古史新证》这部讲义,是季镇淮先生在家中书柜里翻书时偶然发现的,季先生说他亦记不清此书是怎样得来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季镇淮从清华大学新西园移居北京大学中关园。有一天,许维通骏斋先生(已故)夫人带信让季镇淮到她家去选一些所需要的书,还说要处理许先生的遗书。季镇淮先生前去选取共五部书,其中大概即有这部讲义。季镇淮将书自许家拿回后,只《日知录》、《容斋随笔》二书常查阅,其他书俱很少用,这册讲义一次亦未用过。后来发现后,告知清华大学校史室孙敦恒先生,时孙先生正编著《王国维年谱新编》,对此讲义颇感兴趣,即携书去城内出版社请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可以出版,但出版社无钱。后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得知此事,即决定出版此讲义,请专家裘锡圭先生加以整理并撰写了分析精当之《前言》,后影印出版。该讲义199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得到北美中国制造公司总裁、白求恩国际集团副主席、著名诗人、哲学学者、教授、加拿大籍华人汤潮先生的全力支持。否则,还很难出版。王国维先生若活至今日,知悉他的这部讲义因为经费缺乏而难以出版,他不知作何感想。这是题外话。该讲义为王国维研究甲骨文的结晶,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裘锡圭先生撰写了长达万言的《前言》,逐篇介绍,校正其错讹,列成一表,为后学阅读提供了非常有力之帮助。
《古史新证》是专为讲课而撰写的,在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对当时学界过分怀疑古代典籍之思潮予以批评,并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著名“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写道: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8-39页)
那么,什么是“纸上之材料”呢?王国维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先后,列出他认为可靠或有价值的材料共十种。即(一)《尚书》,(二)《诗经》,(三)《易经》,(四)《五帝德》及《帝系姓》(此二篇同在《大戴礼》),(五)《春秋》,(六)《左氏传》、《国语》,(七)《世本》,(八)《竹书纪年》,(九)《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十)《史记》。所谓“地下之材料”,王国维认为“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殷时物自盘庚迁殷后迄帝乙时。(二)金文,主要指殷周两代。
在《古史新证》的第四章之后,王国维复据第三章与第四章“商诸臣”之内容,写了一段发人深思之案语。王国维写道: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2页)
王国维的此段论述与上引“总论”的话是紧密相联且相互呼应的。王国维的这些学术见解与他的学术实践,对我国20世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和有益的影响。
王国维去世后,《古史新证》这部讲义尝登载在《国学月报》二卷八、九、十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和《燕大月报》七卷一、二期合刊(1930年2月)上,但是《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却未收此文。1935年北京来薰阁旧书店曾影印出版《古史新证》的王氏手稿本,由于印数不多现在已很难找到。台湾的文华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和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皆收入了《古史新证》,可是在大陆地区亦不易看到。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影印出版了王氏讲义《古史新证》以后,才使这一学术名著在大陆普遍得以流行。
二、沉甸甸的著述
王国维讲完《古史新证》一课后,从1926年初开始撰著《克鼎铭考释》及《盂鼎铭考释》,并着手修订《毛公鼎》考释和《散氏盘考释》,以授诸生,其他宗周诸重器,亦多写为释文,用为演讲材料。为准备讲义,王国维致函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请其代购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一书,并告其近日学术研究情况。信说:“那珂博士《成吉思汗实录》一书,不知何处出版,现在书肆想尚有新印本出售,拟请代购二部。如能由代金引换邮便,令书肆迳寄北京,最为便捷。如无新印本,则请随时留意购一旧本见寄,并示价值。种费清神,至为感谢。弟近作《鞑靼考》一书,证明唐五代之鞑靼于辽金史为阻卜阻,并言元人所以讳言鞑靼之故,三四月后可以印出,当呈教也。”(《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6页)王氏治学之精勤,由此亦可见一斑矣。此间,王国维完成了《元圣武亲征录校注》、《西游记注》,并写信给罗振玉说:“近来写定《西游记注》,已成上卷,其下卷较少,并《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一月之中或能写成,即与《亲征录校注》同付排印,此一年内成绩也。”又说:“前令媛来禀,有四月中赴沪之说,不知随公同行否?沪上见诸老及同人,乞为致意。公到彼后,当知维三年来书问甚疏之故也。维本欲赴津,因近日无假,又闻须早车方便,是以中止。若公行在即,则须俟公赴津矣。”(《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8-429页)王国维初拟将《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校注,合《耶律文正公年谱》及《蒙古源流校注》汇集刊印。继以文正公行事未详处尚多,而《蒙古源流》一书又无佳本可校,且蒙文原本,仓卒间亦无从尽通其义意,乃将《蒙鞑备录》及《黑鞑事略》二书之校勘眉注,录为笺证各一卷,合《西游记校注》二卷,《亲征录校注》一卷,并刊之,并附鞑靼考一卷,《辽金时蒙古考》一卷于后,名为《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后附赵万里跋文,于1926年夏,由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活字版印刷发行,为院刊丛书之一种。对此,王国维尝致函神喜一郎说:
近日将敞撰《皇元圣武亲征录校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各一卷,并《鞑靼考》、《辽金时蒙古考》诸种,共为小丛书,付诸排印。大约两月中可成,印成即行奉呈教正。《鞑靼考》又登入《清华杂志》,兹先将杂志抽印本送上四册,祈惠存为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30页)
王国维之学人品性即是如此,在生活方面他可以不讲究,不求人,甚至到了穷旧潦倒之地步,他也不肯向友人张口;你不问他,他是决不会轻易开口,谈起话来总是“雅尚质朴,毫无华饰”(徐中舒语),但做学问方恰恰相反。碰到难问题他若解决不了,即直接说“我不知道”。为学术研究可四处寻觅资料,为一部《成吉思汗实录》可向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求助,请求代购;并将研究进度随时写信告知友人,以便达到学术交流之目的。是的,真正之学术研究是离不开书籍,难怪王国维一进清华园,首先考虑的是书;感谢国学研究院将购书之权利交给了他,他四处奔命,购得了难得之经典。的确,王氏之学问,无日无时不进,盖全得力于图书,然王氏自家却藏书不多,做学问多赖于藏书家。如他与蒋盂之相识相交即缘于藏书。“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胆,重友朋,其嗜书盖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交,由是得尽览其书。”(《观堂遗墨》卷上)蒋孟密韵楼之藏书,王国维皆一一检阅,提其要而编其目,对王氏学问之进境贡献极大。如门人姚名达所说:“成学固不易。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藉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版、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官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焉,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博尤为有数。返观身后所遗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79页)姚氏所言可谓极为切要矣。
三、以学术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