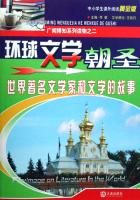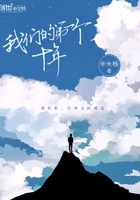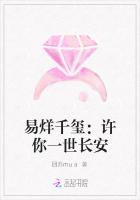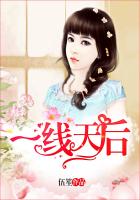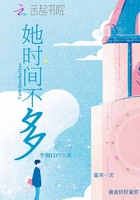王国维在教学中坚持依事实说话,反对凭空推断,这是王氏一贯之风格,也许是由于考据的治学习性养成的此一作风。姜亮夫在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上课之情景时说:“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姜亮夫在谈到王国维做学问的特点时又说:“王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要解决—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搞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打通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字下结论。这中间有一个综合研究方法,他不仅综合一次,再经过若干次总结,方成定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一切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和。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载《清华旧影》,鲁静、史睿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2页)上课时,王国维操一口浙江“海宁官话”,这更促使学生们能够聚精会神地聆听。按照姚名达之说法,当天九时上第一课,听先生讲《说文》,大家就被他之“妙解”惊服了。但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地方,还在于王国维平时亲切平等对待后学,王氏不以名家自居。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老实态度,对待学生。王力回忆他那时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到了冬天,棉袍上勒了条粗布腰带,一副私塾“冬烘先生模样”。王氏讲书经(即《尚书》),当堂告诉同学“这个地方我不懂!”谈到学术问题,他直率地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就更加赢得了师生们的敬重。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首届的即有杨筠如、余永梁、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徐中舒、方壮猷、高亨、何士骥、姚名达等近三十人。第二届的有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戴家祥、卫聚贤、朱芳圃、姜亮夫等三十余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在人文学术领域皆作出了杰出贡献。回顾昔年受教于王国维,大家皆敬仰不止,并由此而养成敬业乐群之学风。王氏门人徐中舒尝谓:“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阙,遂于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窘丛书’中,得读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民国十四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延先生主讲席,余遂决然前往就学,欲以偿积年愿见而无缘相见之大师焉。初余在南中,颇闻先生尚留辫发,至是验之而果然。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时先生方讲《古史新证》,以钟鼎款识及甲骨文字中之有关古代史迹者,疏通而证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为之根据,此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盖取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诸篇,增定而成。先生操浙江音之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当先生每向黑板上指示殷虚文字时,其脑后所垂纤细之辫发,完全映于吾人视线之前,令人感不可磨灭之印象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5—456页)可见,王国维的教学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刻!王国维非常重视直观教学,他尝谓:“教育者,非徒以书籍教之元谓,即非徒与以抽象的知识之谓。苟时时与以直观之机会,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此亦属于教育之范围者也。自然科学之教授,观察与实验往往与科学之理论相并而行,人未有但以科学之理论为教授,而以观察实验为非教授者,何独于美育及德育而疑之?”(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王国维在强调教育的直观性时将“美育”提到了一个属于培养什么样人的高度,早在1903年时,他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中详细地论述道: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性育)是也。”(《王国维论学集》第373页)
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造就一个“完全之人物”,要造就一个完全之人,教育就必须在智育、德育、美育方面下大力气,方可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智育,王国维说:“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疆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王国维论学集》第373页)关于德育,王国维说:“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同上注,第374页)关于美育,王国维说:“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人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同上374页)这一时期,王国维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教育和倡导美育的文章。此处不引。
七、最早提出“美育”的人
王国维在详细深入地分析智育、德育、美育的功能之后,明确指出:“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同上374,375页)王国维并附加了一个图,说明教育之宗旨。王氏图式内容为:教育之宗旨,包括体育和心育两个方面;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三个方面,最后才能成为“完全之人物”。由此可知,王国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同时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而且鲜明地提出教育之宗旨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
但是,长期以来,学界总有人说:“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把美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人,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44页)“在我国‘美育’这个名词最早是蔡元培在本世纪初从德文译出的。”(《蔡元培的全民教育观》,载《光明日报》1982年1月13日)不少书刊亦皆如是说。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五年中国之美育》一文中也说:“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译出的,为从前所未有。”最近还有人提出“最早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系统教育思想,是近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蔡元培。”(《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内容提要”)然而,包括蔡元培先生在内的这些说法皆不确切,均有很大误会。应该说,在中国最早提出“美育这个名词的人是王国维。蔡元培第一次提出“美育”这个名词,始见于《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其后发表了此篇文章。先后刊登于《民主报》1912年2月8、9、lO日,《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1912年2月10日出版),《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1912年4月出版)。可见,蔡氏在发表和出版此篇文章时,已是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九年以后之事了。
1920年,蔡元培出国考察,在新加坡南洋中学作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提出此一观点后,又进一步地予以了阐释:“所谓健全的人格,分为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四育,都宜时时试验演讲,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文明的呼唤———蔡元培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l、124页)这是蔡元培第一次明确提出体、智、德、美四育并重,并提出了较王国维更为完整先进的教育宗旨。但即使这个教育宗旨是“前年”(1918年)制定的,亦是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十五年后了。王国维与蔡元培之兴学思想,既有时代之差异,又有历史之传承关联。王氏的兴学思想并未超越晚近“变法图存”之思想范畴,他所要培养之“完全之人物”,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德育”之标底的,与蔡元培“养成健全的人格”与“发展共和精神”之兴学思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王国维在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首倡德、智、美、体四育并举,并提出在当时较为先进之培育“完全人物”之教育宗旨,这无疑是对我国现代教育的杰出贡献。
八、装古史与西北研究的卓越成就
王国维给人的印象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做学术研究之好料子,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后,其学术方向即转入治蒙古史和西北地理,致力于四裔金石文献之考释。1925年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赴洛河考古,所获甚半,遂将“汉魏石经残石拓本”数十种送王国维考研。他知道王国维会喜欢的。王国维对马衡如此慷慨提供这些珍贵资料,十分感佩,当即致信感谢,并告以初步所得之见解。9月9日,在致马衡的一封信中说:“顷何生士骥到校,携来所赐汉魏石经残石拓本共近七十种,百朋之锡何以加之,敬谢敬谢。询之何生,知兄上月返京并未再赴雒阳,想发掘事尚未有成议。此次所得残石至六七十片之多,可谓大观。然非兄亲往恐亦不能运至此也。汉石经中其一块有阳字及弭字者,乃《小雅》、《采薇》、《出车》二篇之文,弟才阅一过仅能知此,想兄必已考出也。(魏石经中似尚有《无逸》残字,不止《民命》一石,尚未细检。)小字隶书究系何物,兄已考出否?”(《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0—421页)马衡接到王国维之信后,亦将自己“考出”之成果告知了王国维。此后之一段时期,他们多次信书往来,交流学术研究之心得。10月,王国维假沈宝熙藏芗楂书室抄本《蒙古源流》,以校光绪中刻本,复以《元秘史》、《元史》、《明史》等书详为校注。刻本错字累累,端赖抄本正之,王国维原拟写定为校注,与蒙古史料四种并行,后因找不到善本及蒙古原本比勘,未能如愿。门人赵万里说:“余顷见漠南汪睿昌译本,较沈藏抄本尤善,文字多与先生校语合,恨先生不及见也。”(《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见《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8页)王国维的终生至交沈曾植著有《蒙古源流笺证》一书,由张尔田校补付印。张尔田在序文中说:“嘉兴沈乙庵先生与洪文卿、李芍农二侍郎同治西北舆地之学,而于此书研殷尤勤,洪、李书行世最早,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先生既归道山,与始与亡友王忠悫相往为之理董。”又在附记中说:“此书写成后,复从赵君万里假得传录亡友王静安校本,静安自识云:“乙丑重九,假沈庵官保所藏芗楂书室抄本,比勘竟,抄本亦有脱落,然文字颇胜于此本也。……细审其本脱误,亦与通行本同,实未大远于先生所据诸本,惟静安简端签语郅精,颇有可与斯笺印合处,今遴其当及小有意者,都载笺中,称王静安校以别之。”(《蒙古源流笺证》,见《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58—459页)可见,王国维在此一学术领域用力甚勤。当然,说王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转向此一领域,并非自此涉足这一学术领地。其实,王氏长期一直即致力于此,只不过根据教学之需要,将多数精力向此一领域倾斜罢了。如王氏除了蒙古史和西北地理学研究之外,是年秋,还撰写了《克鼎铭考释》,复草成《元朝秘史地名索引》,并写成《元朝秘史》跋,稍后,又跋《蒙鞑备录》,撰《鞑靼考》等。其实,王国维不论在什么时候,皆是多学科同时并进。只是在某一个阶段,他的学术表征之方式有所差异而已。就在这一年的12月16日,王国维正在研究元史,急需《黑鞑事略》等一些参考书,遂致信罗振玉,信说:“造辟之言,不知能有效否?近日风云又变,故道途恐有阻滞,故不敢赴津。前借之书,现已由上海寄到,故可无需矣。公前所印《黑鞑事略》如有存者否,乞赐一本。内人返南,殆已一月无音信,目下或者北来,稍迟则道路或不通矣。李文诚《元秘史注》纰谬甚多,与其所著无异,培老(沈曾植)乃盛称其人,殊不可解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25页)此前,王国维亦尝写信给罗振玉,说自己近来“颇力于元史,而功效不多,将来或为考异一书,校之凤老之《新史》,或当便于学者。”(同上书第424页)王国维的确精力饱满,学业成熟,著作彪炳。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尚能有丰厚的学术成果问世,这在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教师中是不多见的。王国维作为载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其学术遗产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所研究。他撰写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前些年被发现,其内容共二十八篇,有的不过虽尝发表,但已不易见到,多数则没发表过。它是王氏研究甲骨钟鼎文之结晶,复系统记录着王氏在清华的学术生涯,是研究王氏的一部重要文献。现在,该讲义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书后附有吴其昌、刘盼遂等门人的“讲授记”或“学书记”,还有北大教授裘锡圭撰写的《前言》和季镇淮撰写的《跋》。该书“简介”称《古史新证》系王氏在清华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代表了一代大师学术生涯之终点,书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