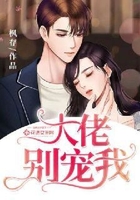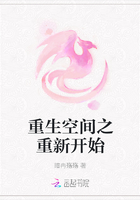在日本期间,罗振玉还写了《殷虚书契考释》一卷。该书在内容上多采王国维之说,成书后复请王国维为之校写,并为之撰前序后跋各一篇附之。前序历述罗振玉考释之成就,赞叹罗氏之书乃“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王国维说:“余受而读之,观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王氏从古文字学研究之视角,对罗氏此论著给予了极高之评价。不仅如此,王国维在该著之后跋中还写道:“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日,窃叹先生此书,铨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创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阙。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王国维为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撰写前序后跋,均见《观堂集林》外二种下,第710—713页)从上述引文可知,王国维对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评价之高,实属罕见。认为罗氏之书不在顾亭林书之下,三百年以来国朝之小学,开其端者乃顾亭林,而集大成者实为罗振玉。王国维将罗振玉之书钞写一遍,交付石印。后人即以为此书本系王国维所作,而王国维是为了报答罗振玉之提携之恩将此书献给了罗振玉。后来罗振玉之名声越来越不好,即与此有关。人们认为罗振玉又做生意又作学问,两样东西一样不能丢。于是,罗氏之学问亦即充满了铜臭味,因此而看不起罗氏,认为罗氏没有真才实学。就连大师级的学问家郭沫若、鲁迅等人亦皆有此种看法。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写道:“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竞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指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的了。”(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596页)可见,学术界的此种看法是何等之深入。然而,1951年。陈梦家先生把罗振玉的手稿找了出来,才真相大白。手稿上多处标明某条某段是听从王国维的建议而改写或增写的。那么,其余就是罗振玉自己写的了。其实,罗振玉的学问做得是很精深的,这一点郭沫若也是很清楚的。郭沫若在其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尝谓:“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页)由此可见,郭沫若对罗振玉的学问还是钦佩的,说王国维的著作署上罗振玉之名而变为罗氏著作,看来,的确是一场历史之误会。王国维撰写序跋,盛赞“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又说“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谅非虚言。其实罗振玉也给王国维抄写过诗稿,但学界并不怀疑此诗稿是罗振玉所写并送给王国维的。要不是陈梦家找出罗振玉之手搞,这一冤案不知何时才能得以昭雪呢?至于后来王国维在古文字考释以及由古文字而研究殷商历史的实践中,有许多超过罗振玉的卓越贡献,从学术传承规律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
除《殷虚书契考释》序跋以外,王国维还撰写了《三代地理小记》、《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秦郡考》、《古胡服考》、《古礼器略说》等学术专论,对远古数千年前民族战争、部落消长,以及古代地理、历史地名、古代服饰、器物等之演变,皆作了考据严密、推理精当之考释,阐明或揭发了古史中诸多未被人发现之“死角”而成学界名篇。更值得推崇的是王国维每治一学,必追本溯源,探其本末,从清理前人成果到辨明历史材料之真伪及来龙去脉入手。他研究词曲、撰著《宋元戏曲考》,无一不是如此。当然,从王国维晚年之辉煌业绩来看,他在日本所用的这些功夫,所作的这些探讨,还只能说是向更大更远之学术高峰攀登时之一种学术过渡。
七、哈同园与“二重证据法”
正在此时,亦即1915年底,有位曾做过海宁知县的同乡邹寿祺写信给王国维,说哈同夫人罗氏在上海拟创办一个学术杂志,认为王国维是最合适之人选,故邀王氏回上海就任编辑之职,并嘱王氏速回商定。王国维考虑,如此不仅可以解求职谋生问题,而且还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定潜心研究学问之处,故同罗振玉商量,接受邀请并在罗氏之前回国。当时,函邀王氏回国的邹寿祺,已在哈同门下任事,熟知内情。当王氏通过邹寿祺了解了哈同园之情况后,他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一、不问校事,不受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之聘;二、不迁入园内居住,亦不在园内办事;三、只编刊物,且有独立自主之权,他人不得干涉。经商定,杂志取名《学术丛编》,分经学、小学、史学三门,并附印古籍,由王国维执行全权编辑之事。王国维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邹安任《艺术丛编》编辑主任,另有《仓圣大学杂志》则由况夔笙执编。后来,罗振玉之许多学术著作便是在这两个《丛编》上刊出的。此时的王国维还兼为他人整理藏书,参与《浙江通志》之编纂,以增加收入,弥补诸子上学费用。另外,他寓居上海数年间的研究、写作等学术活动,主要靠哈同夫妇出钱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哈同夫妇还利用学校招牌举办古器物展览等活动,罗致了一批遗老、宿儒。康有为、沈曾植等名流,皆尝出入过园内;后来成为大艺术家的胡小石、徐悲鸿、黄宾虹、刘海粟等,亦尝与哈同园有过密切之关系。在如此的环境中,王国维虽失去了取阅罗振玉大云书库藏书藏器的条件,却获得了接触哈同收藏的古文物之方便。特别是通过替哈同园整理与鉴别龟甲骨、钟鼎彝器等古物,获得了罗氏所没有的新的研究材料。《观堂集林》内的许多不朽之考释之作,皆是王氏在哈同园的这段时间写就,并在他主编的《学术丛编》上率先刊登出来。他的《毛公鼎考释》,就是此时的一个学术成果。他还写了一篇序,谓“三代重器存于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为最巨,文以毛公鼎为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丰间,而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时学者竞相考订。”(《观堂集林》外二种上,第179页)王国维认为,咸丰以后的学者,如嘉兴徐同柏、海丰吴式芬、瑞安孙诒让、吴县吴大激等,皆尝予以考释,皆有凿空之功,大部分之铭文已考明读通。王国维正是在前辈学者考证之基础上,补其所阙,证其所是,存其所疑,集清代学人研究之大成,提出了一整套学术研究之方法。他在《序》中写道:
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观堂集林》外二种上,第179页)
这就是王国维在考释古器名物中总结出的一整套学术研究方法,时至今日,此方法仍是古文字学研究领域的最基本准则。的确,《毛公鼎铭》,在古文字学研究上具有开山的意义,对周代史事与制度文物研究上,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学术资料。应该说,王国维考释《毛公鼎铭》中所运用的考证方法是极为严密的,他在撰著此文时,给罗振玉写信谈及了此事。他在信中说:“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纸,虽新识字无多,而研究方法则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09页)王氏所谓研究方法,即是指以上所引《毛公鼎铭》序言中的那段话。王国维推出的此学术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以甲金文字之考证上,而且可以用于考证甲骨文,在其后所考释的《殷先公先王考》及汉魏石经皆运用了此种方法。王氏不仅纠正了历来学者之诸多违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近世的科学之考证方法,可以说,王氏在此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乾嘉诸考据学家。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亦承认自己在考释毛公鼎时“虽新识字无多,而研究方法则颇开一生面”。这当是很中肯之自我评价。王氏在为此篇考释撰写之序言,被历来新老学人一致推崇备至,遂成名文。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商承祚、余永梁、杨树达、陈邦怀、唐兰、朱芳圃等,在此领域取得了卓著之成就,但一般来说,其研究方法皆没有脱离王国维所规定之基本原则。
那么,什么是王国维治史之基本原则呢?那就是在《毛公鼎考释序》中首次提出的历史考证二重证据法。王氏认为,用什么方法考证金石文字呢?那得考证史事和制度文物,以了解时代之状况;复要考证古音,以弄通字义之假借;还要参考彝器,以验证文字之变化。此考证方法看上去简单,实乃不易之法,表面上看没什么稀奇,实则至关重要。与王国维同时代之学人康有为、章太炎等就对二重证据法不以为然,他们一度不相信地下出土之甲骨文。所以,王国维强调把书本上之记载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对应,加以比较分析,释其疑惑,方能定论。当然,即使这样小心谨慎,亦不能保证二重证据法不出错,任何先进的考据方法,亦不能百分之百打保票,但是,如果只搞一重证据法,那肯定会更容易出错。故,学界一直推崇二重证据法为“不易之法”。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尝谓: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47-248页)
这就是大师论大师,可谓深刻之至。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并且身体力行,这是对中国学术界做出的杰出贡献。直到今天,王氏提出并推行之二重证据法,仍然是纲领性之指导方法。如果说,王氏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是指文字的考证方法的话,那么,到了1925年在其《古史新证》中明确提出的著名二重证据法即是直指历史事件的,即: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影印出版,第2页)
其实,王氏在1916年《毛公鼎考释序》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与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就不同学科而针对性有所不同而已,便只要涉及考据学,二重证据法即不失为最好的方法之一。
八、《殷周制度论》轰动学界
1917年9月1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说:“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一、嫡庶之制;二、宗法与服术;(此二者因嫡庶之制而生。)三、分封子弟之制;四、定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五、婚姻姓氏之制;六、庙制。此六者,皆至周而始有定制,皆周之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则在德治。虽系空论,然皆依据最确之材料。大约二十左右可以告成,月杪可以写定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10页)王氏信中所言之内容,并在“月杪可以写定”的正是日后名声大噪的学术论文《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在是论文中考定殷以前之典礼制度,可证实而推知者有五个方面:一、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当虞夏时,殷之先世已称王;二、殷人兄弟无贵贱之分,嫡庶之别。故殷人祀其先王,兄弟同体;三、商之诸帝,以弟继兄,但后其父而不后其兄。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商自开国之初,即无封建子弟为诸侯之制度;四、殷周以前无女性之制。据甲骨文,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称为妣甲、妣乙;五、殷人祀典,无亲疏之殊,无尊卑之差,先公先王先妣,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皆有专祭,其合祭亦无定制。王国维认为,周制与殷制很不相同。殷周之际,乃中国制度变化最剧烈之时期。文武周公治理天下靠的就是德治,此乃周代制度之精义也。王国维感叹,这个治国之大计,其思想与规制,是后世帝王所无法想见的。此乃一种新文化、新制度,这就是周公亲自制定出来的。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又说:“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殷周制度论》,文见《王国维论学集》第2页、第12页、第13页)王国维之此篇论文不过一万一千多字,但其门人吴其昌称之为《观堂集林》中最伟大之著作;郭沫若则誉之为是一篇轰动了全学界之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桌。(《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赵万里则认为此篇论文“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曹聚仁说:“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约七千字(应为一万一千三百多字),和郭沫若先生二十四万字的《古史研究》,不相上下。”(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6月版,第11页)从以上所引王氏之论看,王氏对殷周社会制度之考证法十分缜密,义据精深,极考据家之能事。他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所归纳的结论,皆为不易之论。可以说,这是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甲骨文献和旧文献记载,写成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一篇大论文,其学术价值实不可低估。近百年来研究殷周历史文化的学者,无不参考王氏之此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