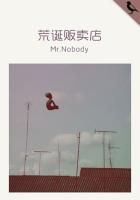他们齐心合力把方舟推到铜兽的小门前,大水上了三级台阶,院以下的城市已经化为泽国。西门望想到船夫的欲望终于实现,他要撑船去南街上领救济品,其实他也不知道南街是否还有救济品供应给他们?那些提早陷入疯狂的人们,已经化身野兽。
白教授从广播中获得的讯息或许已经过了时日,张大全和他的幽灵、护士们终日祈祷,他的父兄是否息怒,对这个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菲律宾已经有数万人葬身波涛之中,像摩西分开了红海,又让两堵海墙在菲律宾合上,人们化身鱼虾,提早进入轮回。宫崎桑不顾张大全的反对,早已上了方舟,西门望只是看了她一眼,笑着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无声无息的幽灵们正以她们独特的声腔构成了和声,虚空将赢得一切,但此刻,虚空还未染指一切。方舟已经向着城中划了过去,如同一个支点,滑到地球的垓心去了。
停电数日的第五医院,再也无法挽救那些需要大功率机器维持心跳的病人的生命,其实他们的生命指数早已归零,只是大功率机器如同生命的影子般终日轰鸣,昭示某人的灵魂正在泄漏,一直到它泄漏干净,在风中摇晃如一只塑料袋子,每个人的灵魂最后都成了一只塑料袋子,马夫的灵魂还在大功率机器的滴答声中缓缓地泄漏,大丽花已经为他上好了时间,每日里摇上几个小时,就能维持一天。那些遍布空中的灵魂,形同瞬间炸裂的礼花,很快就被人们视若无物,只有食物才能维持灵魂,人们在抢到食物的同时,拼命地吃喝、吞咽,继而在某个角落拼命地呕吐、流泪,西门望发现每条街的街牌上面都写着索多玛,这样的日子莫非真的如影随形,直到四十天后洪水退去?
白教授从收音机中收听到的只有元首在访问,其他城市在狂欢,大水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座除了此地之外的城市,一切在别人那里从未发生,甚至在新闻中都未见踪影,他们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旋涡,并且在这个时间的旋涡里终日浸泡着,如同蛇与灵芝浸泡在酒中。以致白教授更加相信,这是玛利亚的召唤所至,风从太平洋席卷了数以万吨的海水,直接掠过沿海城市,抵达常青藤小院的四周,按东南西北四个角分发了等额的海水,使这座形同索多玛的城市淹没在自身的噩梦中,就像一根腌制黄瓜。即便他们祈求玛利亚高抬贵手也无济于事,因为此刻的玛利亚尚不能说出一句人话。
其实洪水退出南街的日子不过是个星期天,好比洪水是头有灵性的猛兽,主的休息日,也是它的休息日。人们并没有忘记洪水带来的一切,使他们失去了身份,他们把横幅拉了起来,自诩是天外遗民,从此要脱离这个国度,自己管理自己,防暴警察在洪水没有退去的时候毫无踪影,如今则是与南街形影不离。星期天之后连着几天放晴,仲夏即将到来,人们早已备好了用具,每个人都带上帐篷、睡袋,在南街上逶迤开来,头上星空照耀,底下帐篷遍罩,有人把一棵刮倒的梧桐重新竖了起来,做成一个十字架,在横杠上写上“睡虫大街”,从此,这次行动就成了“睡虫行动”,只是不知道睡虫所做的梦和这头睡狮所做的梦有何不同?
清场的决定无法从这座空洞的高楼里清晰地传出来,一切还在上层的构想中,防暴警察构成的隔离带没过几天就已经锈迹斑斑,作为一个人,他们在站到这座空洞的高楼之前也已经腐蚀殆尽,生命从来没有如此耗油,在这些谷耗子与油耗子之间,南街又拓宽了四条车道,从这头望向那头,比邻而居从此成了影像,彼岸与此岸如同八条车道一样宽广。大丽花窝在南街的帐篷里,习惯自己已经是条睡虫,每天摇动发电机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帐篷中和睡虫们一起打呼噜成为日常功课,他们再也没有诉求,一切诉求最后都会成了诉苦。
上层不知道他们要什么,他们既不要自治,也不要自杀,他们就想每天在这条大街上成为无所事事的睡虫,没有一头睡狮敢与这么多的睡虫搏斗,将睡虫精神进行到底的人们,对这个国家早已没有什么奢望,他们是在响应做梦的权利,并且把梦做到下一个世纪里去。
西门望和宫崎桑把方舟撑到河道里时,南街已经成了睡虫大街,他们从救济处获得的食品只有矿泉水和方便面,一切正常的活动都已停止,除了睡觉以外,人们不再做任何事情。要是他们用警棍驱赶,用水枪冲击,用瓦斯轰炸,都不会得到任何回应,人们就像遭到催眠的动物一样,失去了使他们醒过来的信号,他们就死在大街上,像成群结队的蝗虫失去火把,他们要告诉还没有成为睡虫的人们,要是你们从来不曾有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你们就将一睡不起,成为虫豸,成为美丽而无用的一堆白花花的肉丸,但也有可能成为圣雄甘地。
对任何人而言,睡虫行动都毫无意义。但对王老头而言意义重大,他在空洞的高楼对面看管的人民公厕,变成了睡虫们隔三差五排队光临的五星级公厕。尽管这种热闹的场面只持续了不到两周的光景,王老头的人生由此却进入了幻境。
某天夜里,西门望从王老头的公厕里出来,发现人民公厕四个闪着霓虹灯的大字颇为异样,仔细一看,才知道其中的“厕”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弄成了“铡”字,四个大字就变为人民公铡,不知道那个改厕为铡的人,究竟要铡掉什么?对门空洞的大楼,还是两千万足以判死刑的官员呢?
紧随他身后出现的一个女人问他,如今是不会再有什么龙头铡的了,青天也从来都是灰蒙蒙的。
灰质是现代的本质。西门望深知这一点,如同官员们终日所穿的西装一样,基本上没有人性可言,所以才成了套装,套在里面的只是流水线生产的玩偶而已,玩偶要想再恢复人形,大抵是个偶然。
每个人的苦衷最初都以为苦不堪言,最后都成了言不由衷。那个女人走前甩干手上的水,紧走几步,很快就消失在转角的路灯下。西门望听了不由地出神,这是他遇到的第二个足以令人省思的女人,像一个装了马达的宫崎桑,独来独往,不必担心这个堕落在黑暗中的城市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她已经视黑暗为光亮,反而不习惯在白天里行走,如同蝙蝠一样,一切使人眩晕的事物都有一层虚假的光晕。
自从玛利亚过境以后,常青藤小院赶往南街的小路就化为河道,西门望一有空就自己撑船进城购买物品,宫崎桑也偶然跟他一起,直到玛利亚开始走路的时候,她才失去了兴趣。那棵作为幽灵们的庇护所的大樟树被伐作方舟以后,幽灵们也就失去了集体站墙的机会,她们多半都躲在活动室里,只在夜里月亮很好的时候,一群人围坐在方舟上,静静地如同一组希腊雕像,失去了舌头的塞壬们,或许还在思念那些早已远去的水手,他们为何没有留下一个,曾经的誓言都是风,风吹到了一座岛上,就带走了一座岛上的洁净。
清场也已结束,时间不在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它所应该完成的一切事务,睡虫们收起帐篷、拎上睡袋,乖乖地回到自己的地洞生活,每天照样要为睡狮打理毛发,在睡狮的鼾声中辨别它究竟在做怎样的梦,嫁接在这样一个梦上的生活又会使他们自己做出何种花色的梦来?睡虫们往往迫不及待地窜进了他们各自花色的梦乡,经久不归的那些睡虫就归为泥土。偶尔有那么一两只睡虫,极为幸运地跑进了常青藤小院,从此也就半睡半醒,不是加入了幽灵的队伍,就归于张大全的合唱团,终日在我主的光辉下接受赐福,“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如是又过了一个玛利亚元年,但谁也不知道一个玛利亚元年应该等于几个基督元年,西门望再次见到那个与他一同见识了“人民公铡”的女人时,她已经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睡虫的症状已经弥漫在这座城市之中,这是一种梦的瘟疫,直到这个国度成为一个梦中之国,他们在梦里说尽了好话,跳完了劲舞,再也不必求助于现实。宫崎桑看见这个女人游进来时,起初以为是条金鱼,后来才知道她是一朵花,一朵从来没有开败过的大丽花,黑色而又芬芳。
西门望把大丽花从河中捞起时,那座十字架般的街牌已经被竖到南街的尽头,睡虫大街四个字被风蚀得更加朴拙,当他们三个人把方舟快要划到常青藤小院,张大全已经赤脚跑出了铜兽的小门,向他们高喊,弥赛亚就要来了,白教授在他身后高举着玛利亚,玛利亚口含拇指,等她把拇指抽出来的时候,她正在说出“马——夫”。可大丽花知道供应马夫呼吸的发电机已经三天没有人摇上,马夫的灵魂已经如同礼花一样绽放,也许是在昨天,也许就在此刻,当那个女孩说出“马——夫”的时候,这座城市里的睡虫们兴许都在醒来,无辜的人们已经永垂不朽,但虚空不会赢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