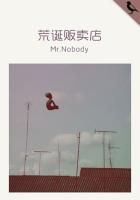这个传奇人物,就是我的好友洛加,在前面提到过的上诉部门的律师。
大学的时候,我读到一本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传记,里面一个片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少女时代的汉娜听说有个富有才华的少女安娜门德尔松,因此坐火车去找她,半夜在她窗户上扔石子,从此结识了这个女孩子,两人的友谊持续一生。我性格很内向,如果不是读到的片段,可能在美国这样异乡的环境里,会孤独到抑郁症的。但这个片段深深地影响了我,时常鼓励我,虽然我还是很少和人交流,在遇见真正喜欢欣赏的人的时候,却愿意大胆主动的结识她,期待获得真挚的友谊。
洛加就是我主动认识的,我通过一个上诉听证的案子认识了她,从此成了好朋友,彼此无话不谈,直到我回国后,她依然和我保持联系,发给我看她最近的工作,有时候是论文,有时候是上诉书,勾起我对那段日子的怀念。
那时候我的另一个supervisor凯蒂在参与这个上诉案子的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我加入。这个案子的上诉完全集中在一个核心法律问题上,即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是否会受证人认证(witness identification)困难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解决“不是我”这个问题。凯蒂负责组织收集证据和法律文书写作,洛加作为上诉部门最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上诉律师,负责协助凯蒂法律文书中的证据组织、逻辑推理、法律问题的探讨上。刚开始向我介绍和翻阅案件资料的时候(上诉资料堆在一起有六个大纸箱,而地区检察官更是准备了十几个纸箱),凯蒂就对我说洛加的聪明和才华让人惊奇,没有她,案子根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案情很简单,一个印度裔女孩,在地铁站里被一个黑人少年持刀抢劫了一条项链。事后她报警,3个小时后,NYPD拿出一系列黑人青年的照片,请女孩指认。她指认了被告。但是我们的被告米克坚决否认自己曾经抢劫项链,然而他首先有过犯罪记录(贩毒),没有任何不在场证明,而且那天刚好在那个地铁站附近活动,最后被定罪。他的审判、上诉,已经进行了六年,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六年。但他很幸运,辩护律师和家人都没有放弃他。之前的上诉辩护都失败了,这次我们提出的witness identification的问题,是一个证据法的事实认定问题,即当事人的指认是否可信。但是,指认可信度问题,虽然没有正式进入证据法教科书或者非常明确的案例,却在之前别的州的案例中被明确认可为一个抗辩证据有效性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可靠的举证,推翻这个印度裔女孩的指证,一方面是希望把这个问题、特别是其中的cross racial identification(跨种族认证)的问题,明确引入纽约州的判例。
茬开来说一下,身份认证的证据,当事人指认是其中最简单的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它至今仍然非常有说服力,因为是目击证人,直观、简便、成本小。缺点也显而易见,比如当事人认错了人,就将使无辜之人遭受牢狱之灾。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很多案件只要留下嫌疑人的皮肤、毛发、血液、精液等,就可以进行精确的DNA认证。这当然是更先进、可靠的认证办法,DNA有不同精度的认定,美国有多家实验室提供不同精度的认定。一旦高精度匹配成功,嫌疑人几乎就百分之百要被定罪。
我曾经参与一个案子,我们的当事人五年前就犯过一起强奸案,用长丝袜套着被害人的头进行强奸。五年后用同样的方式实施强奸,但这次没有用长丝袜,而是用黑布蒙着面。DNA被提取,他的完全符合(此人曾经因为别的罪名主动留过DNA)。但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的同事们仍然打算替他做无罪辩护,以犯罪偏好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一定的不在场证明为主要辩护理由。我问我的同事,胜算几何?答曰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嫌疑人都留下这些可以提取DNA的物质,也不是所有的嫌疑人都愿意主动提交DNA,DNA数据库更是远未达到指纹那样普及的地步。所以,即使在现在的美国,DNA也主要作为一种脱罪证据(没有犯罪的人主动要求检验DNA,以证明无罪),而不是检方的认罪证据。
回到凯蒂和洛加的案子。六年的时间,坐在被告席上的米克已经从少年长成了青年。他穿了凯蒂自掏腰包给他买的西装,昂首端坐在被告席上。当时我想,看起来他真的没有罪吧。
这句话可能会遭到诟病,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没罪,就为他辩护呢?这可能可以扩展到针对公共辩护人的一个尖锐问题,你们怎么知道当事人没有说谎呢?你们怎么知道他确实没有犯下这个罪行呢?特别是前面,我渲染了那么多当事人的可怜、社会环境的糟糕等。但犯了法就是犯了法,贫困、社会环境都不是开脱的理由。
答案是,我们确实不知道。并且,是的,我们对当事人的同情和怜悯,并不是为他们做无罪辩护或者减罪辩护的理由。我们选择相信当事人,选择为他辩护,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地区检察官选择不相信当事人、选择起诉他。如果我们不相信当事人、就不能竭尽全力为他辩护。如果我们不为当事人竭尽全力的辩护,他就可能陷入不公正的审判,可能被冤枉。抗辩双方都竭尽全力,各自为自己相信的事实找证据、找法律依据,最终让陪审团和法官达成最接近事实真相和符合法律精神的判决结果,是整个抗辩制度的核心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公共辩护人必须有和地区检察官一样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加入、各个大所的律师也必须每年贡献一定时间进行免费辩护工作的原因。
回到这个非常具体的证据法问题吧。Witness identification的问题,被心理学家做过的一系列试验所验证。根据这些实验,证人指认可能被一系列的因素所影响。其中在米克的案子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cross racial identification。受害人是一个黄种印度裔,接近亚洲人的面孔,而米克是非裔尼罗特人种,皮肤深黑、厚嘴唇、宽鼻翼,就是一个相貌普通、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黑人青年。事实上,纽约大街上到处都是黑人,却很少有人分辨出黑人其实有很多不同人种,长相也完全不同。心理学家认为,这就是cross racial identification的困难。实验数据显示,亚洲人、白种人,对黑人的面目认知都很困难。同样,黑人、白种人对亚洲人的面部特征指认度也很低。
此外,根据其他的心理学实验显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进行指认的时间间隔越长,指认就越容易出错。当事人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指认也会出现困难。当有武器出现的时候,由于当事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武器上,对加害人面部的认知也会出现错误。
当然,就像任何一种科学一样,公理是很少的,学说是很多的,统计学也有概率问题,实验有实验方法的问题。以上的这些心理学论文,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反对数据的存在。比如反对方的心理学家认为,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反而会牢牢记住加害者的面孔,长久不变,远强于普通交往环境中认识的陌生人。这当然也和普通人的经验并不违背,同样能被大众(陪审团或者法官)接受。但是,并没有一种经得起检验的理论和实验数据,也没有任何历史案例,完全符合这里的案情,从而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而听证的过程,就是双方聘请心理学家,各自介绍大量的法学、心理学论文和研究成果,结合案件事实,把论据摆在法官面前,由法官决定,witness identification的这些问题,是否给她的指认带来了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即她的指认出错。
听证会开庭那天,我由于和丽莎在另一个法庭出庭,迟了半个小时才进入。当时最后一排只坐了三个人,靠近门的那一侧有空位,于是我坐下。聚精会神地听了两个小时对方的证人(一个看起来非常傲慢的心理学家)接受凯蒂的一轮质询后,法官宣布休息10分钟。洛加向我伸出手,热情的向我介绍自己。我一下子发现自己坐在被凯蒂所夸赞和欣赏的洛加身边,非常开心。她五十多岁,泛白的深褐色齐耳短发,在中间分叉,身材清瘦娇小,面孔聪慧而富有魅力,长着一双真挚美丽的大眼睛。
洛加和我聊了几句刚才的听证,接着用她非常具有幽默感的腔调评论说,她很惊奇在这无比枯燥的两个半小时后,台上的法官居然还没有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