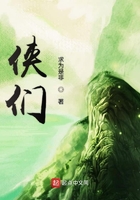又是寒冬,雪花如鹅毛落下,一层,又是一层,没有尽头。
直到万物都被掩盖,天地再无颜色,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才有片刻停息。
原本在这个哈口气就能结成冰渣子,围在炉火旁烧着炭都嫌冷,上个茅房都恨不得爹娘多生出两条腿好跑快些的日子里。自然是个人都不会选择外出。
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个傻子,此刻却在雪地上不疾不缓地走着,身后响起此起彼伏的踏雪声。
准确地说,这是一大一小两个傻子。
大人走在前面,风衣,斗笠,手套,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唯一可见的就只有那双眼睛,冷漠,孤独,不带任何感情。眉毛上沾满风霜,若不是那眸子偶然的转动,真让人误以为那只是一双摆设。
相比大人的严严实实,少年穿的却是要单薄太多。一件堪堪能够挡住风雪的大衣,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同样是一双让人很是在意的眼睛,明亮,睿智,更多的却是倔强。
若真要说这两个人除了傻之外,还剩下什么,或许还有些怪。
大人步子大,一步的距离,少年往往要花上两三步才能勉强跟上。可大人却从来没有放缓过脚步,甚至从来没有回头看过那少年一眼,仿佛从一开始身后就没有人,只他一人行走在风雪中一样。
少年也很怪,明明冻得脸色发红,牙齿在唇间不停打颤,双腿僵硬,跌跌撞撞,随时都会倒下。却硬是一声不吭,跟在大人背后默默地走着,没有丝毫求助的意思。
“啪。”
深陷雪中的脚有点脱力,一下未能全部拔起,少年便摔倒在地。
寒冷像是闻到有缝的鸡蛋的苍蝇,瞬间一涌而去,在顷刻间传遍少年的全身。
“嘎嘣。”
那是少年咬碎牙齿的声音,鲜血还未能顺着嘴角流下一寸,便已经干涸。
这是寒冬的威严,它不允许任何液体在它的眼皮子底下流动,不管是水,亦或是血。
少年挣扎着爬起,拍了拍头上的雪花,只那摔倒的一会儿,少年头上已是乌丝变了“白发”。
黑衣人越走越远,仿佛天地间已经没有能让他停下脚步看一看的东西。若不是这冰天雪地里实在没有第二个移动的黑色物体,恐怕少年的一跤就要彻底和他失散。
少年没有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小跑着向前追去。
地上因摔倒而出现的人形印子很快便被落下的雪花重新覆盖,只是那人形中间却有一条方形的长印子将人形“斩”为两半。
那竟是一把剑!一把被少年藏在怀中的剑!一把没有剑尖的断剑!
一把让少年宁愿自己冻着,也要将身上最温暖的胸膛用来温养的剑!
寒风透过衣领想要一观那剑的真容,却被捂着衣领匆匆赶路的少年甩在了身后。
风雪落下,掩盖了足迹,又重新变回白茫茫的世界,终于再没人记得这儿曾有两人来过。
少年重新跟上黑衣人的脚步,黑衣人依旧没有回头,一如之前。少年依旧没有说话,亦如之前。
也不知走了多久,两人终于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山谷,谷口空荡荡的,只有一块石碑孤零零地竖立在那儿。
石碑似是已有了年代,字迹有些模糊,加之有些地方又被雪花覆盖,只能勉强辨认出应该是李太白的《月下独酌》中的四句。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少年看着石碑,鬼使神差地上前将上面的雪花一点点拭去。他想看看他忍着天寒地冻都要来到的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
少年看着在眼前露出全貌的石碑,杵在原地,有些发愣。
诗是没错,确实是《月下独酌》,可是诗中的“酒”去哪了?没有酒的独酌,酌的是什么?难不成是茶?或者是寂寞?
少年看着石碑上,“天若不爱,星不在天。地若不爱,地应无泉。”的字样,满是迷糊。
黑衣人似是看透了少年的不解,闷闷的声音自蒙面下传来。
“别找了,酒在谷里。走吧!”
少年惊奇地回过头,使劲揉了揉眼,似是不相信一般。比起黑衣人所说的“酒在谷里”,他更不解的是为什么黑衣人会突然和自己说话,而且还是这么无关紧要的一句话。
倒不是少年小题大做,实在是黑衣人的沉默寡言已然到了一种近似哑巴的程度。
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加上眼前这次,黑衣人只对少年说过三次话,每次不到两位数。
第一次,是少年刚刚懂事,有了自主能力。黑衣人说了句,“以后全靠你自己。”自此再没有管过少年的吃穿住行,即便时刻陪在少年身边,也和放任其自生自灭没什么两样。
第二次,是在三年前,陪在少年身边的十位黑衣人只剩下眼前的一人,他说了一句,“收拾一下,我们搬家。”自此三年漂泊,居无定所。
第三次,也就是眼前。竟然只是为了告诉他谷内有酒?
黑衣人没有去管发呆的少年,迈开步子,自顾自地向谷内走去,只是这一次,少年却没有移动分毫。
“你从来不说废话,也不会用用过的东西,虽然你不说,但不代表我不懂。我没有问过你,那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你不肯说的事一定会有你的道理,别的孩子有的任性我不能有,因为我知道你们承受的远远比我想象地还要多。”
“可是,今天你开口了。我担心了三年,你终于还是开口了。事不过三,我知道你也快要离开了,就像当初的九位叔父一样。这一次,我想要任性地问你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们是谁!”
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黑衣人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那刚刚跨出的脚都忘了收回来。
少年没有上前,只是盯着黑衣人的背影,眼中满是坚定。胸口的热血滚烫,似是要破体而出。
“嗡。”
一声剑鸣,少年从怀中拔出断剑。剑身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弧,又落到地上。这轻飘飘的一剑,竟然一瞬间在雪落不停的空中砍出了断层?!
“自我懂事起,身边就只有你们十人,第一年三人一去不归,第二年又是三人,直到今天十人只剩下你。虽然你们从未告诉过我我的身世,我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了解真相,我是不是姓白?!”
“!”
黑衣人猛地转身,眼光灼灼地逼视着少年。
“是谁告诉你的!”
那语气中的质问,杀意,汹涌而出。天地间的寒气似乎又猛涨了一些。
少年摇摇头,继续说道:“没有人告诉我,原先我只是猜测,现下却是确定了。我的确姓白,还不是简单的白姓人家,或者说我的‘白’其实是落白山庄上的‘白’吧?”
黑衣人没有回答,眼神中的伤感却是给了少年一个默认。
“我跟着你漂泊了这么多年,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那几位一去不归的叔父是去替我引开仇人了吧?倒退十五年,唯一让江湖震动的也莫过于是落白山庄的覆灭,白家鸡犬不留。你以为我日日夜夜练剑,把这把剑照顾地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用这把断剑砍下那些人的项上人头!”
内劲离体,刮起漫天雪花,击打在黑衣人脸上,有些生疼。
呵,这小子什么时候连内力都修习出来了?莫不是这白家的后代,天生对武艺的领悟力就如此之高?白公是如此,吟风公子也是如此,现在连这小子也..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黑衣人露出一丝苦笑,像是第一天认识眼前的少年似的,心中却满是欣慰。
“你比你祖父,爹爹都出色得多。”
一句简简单单的夸奖从黑衣人口中说出,却好似千金般沉重。却没有让少年有半点喜悦。
“我若不更好,怎么替他们手刃害死他们的奸人?告诉我,他们是谁!”
那是一股倔强,倔强地将仇恨植入自己体内,作为自己的动力逼自己成长,倔强地将动力带来的出色又用来滋养着仇恨。
“?!”
当少年反应过来的时候,手中的断剑已经到了黑衣人手中,而黑衣人却还是站在先前的位置,仿佛从未离开过一般。没有人能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更可怕的是,从一开始,漫天大雪竟然就未能在他身上沾到分毫。
“你很出色,可惜还是差得太远。我本想告诉你,现在看来还不到时候。”
黑衣人摆弄着断剑,秀出一个剑花。
少年握着断剑的手上余温还未消散,此刻却只能咬着牙,握紧拳头。他又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弱小对于任何心有大志的人来说都是最大的敌人。
“那什么时候才是你口中的时候?”
黑衣将断剑重新抛给少年,眼中又恢复以往的冷漠。
“一个剑客,若是连自己的剑都保不住,那么不管他多么出色,也终究是个废物。而废物的下场,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你该庆幸夺下你剑的人是我,这样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直到再没有人能轻易夺下你的剑,那时候你才有资格去做那些你看透的事情。”
“要看透这世界的事很容易,要改变这世上的事却要很大的能力。记住我的话,不要轻易拔剑,一旦拔出,就要抱着必死的信念。剑就是剑客的命,剑没了,命也就没了。等到有一天,天下再没有你的剑砍不断的东西,再没有你的剑到不了的地方,那么我不告诉你的,你自然也会知道。努力吧,孩子,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少年仔细地抚摸着这把看了不知道多少遍的断剑,将剑重新放回怀里。径直走过去,与黑衣人擦肩而过。
“我需要在里面呆多久?”
“三年。”黑衣人冷冷回道。
“好。”少年丝毫没有犹豫,仿佛不管黑衣人的答案是什么,他的回答都是一样。
黑衣人转过身,左手搭在少年的肩上,拦下将要进谷的少年。
“没有我领着你,你进不去。”
少年没有回头,左手将自己右肩上的手扶开。
“我若进不去,不过一死而已。我的剑到不了的地方,就从这里开始!”
没有留恋,没有踌躇,少年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谷口。
黑衣人望着少年消失的地方,眼带笑意。
真是倔强啊!也罢,以后真的就靠你自己了。真想活着看看以后的你能走到哪一步。
转身,回头,黑衣人又隐没在来时的风雪里。只留下那座石碑孤零零地立在风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