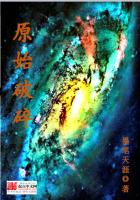魏清再见到许显军,是晚上下班回到家后。
他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鼾声震天。看得出来,许显军是真累了,以至于光脱了鞋,裤子和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地上还放着没吃完的半碗泡面。不管怎么说,没出事就是好事,扭头给范风拨了个电话后,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来。
范风很快就倒了。和魏清俩人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看着死猪般的许显军,面面相觑。
“嗯?啥时候来的,怎么不叫我?”
许显军像结束了冬眠的棕熊,从床上坐了起来,舔了舔嘴唇。
魏清识趣的端了杯水递给他。范风掏出一根烟扔了过去,坐在许显军的旁边。
“什么情况啊?一天一夜鸟无音讯,以为你进鬼子宪兵队出不来了,我和魏清都琢磨着准备开追悼会了。”
“滚你的吧!盼着我死你有什么好处?你又不是我的死亡受益人。还有我们家魏清呢。”
魏清红着眼圈看着许显军,显得楚楚可怜。许显军一把把魏清搂到怀里。
“能不当着我的面起腻吗?我怎么着也算个活人吧?别摆出一副劫后余生的劲儿,到底干嘛去了?先说正事啊。”
范风极不情愿的站起来走到窗台旁。
“还真不能怪我,完全是突发事件。”
许显军的韩国老板朴载庆本身就是七星帮的一个小头目。这次七星帮有批货从码头上岸,需要不少人手干活。本来不会让许显军这样的中国人参与其中。可无奈人手不够,加上韩国老板对许显军也相当信任,毕竟干了两三年了。相对于美国人和老黑来说,朴载庆对中国人还是有好感的,毕竟都是亚洲人,感官上没有太大落差。出于保密需要,此次卸货,所有人必须上交手机,在指定的地方呆了一整天,不许出门,不许有任何外界联系。对于许显军来说,内心清楚极了:这批货物不是毒品就是军火。可他一点也不怕。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也不在乎再干点非法的事情,何况还有一千五百美刀挣,相当于大半月薪水了。人为财死嘛!何况又死不了。就这样,在韩国人的码头屋子里睡了一整天,又干了一晚上活,这会才重获自由。
“噢,等于你被抓了壮丁了。难怪联系不上你,那你这次有没有发现什么和那包东西有关的消息?”
“没有,我又不很懂韩国话。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韩国人并不知道咱们俩的情况,也不知道那东西的下落。要不码头也不会让我来,对吧。”
“嗯,要知道了,你去了也就回不来了。”
魏清上去狠狠打了范风大腿一下,恶狠狠的说:“就你心眼坏,总盼着显军出事,他要出了事,你也别想好过!”
“整个一个未驯化的藏獒!我,别人不知道,老六还不知道吗?他敢出事,我第一个就过去拼了,九肋插刀,死而后已!”
范风得知事情没有泄漏,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言语间也调皮起来,顺带着有些不正经。屋子里气氛活跃了。
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是屋内风平浪静,屋外海浪滔天。一次天崩地裂的地震背后,其实只是起始于一次小小的地核震动。范风许显军哪里知道,看似风平浪静的芝加哥,因为上次泰华纳公园事件,七星帮已经和<十八街>暗地里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监视,拘禁,甚至暗杀,短时间内,芝加哥个报纸上尽是案件专题版面,连芝加哥警局——这个威名赫赫的美国第二大警察系统,也因为自己的无能纷纷遭受媒体和市民的诟病。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小小的黑色塑料袋。
十八街。这个和中国TJ的十八街大麻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和亚洲男孩,兄弟连这些组织一样,也和乐队没什么关系。十八街原来其实是血帮在芝加哥的一个下属分支,后来由于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基本上除于独立状态,和血帮除了生意上正常往来,几乎没什么直接隶属关系,唯一的共同点也就大家都是黑人这点了。十八街本来和七星帮也算相安无事,但随着黑人群体不断扩大,和原先韩国帮会控制下的地盘就有些重叠了,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七星帮的利益存在。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它也一样会被推翻。
十八街不是几何公理,那它注定就可以被推翻,韩国人开始反击了。总体来说,亚洲人除了RB人,基本上都不具有攻击性,大多以守成居多。欧美人则不然,天生茹毛饮血的战斗民族,美国人更是称得上横枪跃马。没有进攻性哪来的美国西部大开发?没有进攻性的民族私人会合法持有枪支?这下好了,一个进攻,一个防守,就像一场巨大宏观的足球赛,在芝加哥这个大绿茵场展开你来我往的淘汰赛。被淘汰者将无权在这个城市立足,获胜者则将获得这个城市大部分街区的毒品销售权。在巨大的财富面前,人人都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宗教,忘记了信仰,有的只是不断被夺走的鲜血和生命。
这次泰华纳公园事件就是一个双方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七星帮的毒品在一次运输中被十八街有预谋的抢劫,而后七星帮派出杀手进行追杀,希望把货物抢回来。上次范风和许显军捡到的只是其中一包,还有一包毒品被七星帮在死去的黑人身上找到了,这一点范风他们并不知情。那是一包价值几十万美金的高质量毒品,足以值得让任何人心生贪念而冒任何风险。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范风和许显军参与和直接导致了芝加哥两大黑帮的全面武力争夺,只是因为鬼使神差的坐在公园里吃个墨西哥鸡肉卷,一切就是这么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
而掀起此次如此巨大风浪的,我们的主人公范风,此刻正惬意的躺在热气腾腾的浴缸中,在白烟袅袅中,飘飘欲仙。
三楼阁楼,那黑色塑料包还静静的躺在箱子里,就像婴儿躺在自己满是杂乱玩具的婴儿床,那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