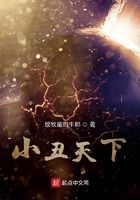不知道是不是天太冷的缘故,或者是在这个季节发生脱毛了。一头毛驴的四条腿上竟然穿着皮裤子。看皮裤子外表臃肿的样子,不难猜出来它很厚,里面一定塞了大量的丝棉。
一头驴能装扮成这样,至少说明了一点,它很娇贵。
很明显,它的主人容纳了它这种娇贵。
这应该不是一头普通的驴子。
它果然不普通。
因为,你若是仔细看的话。它后面拉的那一辆架子车,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架子车。而是用纸草糊的。
奇怪的是,楼顶上明明刮着这么大的烈风,那辆纸糊的架子车却停在那里,丝纹不动,好像根本不受风力作用。
更为奇怪的是,这纸草糊成的架子车上面竟然能躺着一个人。只不过这个人身上正盖着一层被子。连头都蒙住了。只露出一双脚,脚上面蹬着一双黑色的尖头布鞋,拥有厚厚的白色底子,给人感觉很是崭新。
娇贵的毛驴没动,后面的架子车也未动,甚至连躺在上面的人也没有动。只是,现场多出了另一种声音。
听到这种声音,你分辨不出来到底是男是女,调子响亮急促,你会以为这是一头驴在叫唤。但马上就否定了是驴叫,因为你从里面听出了人类的语言:“我们走,不要这条活太岁了!”
捡剩饭的老头子显得作难了,他嘬着牙花子说:“这可是一百万啊,难道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种声音又响起来:“是一百万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当然是我的命重要!”老头子不假思索地说道。
接下来,他骑到了毛驴身上。
毛驴却没有转过弯往出入口处走,而是直直地往前走了。
它若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就会挨近拦马墙。
楼顶边缘垒上拦马墙,是为了防止人掉下去。
不晓得这头驴子知不知道拦马墙的作用。
它好像不知道。
连它背上骑着的老头子好像也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喝止毛驴继续前行。
毛驴纵身跃过一米多高的拦马墙跳了下去。
要知道,这可是七层楼的顶端,高度少说也有二十五米。
它后面拉着的那一辆纸糊的架子车悬浮了起来,好像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将驴子下降的速度抵消掉绝大部分,并且保持它在空中的稳定,轻飘飘的落地了。
楼顶上只剩下了三个人。
两男一女。
有一个共同性质:都不曾破处。
这并没有什么光荣的,都二十一世纪了。成年处女尚可敬佩。但成年处男,在大多人眼中,绝对是一种即无能又窝囊的表现。
好像从来都是,世人的观念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对和错。
我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默不作声。但心中岂能平静,额头止不住地冒汗。
前面这俩女人,一个比一个不好惹。
可我偏偏都惹上了。
尤其是班花。我一根手指头的去留,对她造成了能否存于世的威胁。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从小到大,我总是渴望能跟别人和平相处。
可有些事情,偏偏由不得你来决定。
“姐,我们应该把杨大宝杀掉!”李贵香笑嘻嘻地说道。
她这人总是喜欢作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状态,能笑的时候,绝对不会表现得失落。这好像不应该苛责,而是应该褒奖,因为这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她这种人的存在,为诠释“幸灾乐锅”做出了贡献。
她看我的时候,就像看着一头猎物,弯成月牙的眼睛里笑意饱满。
班花脸上依然冷漠,但一双眼睛开始变得火热,因为她正在盯着李贵香的胯部。
也可以这样说,她正在盯着一百万。
很少有人在盯着一百万时眼睛不变得火热。
我开始替李贵香感到担心。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将一条活太岁从班长的尸体里拽了出来,结果发现活太岁的尾部正在死死地吸附着一颗心脏,将心脏从胸腔里带了出来。
我不知道李贵香的下场最终将会怎么样。但我总觉得,凶多吉少。
她笑得还是很开心。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二十万。二十万对他来说,乃天文数字。很明显,李贵香就是这种人。
但还有一种人,就算有了钱,也没命花。
我觉得,李贵香也是这种人。
听得班花冷冷地说道:“杨大宝可杀不得!”
李贵香一愣,问道:“怎么?难道你杀不死他?”
班花说:“就算我能杀死他,我也不敢!”
“为什么?”李贵香满脸疑惑。
“因为我这么好的身材,可不想突然被一双白生生的手撕成两半截子!”
气氛变得沉默了。
过了很大一会儿。
李贵香声音有些哑涩地说:“我也不想被撕成两半截子!”
她看我的时候,脸上不再带笑,而是充满了忌惮。
接下来,班花提议道:“妹妹,你不如亲自动手,将体内的活太岁取出来!”
李贵香点了点头。
然后她也不嫌冷,将一只光屁股坐在了白皑皑的雪地上。俩手掌夹住那条活太岁的头部,开始往外拔。
很快,她的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手上停止了拔的动作。
“怎么了妹妹?是不是出口太狭窄,撑得疼!”班花关切地问道。
毕竟,李贵香是个石女。
“除了撑得疼,还有另一种更可怕的疼,我往外扯活太岁的时候,感觉在扯我的心脏。心脏处传来一阵一阵撕裂的疼!”李贵香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地说道。
“你不能这样冒险了,活太岁的尾巴紧紧吸附着你的心脏,能把你的心脏带出体外,你焉能活成!”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劝阻道。
班花扭头瞥了我一眼,冷冽的目光里充斥着怨毒。
“姐,杨大宝说的是真的吗?”李贵香喘息着问道。
班花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阴沉着一张脸。
过去良久,她才缓缓地说道:“妹妹,你的一条命能值一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可以瞑目了!”
李贵香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她破口骂道:“赵世兰你这个臭****,是不是想害死我?”
班花笑了,容貌灿烂极了,仿佛能融化掉雪。
她周围的雪真的融化了,连融化成的水都被热量蒸发。
我仿佛置身在燃烧得熊熊的大火炉旁边,感受到了那种滂湃汹涌的热量。
她目中的瞳仁已变得赤红赤红的,仿佛两轮刚冉冉升起的红日正在炽燃着。
我突然想逃跑。
李贵香已经从地上爬起来,开始逃跑了。
她像一条蛤蟆一样,一蹦老高,往前纵去,眼看要纵出拦马墙之外了,却被一只雪白纤手给抓了回来。
班花两手捉住她腰,将其颠倒成头下脚上,于空中落下来时,像工人使用夯机一样,把她给夯在了楼顶的小地砖上。
李贵香的脑袋像西瓜开瓤一样爆裂了,瞬时毙命。
我吓得全身哆嗦,双腿发软,呆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她扭头瞧了我一眼,说:“别只顾愣着,过来帮个忙!”
我挪动脚步,慢慢地走过去了。
所谓的帮忙,就是替她把住尸体的两只肩膀,由她攥住卡在死尸胯下的那条活太岁的头部。俩人像拔河一样,一起往相反的方向使劲。
嚓嗤一声。
活太岁被拔出来了,足有五十多公分长,尾部吸附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将它纳入一口布袋中,班花转身欲离去。
“赵世兰!”我张嘴喊道。
“怎么?”她回过头来,冷冷地瞧着我。
“这尸体怎么办啊?”我指着地上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问道。
“你烧了吧!”
她也是纵身从楼上跳下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到现场,极有可能误会人是我害死的。
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暮色朦胧中,远处过来一个人,正在沿着拦马墙疾速行走。
当我看清他时,更是被吓了一大跳。
来者正是于金龙不假。
想不到他死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还能认得我:“杨大宝,你给我站住!”我若此刻站住,那就真的成了傻子。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出入口,眼看要下楼梯了。眼前影子一晃,于金龙已经挡在我面前。
但他好像不打算攻击我,或将我掳走,而是从穿着寿衣的身上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让我把它亲手转交给张元校长。
看着一张脸肿胀发黑,脖子上严重溃烂的于金龙,我到底是抑压不住好奇,问道:“你现在到底算是什么?死人?还是活人?”
他没有回答,而是从鼓凸的眼睛里逐渐流出两行污浊的眼泪。他这眼泪一流出来,气味老大了,非常臭,跟一块肉严重腐败发出来的味道一样。
当我出了北教学楼,走开老远了,再没感受到地震,来到操场上一看,已是空荡荡的了,地面上并无损毁痕迹。教学楼上的灯大部分已灭了。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想必师生们都是回寝室睡觉去了。
在教学楼的一楼,东侧靠边,有一间屋子还亮着灯。正是校长的办公室。我来到门前,迟疑了一下,最终将门子敲响了。
吱呀一声,门子打开了。
进了办公室后,我不仅看到了发须眉皆白的张元,也看到了二桃。
“你来干什么?宝子!”因为张元入赘到了我村,故而认得我。
我把那封信掏出来递过去,说这是于金龙让我送给你的。
张元脸上带着疑问,拆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纸一看,面色突变。
二桃从里处踱步过来,问怎么回事。
张元将信纸给了他,咬牙切齿道:“这是逼我把北教学楼给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