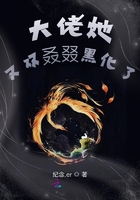不明他来时既和玉容你侬我侬同乘一车,现在倒好了,喝的晕醺醺一路需要人照顾得时候,却是知道心疼人家公主,上了她的车。
“夫人,请上车,”阿肃绷着冷脸,见暮夕不动作,遂伸手请示。
她朝他一瞥:“你家主子,你看着心疼你倒是可以上车照顾去。”
“阿肃不敢”他说话不卑不吭,始终冷着个脸,好像天生的。
楚辞靠坐着车壁抱臂低头闭目半倚在小榻前,随着车辕的滚动,他披落在背的长发也会因为颠簸一娄一娄从肩后落到肩前来,掩遮着那堪称精美绝伦的侧容轮廓,简直想让人移开一眼都难…
如斯即便坐在另边的女子手捧来时看的津津有味的话册子,吃着小案上备置的点心,被这么个男子在身边,难免走神看不进吃不下,满眼满心都是出了神的盯着对方瞅…
他是真的醉了吗?
鬼使神差放下手里的两样东西,慢慢朝前倾了过去,蹲在他跟前半俯着身,观察了许久,清晰的感觉到他均匀的呼吸声,
顿感这人醉了真好,不打不闹还能供人美滋滋的观赏,
等欣赏好终于肯坐回去继续欣赏,抬脚意外的察觉腿…竟然…呃麻了,
还好控制得当起身被她及时扶住近前的小案,免掉了一番出丑的境遇,
稳住身想好好呼口气,这时戏剧的一幕发生,只听马车下方稳稳滚动的车辕忽地被杠了一下,这一来一回,她控制不住打麻的腿,竟一骨碌朝榻上甩了过去,
砸在某人身上,抬头恰巧对上他刚睁开的迷蒙渐至清醒的眼,
暮夕的眼睛缓缓睁大乃至瞪圆,忙摆手解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有意的”
啊?
楚辞伸手握住了她的肩试图稳稳她差点因为这句话而一头栽倒的兴奋无策…
人还趴在他身上,尴尬到脸红,他只是用手轻柔握住了自己的肩,身上连丝毫的重度都没有,但她挣了挣竟没有给挣开…
不仅怀疑道,“你真的喝醉了?”
“醉了,还醉的不清,”他處眉眯眼像是在思考,“就总想做点什么出来…”
她被楚辞圈在怀里,既挣不开,就低头想往下悄悄缩走…
“想做什么?”
她往下继续努力的爬,他突然抱着她翻了个身,转瞬已将自己压在了下方,被那流畅的墨发轻拂了下耳郭痒痒的,眯着眼,一个劲儿的就想去挠,可是她腾不出手,被他压住,浑身上下乃至指甲尖脚趾心都紧绷着动不了一点,
旋即一只手落在了脸蛋上,细抚过她的眉睫眼睛鼻翼嘴唇,指尖从每个角落轻柔的划过,每过一处她的心就会跟着波澜壮观的扑腾扑腾掀起一阵狂潮,比从胸口直接掏出来扔到那该死的车辕底下碾压还折磨…
在这种被楚辞撩拨的极度心慌意乱的情况中又必须要保持清醒的知晓,他因为醉酒了才会这样,
但当对方的唇压下时,那点保持清醒的良知也很快被淹没在他那幽沉迷离的眼神中消亡殆尽…
润糯的舌尖齿甜交错着轻舐对方醇香清凉的口感,从胸口呼之欲出的心动滋味也在这样的亲昵举止下彻底膨胀爆发…
这样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毒,从内里潜藏多时的慢性直接演变成今日不可控制的发作,而毒来源于这个谜之一样让她担忧惊心同时提防始终未敢轻易交心却又总被他迷惑的男子之身—
时辰在昏厥的思想里停顿,剩下的只有快被她囚禁到天荒地老的随性所欲,无所不纵…
耳边装不进任何事,心里也再无法继续欺骗自己在他面前清明的思想…
她输的这样彻底,他赢得这样精彩…
楚辞将她抱坐在怀里整了整身前有些凌乱的衣衫,注视着怀中人在清醒过后情绪涌动的双目,往她额前印下一吻,低声浅吟,“什么也不要多,你没有输—”
暮夕眼神诧异,
为什么自己再想些什么,他都能知道—
她不清楚应当适量的去做些什么,只感觉当被他牵着下了马车,自己乖巧的如同他牵在手中的一匹终于被驯服的野马。
既然这样,有很多事情就不得不去面临摊牌的时候了,
他松开了她的手,背对她立在殿内,似乎已经知晓她会对自己说些或问些什么,再进入流华殿前便已吩咐小北他们谁都不许进来打扰,
“你想我怎么做?”
“我只想知道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
“南方,”
暮夕轻眨眼睫,“南方…哪里?”
室内片刻的寂静,楚辞缓缓沉吟,“南上破风悬玲引,马蹄归载潇珑姿,醉卧笑谈昔风华,彼时相伴尽巫山—”
暮夕向后倒退几步,悄然摇头而笑,唇下有痛楚,楚辞转身凝视着她,眼神微漾,走近几步,伸手轻抚她唇,俨然几滴殷红染于指…
她被楚辞缓缓抚平唇角撕扯之痛,却抚平不了这即将坐定的而让人心寒的事实,
自己是被掳来的—
当她渐渐明了这个被他亲口应征的真相,恍被天地间沉沉的迷茫无助渐渐所包拢,它像是一个忽明忽暗的蛹,识不清晰却能凭凭感受到要将她浑身上下裹得密不透风,大气都无法出,只因那个施加于凶之人,正是面前这个让她思绪深陷于囤境现实中却明明只记得他是自己相伴最久之人。
这个世上莫大的无奈伤害,便是发现原本所认为的该是相亲相爱之人竟给自己设下这样一个巨大的谎言—
“我……”她执拗的对视着他,“没办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