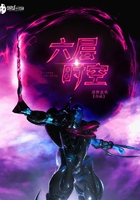郑太医一如既往提着大大的药箱出入永巷,此时正去往远涤宫给赵飞燕请脉。看护孕妇一说只为掩人耳目,郑太医真正的目的是给刘骜捎话。
郑太医做人细致谨慎,把药箱轻轻放在了地上,取出丝绢捂在赵飞燕腕上,毕恭毕敬的给她把脉,把程序客套的走了一遭。
赵飞燕私下有话与郑太医说,把不古支开到殿外打扫庭落。
赵飞燕身份已不抵从前,不能再骄纵跋扈,谦卑的给郑太医倾上一盏茶,答谢道:“劳烦太医为本宫捎句话给皇上,谢陛下不杀之恩,也感谢太医当时为我隐瞒。”
“娘娘甚是聪慧,想是料到老臣会隐瞒不报才出此计策。”郑太医谨慎但并不拘谨,畅快的喝下一盏茶后将杯子递于赵飞燕,请她再倾一盏,语重心长道,“有心掩瞒则必有私心,老臣私心保全皇后与昭仪,亦为保全太后尊严,殊不知大司马何意,娘娘可知那王根心思。”
“既然太医舍命护我姐妹,本宫便实不相瞒,”赵飞燕倾下身小声道,“王根觊觎皇位,想讨好合德劝陛下立太子呢。”
“原是这样,”郑太医似有所领悟,转了话题,“老臣有一事不明,娘娘既然说下了这个慌,可为日后铺好了路子?到时候没有龙嗣,娘娘该如何自保。”
赵飞燕仰首叹了叹气,侧身看了正在院里除草的不古,目光温和,“得罪了太后还哪敢贪生。”说罢换上肃穆的面容,整理了衣冠,郑重的给郑太医行稽首大礼,“求陛下把合德贬为庶民,放她归市井做一世平民。”
郑太医忙的扶起赵飞燕:“娘娘使不得,论官爵老臣还不及娘娘,受不起这大礼。”
赵飞燕洒着泪滴俯身不起:“本宫待罪之身不能见到皇上,求太医转达。”
“好好好,老臣会与皇上说去,娘娘快起来。”郑太医宅心仁厚,视刘骜为自出,自然视赵飞燕为媳,眼里是对后辈关怀的目光。
赵飞燕抹了眼泪再次谢了郑太医,重新坐正身子。郑太医把大药箱提到赵飞燕身前,面露喜色道:“陛下还是念着娘娘,让老臣给娘娘带来份惊喜。”
赵飞燕十分意外,刘骜能搭理自己已是万幸,她万万不敢再奢求他的什么惊喜。赵飞燕触摸着药箱,这药箱与普通的药箱不同,是镂空的遮盖。“是什么呢?”
“娘娘打开看便知。”
郑太医面容慈祥,令赵飞燕心生宽慰,她慢慢揭开盒盖,看到里面存放的东西竟吓了一跳,里面并非蛇虫鼠蚁,但比蛇虫鼠蚁来得更让她触目惊心,里面居然是一个熟睡着的脸色红润的婴儿。赵飞燕吓得差点叫出了声,连忙捂住了嘴,“太医,这……这是?”
郑太医:“是笑儿,可惜不是皇子,是冯无方的孩子,那日陛下去审许美人,许美人便招了。”
“笑儿不是……难道!”赵飞燕喜极而泣,满足的看着药箱里的孩儿,虽不为人母,但眼里满是母爱的柔情。笑儿努着粉色的雀儿般的小嘴,似乎梦见母亲给自己喂乳,赵飞燕极想把它揽入怀中,又怕惊扰它甜甜的酣梦。
孩子清纯,看着它,赵飞燕心中的仇恨烟消云散,一时间,她感知自己是极幸福的人,“皇上真知我心意,本宫有愧于他。”
“天意,恰是那天皇上令老臣携笑离开,怕是晚一刻笑就命丧人间了,”郑太医想起那天的景象,不忍心惊。
赵飞燕诧异的看着郑太医:“难道那刺客不是陛下派遣演戏的人?”
“非也,”郑太医抹一把额角的汗水,“是真正的恶人,来取笑儿的命,皇上是想令笑儿出宫做一介平民百姓,说到底,还是皇上救了这孩子一命。”
赵飞燕的喜色瞬间转换为焦虑:“那刺客是谁的人?太医,这孩子你快带走,宫里不安全。”赵飞燕能见上刘笑一面就已经满足,不求长伴它左右,只要孩子能康健长大,此生不相见她也愿意。
郑太医:“大司马怀疑是傅太后与冯太后作祟,太后也这般认为。”
立太子已是前朝政事,赵飞燕无力多问,可很是想知道刘骜会怎样处置许琰,“许琰如何了?”
“皇上暗里把她遣出宫了,”郑太医侧身朝庭外看了看,感慨道,“自陛下与昭仪相识,性情也变得温和,不喜杀戮,还常常自省自己是否愧对了各宫妃嫔。”
赵飞燕指腹触了触笑儿脸蛋,欣慰道:“皇上果真是变了。”
“娘娘多看笑儿几眼,老臣要出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