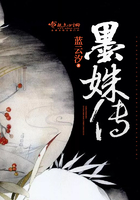今天公孙夫人比起往日足足晚了一个时辰未回,王政君心感不妙,许是麟儿弄了什么病令公孙夫人忙不开身。王政君爱孙心切,亲自提一把烛台下了地道去往柏梁台。然而王政君未到柏梁台就听见里边传来急促的摇门声,伴着公孙夫人急切又小声的叫唤。不祥的预感如同蚂蚁密密麻麻的涌上心间,王政君眉头不自禁紧蹙,加快了步伐。
王政君赶到铁门前,铁门好好的扣着,因公孙夫人的摇撼而不停震动。王政君打开门,看见公孙夫人面红耳赤,衣冠乱斜,气喘吁吁,双眼里尽是惶恐,尽管她老道于世,此时此刻也难免失措。
公孙夫人一个趔趄猛的跪地,声音发颤:“太后,赵昭仪母子失踪了,老奴不知为何被反扣在了地室里出不去。”
王政君掌上的烛台“哐当”一声掉地,她作为主要的责任人,弄丢不古事小,弄丢皇嗣责大。王政君脑海里如岩浆迸发,霎时间混乱了意识。她怔了片刻后才冷静了下来,把门紧紧掩上,小声问道:“你先起来,你可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公孙夫人起了身,“老奴搜了一遍寝室,发现昨天赵昭仪要人送来的箱子里斗篷和玉坠子不见,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对劲。”
不古的失踪深深震撼了王政君的认知,她在王政君心里就像一个裹着云雾的女妖,亦善亦恶,亦乖亦戾,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毫无逻辑。
不古比赵飞燕来得更令王政君感到害怕,虽然赵飞燕喜怒不形于色,但她做事一向目标准确,下手狠绝,赵飞燕所图的利益关系能王政君能一目了然。但不古事事优柔寡断,掐到点的适可而止,似乎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其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令她摸不着任何头绪。有时候王政君觉得不古就像一个“三界”之外的幽灵,不站在任何人的一边。
而此刻最令王政君困惑的是不古的失踪到底是他人绑架还是她自己一手策划:如果是他人劫走,那那些人是谁,可知她?如果是她一手策划,院子外可是围着七米宽的深河,她岂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
王政君语气严厉又疑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襁褓能走去哪?你又怎被锁在里头!”
公孙夫人费解诧异:“若非门外有人,老奴不可能被锁在里面。”
依铁门的构造,把自己锁在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古入柏梁台后王政君寝殿只能刘骜和公孙夫人进出。如果不是有人潜入地道的话,王政君大惊:“难道是她自己跑出去的?”
公孙夫人认可的点了下头,这是最合乎逻辑的猜测。“老奴进来时唤赵昭仪不见她回应就上小院去寻,结果就被锁上了。”
王政君紧紧握起拳头,咬牙道:“竟敢心存非念,还从孤眼皮子底下溜走,真不简单。”
公孙夫人:“太后,眼下我们该做什么,又如何跟皇上说?”
“这个女人的企图到底是什么?”王政君百思不得其解,若自己是压迫剥削而导致她潜逃可以理解,可自己为她母子瞻前顾后她却出逃是为了什么?此等举动就算她心无敌意也造成对自己的大不敬。王政君愤愤然,冷血无情道,“暗地查她下落,保全麟儿,至于那个女人,杀了,皇帝那边到时候孤自会去解释。”
王政君想:如果那女人想以麟儿来威胁骜儿,岂不是祸害,无论她目的是什么,有如此胆识和能耐的女人已留不得。
经三天三夜马不停蹄的赶程,不古回到了南淮县。不古遮遮掩掩直奔到马嫂家,把脓包托付给马嫂。马嫂本是欢喜,见不古带来了孩子都替她感到高兴,但不古只身前来又愁眉紧锁,像是遇到了大麻烦。
不古编了个理由,眨一眨眼睛泪水哗哗落下,哭啼道:“人心不慎摔死,婆家嫌我命贱克夫,把我从家里撵出来,我无处可归,马嫂求求你帮我把麟儿养大成人,我来世再报你大恩大德。”
马嫂听不古轻生的语气立刻把不古训斥了一顿,讲了大半天的大道理。不古听着有点无辜,但是心里温慰。像马嫂这样的好人一定会好好待她的麟儿,只是千万别吓了麟儿,别像吓他老爹那样……
不古假装会意释怀的笑了,在马嫂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脓包还在熟睡,不古已穿好衣裳。不古慈爱的看着脓包,它呼吸匀畅,鼓鼓的小肚子有节奏的一起一伏,睡相安稳踏实。不古看了几眼不得不起身离去,怕是多看它两眼就忍不住留下来,不古吻别了脓包,留下些钱财和一封信就匆匆走了,希望脓包能够乖乖的不哭不闹。